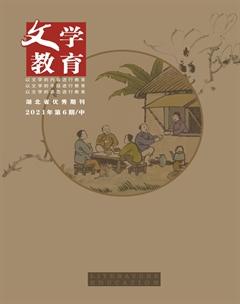美國雙語教育政策變遷分析
盧楊均
內(nèi)容摘要:美國雙語政策經(jīng)歷了放任期、限制期、機(jī)會(huì)期和現(xiàn)在的否定期,其形式也從保持性雙語轉(zhuǎn)為過渡性雙語。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美國雙語教育政策與社會(huì)的轉(zhuǎn)型邏輯自洽,在很長一段時(shí)間內(nèi)運(yùn)轉(zhuǎn)良好,其強(qiáng)調(diào)英語的偏向性是一以貫之的,但近些年卻加深了社會(huì)裂痕,美國雙語教育因此啟示我們要推行多元文化教育、加強(qiáng)國家通用語言、切實(shí)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
關(guān)鍵詞:美國 雙語教育 政策 功能主義
美國的民族雙語教育經(jīng)歷了一個(gè)漫長的發(fā)展歷程,有學(xué)者認(rèn)為其先后經(jīng)歷了放任期(18-20世紀(jì))、限制期(20世紀(jì)初至五十年代)、機(jī)會(huì)期(六七十年代)和否定期(八十年代至今)[1](p73),值得注意的是普遍認(rèn)為近年來美國的雙語教育遭到了全面的抑制[2],這與美國所標(biāo)榜的民主與自由背道而馳,美國雙語教育政策演變的內(nèi)在邏輯,以及雙語教育的經(jīng)驗(yàn)與教訓(xùn),值得深入分析。
一.政策變遷:基于功能主義視角的分析
本文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分析美國的雙語教育政策變遷。功能主義是一種積極看待社會(huì)變化的理論,它認(rèn)為教育可以帶來繁榮,并且對(duì)人類發(fā)展的前景表示樂觀。功能主義強(qiáng)調(diào)在凝聚認(rèn)知和共識(shí)的基礎(chǔ)上維持社會(huì)穩(wěn)定,它試圖將社會(huì)作為一個(gè)運(yùn)行良好的機(jī)器并且解釋它的合理性。功能主義的理論框架主要有社會(huì)化、分工合作、道德教育[3](p50)三方面,在這個(gè)范圍內(nèi),與雙語教育的變遷狀況比較相符[4](p3)。因?yàn)槊绹p語教育的變遷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特別是在融入社會(huì)、社會(huì)分工以及道德共識(shí)方面是合理的,在此從這三點(diǎn)來對(duì)美國雙語政策的變遷進(jìn)行分析。
1.社會(huì)化
功能主義認(rèn)為社會(huì)化是積極的,理想的狀態(tài)是個(gè)體通過“有機(jī)連帶”構(gòu)成整體,個(gè)人可以保持自己的個(gè)性,而社會(huì)則呈現(xiàn)和諧的狀態(tài)。但是問題在于,能否同時(shí)適應(yīng)兩種文化。蘇霍姆林斯基持有偏向的肯定態(tài)度,他認(rèn)為必要學(xué)習(xí)外語,但是外語的掌握是以祖國語言的熟稔為前提的,對(duì)祖國語言微妙之美的掌控,有助于在世界語言寶庫的徜徉。德國學(xué)者呂爾克爾認(rèn)為每一個(gè)學(xué)生都要掌握一種外語,同時(shí)適應(yīng)兩種文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而且“屬于少數(shù)民族的學(xué)生,在除學(xué)習(xí)母語外還應(yīng)學(xué)習(xí)主體民族的語言”[5](126)。
美國的雙語教學(xué)也是基于學(xué)生能學(xué)而且學(xué)好多種語言的假設(shè),文化與文化相得益彰而不是彼此對(duì)立。有學(xué)者研究發(fā)現(xiàn),在非裔美國人使用的日常英語與白人也有不同,白人說“thats cool”而黑人卻用“thats butter”或“thats phat”來表達(dá)。如果使用白人的說話方式,就會(huì)被認(rèn)為是acting white(裝白人)從而受到本群體的排斥[6]。雙語政策從放任期、限制期再到機(jī)會(huì)期,雖然政策寬容度逐漸民主化,但是它的宗旨還是要塑造美利堅(jiān)民族的“一體性”,是為了培養(yǎng)“適應(yīng)美國、熱愛美國的良好公民”[7]。
同樣的,美國的雙語政策轉(zhuǎn)向否定期,也是為了上述目的,在社會(huì)化方面,是重新發(fā)揮美國的熔爐作用,統(tǒng)一起各民族,這一理想符合美國的國情,但是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效果,2020年美國大選更是暴露了美國社會(huì)的兩極分化問題。
2.分工合作以及社會(huì)的紐帶
涂爾干將社會(huì)分工分為機(jī)械連帶和有機(jī)連帶,機(jī)械連帶會(huì)消除人與人直接的差異,產(chǎn)生一種集體意識(shí),而有機(jī)連帶使人高度分化又彼此依賴,既保留個(gè)性又促進(jìn)團(tuán)結(jié),通過有機(jī)連帶的進(jìn)行,就解決了人的異化的問題,人也不再是一個(gè)喪失意志的社會(huì)大機(jī)器的一顆螺絲釘,而是一個(gè)積極的成員。科林斯認(rèn)為社會(huì)需求是人的行為及其報(bào)償?shù)臎Q定因素。[8]
在美國雙語政策的放任期,美國還處于西進(jìn)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淘金熱、美國夢(mèng)吸引了大量移民,曾經(jīng)寂靜的美洲大陸變得熱鬧非凡,英裔、西班牙裔、法裔等歐洲移民率先占據(jù)了優(yōu)勢(shì)資源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定居點(diǎn),也有遠(yuǎn)涉重洋的亞裔來尋找機(jī)會(huì),在這個(gè)時(shí)期,美國還很年輕,它的眼光還沒有關(guān)注在教育上,因此有了一段自由發(fā)展的時(shí)期。這時(shí)美國的社會(huì)分工有很明顯的階層性,白人從事體面的工作、成為農(nóng)場主,而亞裔則充當(dāng)勞工、開設(shè)洗衣店,黑人的地位最低沒有人身自由、淪為奴隸,每個(gè)人在自身的等級(jí)上各行其是。
在雙語政策的限制期,美國社會(huì)由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科技進(jìn)步產(chǎn)生了變化。一戰(zhàn)二戰(zhàn)的戰(zhàn)場遠(yuǎn)離美國本土,客觀上給了美國發(fā)展國力的契機(jī)。為了維護(hù)國家機(jī)器的正常運(yùn)轉(zhuǎn),美國繼續(xù)其清教徒立國的核心價(jià)值,主張以英語作為文化的紐帶,威爾遜政府強(qiáng)制推行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為核心的同化政策,3K黨復(fù)興并提出“團(tuán)結(jié)本土出生的白人基督徒”[9]。上個(gè)世紀(jì)二十年代最高法院否定了對(duì)非英語語言教學(xué)的禁令,二戰(zhàn)之后美國又迎來大量歐洲移民,這些移民同樣把美國視為“自由的避難所”[11],他們對(duì)美國價(jià)值的高度認(rèn)同成為新的社會(huì)紐帶。在這種情況下,少數(shù)族裔希望融入美國文化,雙語的限制對(duì)此推波助瀾。
在雙語政策的發(fā)展期,隨著美國《移民和國籍法》[11]的頒布,美國社會(huì)的人口組成呈現(xiàn)多元化,這一時(shí)期伴隨著平權(quán)運(yùn)動(dòng)的蓬勃開展,對(duì)少數(shù)族裔的優(yōu)待成為共識(shí)。后來矯枉過正而且引起了白人群體的反彈,在強(qiáng)調(diào)“black lives matters”的時(shí)候,出現(xiàn)了“all lives matters”的聲音[10]。按功能主義的觀點(diǎn)來看,社會(huì)的有機(jī)連帶是在保持個(gè)性的前提下的彼此依賴,美國的問題不是沒有保持個(gè)性,而是社會(huì)分工出現(xiàn)了問題,階級(jí)固化、貧富差距驚人[11],在這種情況下,學(xué)習(xí)英語有助于跳出少數(shù)民族圈子、提高社會(huì)地位,因此美國政府選擇了讓雙語教學(xué)過渡到英語教學(xué)。
3.道德教育:民族認(rèn)同和愛國主義
功能主義社會(huì)學(xué)家涂爾干認(rèn)為:道德教育是社會(huì)的基礎(chǔ)。他將社會(huì)看作一種實(shí)體,社會(huì)規(guī)范的道德是一種共同理想,其解組就會(huì)產(chǎn)生迷亂[4](p46)。關(guān)于美國的共同理想,有學(xué)者指出“自由、民主、公民權(quán)利、三權(quán)分立、政教分離、以私有財(cái)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為基礎(chǔ)的市場,憲法至高無上的法制等等,都是美國社會(huì)成員一致接受并不容挑戰(zhàn)的原則。”[13]美國社會(huì)被認(rèn)為是較為同質(zhì)化的社會(huì),特別是二戰(zhàn)之后美國經(jīng)濟(jì)騰飛出現(xiàn)了大量穩(wěn)定的中產(chǎn)階級(jí),而羅伯特.達(dá)爾認(rèn)為具有同質(zhì)化的社會(huì)的社會(huì)更有可能在民主政治上取得成功。
雙語政策是美國多元文化政策在教育方面的重要組成。1968年的《雙語教育法》規(guī)定地方教育部門要為非英語母語的中小學(xué)學(xué)生制定提供新的學(xué)習(xí)計(jì)劃,聯(lián)邦政府提供經(jīng)費(fèi)支持。1973年發(fā)布了《1973年雙語教育綜合修訂法》,對(duì)現(xiàn)有的雙語教學(xué)進(jìn)行改進(jìn),出資支持雙語教材的編訂和出版。通過進(jìn)行雙語教學(xué),能夠使少數(shù)族裔學(xué)生產(chǎn)生被接納感,從而增強(qiáng)對(duì)國家價(jià)值的認(rèn)同。[12]在六七十年代的雙語政策蓬勃發(fā)展期,保證少數(shù)民族權(quán)益成為政策正確,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受到了極大尊重,但是這在某種情況下又導(dǎo)致了如今美國社會(huì)的分裂。80年代的里根政府特別反對(duì)雙語教育,里根總統(tǒng)認(rèn)為雙語教育使得學(xué)生“不能獲得足夠的英語知識(shí)以進(jìn)入就業(yè)市場”,因此是“與美國的思想背道而馳”的[2],他在這里提到的美國思想不言而喻,是一種國家的共識(shí)。
統(tǒng)整的社會(huì)必然有一套“道德符碼”,包含各種社會(huì)責(zé)任與任務(wù),而功能主義認(rèn)為這些都是有利于個(gè)人與社會(huì)的[4](p51)。關(guān)于雙語教育產(chǎn)生的民族認(rèn)同,有兩種相反的看法,一種認(rèn)為少數(shù)民族在民族文化被認(rèn)同的時(shí)候會(huì)對(duì)國家產(chǎn)生歸屬感,另一種則認(rèn)為強(qiáng)調(diào)少數(shù)民族文化則削弱了主流文化的融入,美國的雙語教育政策也在這兩種認(rèn)知之間搖擺。奧巴馬政府對(duì)《不讓一個(gè)兒童掉隊(duì)法》進(jìn)行改進(jìn),為公民教育提供資金支持,同時(shí)要求大學(xué)生參加社區(qū)服務(wù)[13]。
二.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
美國的雙語教育既有經(jīng)驗(yàn)也有教訓(xùn),總的來說,它試圖造就“美利堅(jiān)民族”的意識(shí)是正確的,但是卻落入了回歸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文化的歷史中。對(duì)于中國的借鑒意義在于,要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真正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在此基礎(chǔ)上開展有特色的雙語教育。
首先,要推行多元文化教育。
美國的教訓(xùn)表明不能通過抑制少數(shù)民族文化來強(qiáng)求和諧統(tǒng)一,只有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才能實(shí)現(xiàn)國家的繁榮。之前的論證一直在說明美國政策的幾次變遷是合理的,其實(shí)是在指“變”是合理的,但是“變”的方向不能走向單一,而應(yīng)該實(shí)現(xiàn)“一核多元”、“中和位育”[14]。核是主體民族的主流文化,多元是少數(shù)族裔的燦爛文明,有了核就有了凝聚的中心,但是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也和諧共存,不能漠視或者歧視。“中和位育”源自禮記,這種多元文化觀強(qiáng)調(diào)“天人之和”、“禮樂教化”,通過雙語教育促進(jìn)文化的繁榮[15]。
其次,突出國家通用語言的溝通功能。
對(duì)于美國學(xué)校而言,雙語教育更側(cè)重加強(qiáng)英語的教育和輔導(dǎo)[16]。如今美國大學(xué)普遍開展了寫作中心服務(wù),學(xué)生可以通過電話、郵件預(yù)約,帶上寫好的文章論文接受一對(duì)一的輔導(dǎo),老師一般是經(jīng)過寫作中心培訓(xùn)的在校大學(xué)生,通過這種方式,美國大學(xué)為處境最不利的英語能力不足學(xué)生提供了免費(fèi)的幫助,這也是一項(xiàng)深受少數(shù)族裔和留學(xué)生歡迎的服務(wù)[17]。另外還有許多大學(xué)設(shè)立了英語中心ELC(English language center), 英語不過關(guān)的學(xué)生可以通過1~4個(gè)學(xué)期的英語學(xué)習(xí)拿到英語能力證明,大學(xué)就可以直接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錄取。英語中心也大量招收留學(xué)生和少數(shù)族裔。從上述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美國教育對(duì)英語能力的重視是恰當(dāng)?shù)模颐绹鴮W(xué)校采取的大量措施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有學(xué)者將我國的各民族語言比喻為中華民族交響樂中樂器,既要掌握國家通用語言,也要傳承好少數(shù)民族語言,“以五聲播于八音,調(diào)和諧合而與治道通”[18]。
最后,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
美國現(xiàn)行的雙語政策的最大訴求就是培養(yǎng)有共同信念的美國公民,雖然它的嘗試近年來證明效果不佳,但是這更啟示我們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始于清末,成型于中華民國的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爭中逐漸普及全國[19]。費(fèi)孝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書中提出中華民族不是統(tǒng)稱而是實(shí)體,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gè)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不同層次可以并行不悖、作為共同體生存和發(fā)展[20]。美國的雙語政策的教訓(xùn)就在于未能將非裔、拉丁裔、亞裔等少數(shù)族裔的文化和歐洲文化同等看待,它沒有形成一個(gè)高層的一體格局,各個(gè)族裔反而更加激烈地爭取本民族的語言權(quán)利。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描述美國雙語政策的變遷展現(xiàn)了美國民族文化問題的演變邏輯,試圖從功能主義的角度解構(gòu)其合理性,說明在八十年代以前美國雙語政策的調(diào)節(jié)機(jī)制都是有效的,但是在雙語政策全面衰落之后,美國社會(huì)的裂痕不斷擴(kuò)大,美國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問題所在并竭力將英文作為重點(diǎn)。美國的這種努力效果不佳,近年來的社會(huì)抗議游行甚至暴力事件不斷,啟示我們要推行多元文化教育,在突出國家通用語言的溝通功能的同時(shí)真正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
參考文獻(xiàn)
[1]胡玉萍著. 美國當(dāng)代少數(shù)族裔教育理論與政策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10.
[2]劉麗敏. 美國雙語教育政策及主要模式研究[J]. 齊齊哈爾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9, (6):157-160.
[3]譚光鼎,王麗云主編. 教育社會(huì)學(xué):人物與思想.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9.01.
[4]Sadovnik A R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Reader[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Reader, 2015.
[5]曲木鐵西,夏仕武著. 少數(shù)民族高等教育導(dǎo)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07.
[6]Carter P L . ''Black'' Cultural Capital, Status Positioning, and Schooling Conflicts for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Youth[J]. Social Problems(1):136-155.
[7]張利國,郭立強(qiáng).美國國家認(rèn)同教育發(fā)展趨勢(shì)與啟示[J].現(xiàn)代大學(xué)教育,2020(02):78-86.
[8]Collins, Randall.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6, no. 6, 1971, pp. 1002–1019.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093 761. Accessed 29 Dec. 2020.
[9]徐長恩. 戰(zhàn)爭、制度與多元文化政策——美國族群關(guān)系演變的推動(dòng)因素[J]. 西北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4, 第51卷(2):91-97.
[10]Suryia Nayak. (2020) For women of colour in social work: black feminist self-care practice based on Audre Lordes radical pioneering principles. 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 8:3, pages 405-421.
[11]劉世強(qiáng),趙樂.社會(huì)分化、民主失靈與美國政治的未來前景[J].當(dāng)代亞太,2018(05):129-155+159-160.
[12]周莉萍.美國多元文化政策初探[J].國際論壇,2005(02):62-67+81.
[13]康夏飛. 二戰(zhàn)以來美國公民教育演變與發(fā)展[D].西北師范大學(xué),2011.
[14]吳明海.一核多元? 中和位育——中國特色多元文化主義及其教育道路初探[J].民族教育研究,2014,25(03):5-10.
[15]曾繁仁. 中和位育——東亞儒家文化圈共同的哲學(xué)訴求[J]. 甘肅社會(huì)科學(xué), 2017, (3):44-48.
[16]孫云鶴. 美國雙語/多語教育政策的變遷、反思及其啟示[J]. 湖南師范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學(xué)報(bào), 2019, 第18卷(6):92-99.
[17]梁卿,潘滔.美國高校“寫作中心”(Writing Center)運(yùn)作模式及運(yùn)作問題探析——以中密歇根大學(xué)(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為例[J].海外英語,2019(09):46-47+50.
[18]蘇德,張良,江濤.新時(shí)代背景下的少數(shù)民族雙語教育:機(jī)遇·挑戰(zhàn)·策略[J].民族教育研究,2019,30(04):69-74.
[19]金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西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0(02):33-42.
[20]費(fèi)孝通主編.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 1999.09.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