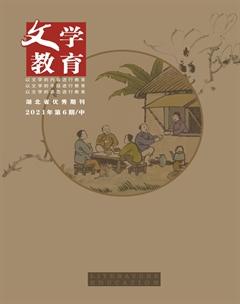《海盜船長》的英國性探究
李雪
內容摘要:《海盜船長》中對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的書寫,無不透露出英國人的性格和傳統。一方面,英國人文明包容、具有虔誠的清教道德品質;另一方面英國具有海盜傳統,但小說中的海盜卻在引路人威廉的帶領下,成功轉為商人。這種轉變為英國民族身份的構建過程提供了真實寫照,也寄托了笛福對英國未來發展方向的期許。
關鍵詞:《海盜船長》 英國性 海盜 商人
笛福的《海盜船長》一直處于邊緣化的狀態,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受到國內外學者重點關注,且集中在敘事技巧、商業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角度。有關小說中英國性的研究屈指可數,而笛福對辛格頓等人的冒險經歷描寫折射出英國文明虔誠的新教信仰。同時,海盜傳統地位的變化與英國轉型時期的發展狀況有密切聯系,海盜到商人的身份轉變對英國性的構建以及后來的變革具有重要意義。
一.關于“英國性”的探討
“英國性”(Englishness)一詞的首次出現與一位名為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的詩人有關,他把德國的浪漫主義帶到了英國,但浪漫主義在當時并不符合英國的語言模式,因而受到人們的譴責,所以他稱自己具有“非英國性”(un-Englishness),以此來諷刺英國人民。近幾年來,隨著英國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對“英國性”的探索業已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凱瑟琳·威爾遜(Kathleen Wilson)認為“英國性”是指英格蘭特性,即英格蘭作為一個民族在各個領域中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特點,而且它是歷史的產物,它所蘊含的文化和政治意義隨時代的發展在不斷變化。羅杰·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在《英格蘭挽歌》(England: An Elegy)中指出傳統的英國性已不復存在,多民族文化構成了當代英國。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在《英格蘭:英國想象的起源》(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中表明英國性本身就具有多樣性,異質同存已成為英國文學和藝術作品的特點。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小說《白牙》(White Teeth)則探討了英國性和多元文化之間關系的問題,并且試圖重構英國民族身份的原型。
可以看出,這些學者和作家都認為英國和“英國性”正發生變革,英國的身份認同也面臨危機。不過這都是19世紀以后的發現,對于18世紀的英國性卻無人問津。愛默生曾說:“如果有一項可以測試天才的標準,那就是成功;如果上個千禧之年世界上有一個成功的國家,那就是英國”。18世紀早期,英國正處于向工業文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從物質生活資料的獲取、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宗教信仰對比、海盜到商人身份的轉變,笛福以其深刻的筆觸參與了英國性的構建。
二.虔誠的新教信仰
1688年,英國國會上下決定鏟除公然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擁護瑪麗和威廉為英國的國王。瑪麗是詹姆斯二世與第一任新教皇后的女兒,威廉三世是信奉新教的荷蘭國王,他為了保護荷蘭不受路易十四的侵犯而奮戰不屈,在歐洲被視為捍衛新教的斗士。為了鞏固新教的地位,國會規定“英國國王必須信奉新教,必須是英國教會成員,且不能與天主教徒結婚”。這項條款迄今依然是英國憲制的一部分。而笛福生活時代的君王威廉三世包容仁慈,正是他心中理想的新教君主形象。笛福在其作品中對魯濱遜、弗蘭德斯、辛格頓、羅克姍娜等具有強烈懺悔精神的清教徒形象的塑造,都反映著他對新教的支持。笛福的清教精神首先體現在英國與其他歐洲民族的對比上。辛格頓在冒險過程中,遇見了許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其中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土耳其人,通過比較英國人與這些人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言行舉止方面的差異,充分展示出英國清教徒的堅貞虔誠,從而體現了英國民族的文明族裔性。
駛向錫蘭島的航行中,威廉向辛格頓闡述了諾克斯船長的故事,通過諾克斯與荷蘭人的對比,凸顯了英國人特有的清教徒的虔誠信仰。諾克斯是一位英國人,擔任一艘東印度船的指揮官,卻遭到虛偽的國王和將軍誘騙,在錫蘭島登陸上岸,自此他和兒子小諾克斯過著痛苦的俘囚生活。老諾克斯離世后,他的兒子變得日漸消沉、一蹶不振,即使物質上的舒適也無法帶給他任何安慰,因為異鄉完全沒有上帝的福音和圣經的儀式。可是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得到一本圣經,他便把這看成是上帝的恩賜:在異國得到一本用本族語言寫成的圣經,是他在俘囚中“最大的安慰”。而另一位有著同樣遭遇的荷蘭人卻表現得完全相反。他被俘虜后,自愿效忠,成為國王的侍者,甚至還誘騙辛格頓等人上岸。因此,笛福借威廉之口指出,他只不過是野蠻人的工具,因為文明的歐洲人絕不應該屈從于這樣落后、未開化的國家。諾克斯和荷蘭人都是基督徒,可是兩人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深深眷戀故土,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后者輕易背叛祖國,成為野蠻異教徒的工具。同為信仰新教的歐洲國家,卻只有英國展現出有新教徒應有的文明虔誠。
顯然,在笛福心中,對《圣經》執著追求、對上帝保持虔誠,是一名合格的新教徒不可或缺的品質。除了勤奮刻苦、文明虔誠,懺悔精神也貫穿著笛福作品中的每位主人公,在辛格頓身上就有明顯表現。取得大筆財富后,本應該是“享樂”的時候,可是辛格頓深知自己的財富是靠掠奪和暴力獲取的,已經無法逃脫上帝的懲罰。這筆巨大的資產反而給他帶來了憂慮和不安:“我現在應該為此而處絞刑,以后我應該為此而入地獄……我真心憎恨我自己是一條狗,是一個無恥之徒,曾經做過盜賊,做過殺人犯……我腦子里閃現著永遠無法懺悔的思想,因為不償還給人家,懺悔就不誠心,所以我一定要受罪,沒有逃脫的余地。”辛格頓最終坦白了自己燒殺搶掠的罪行,他無時無刻不在懺悔。如此一來,沒有宗教信仰的辛格頓變成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通過向上帝懺悔,他擺脫了自己的罪惡感,提高了他作為英國人的形象。
事實上,幾乎所有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國家,尤其在18世紀早期,都是英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所以在小說中,笛福刻意丑化其他種族:“所有世界各個民族,自命為基督教徒的,以葡萄牙這個民族最無信義,最荒淫無恥、最為驕橫殘暴”,“左右盡是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土耳其人、異教徒,以及諸如此類的人們”,通過貶低其他國家的宗教信仰,來彰顯英國文明虔誠的形象,這也是笛福塑造英國性的一種手段。
三.從海盜到商人的轉變
英國是具有海盜傳統的文明,所以最初海盜在英國人眼中并非不法之徒,相反,他們憑借不畏艱險的開拓精神被人們奉為英雄。因為海盜的冒險經歷激起了英國人對海洋的向往,他們確信經過海外掠奪和殖民可以建構一個霸權帝國,《海盜船長》中對海盜行為的英雄化充分反映了這種擴張欲望。而海盜的英雄地位有著深厚的淵源。十六世紀,西班牙壟斷著歐洲的貿易,內憂外患的英國沒有足夠的實力與之抗衡,伊麗莎白一世機智地利用“才藝超群的海上探險家們、勇敢無畏的商人們拓展財源”,以此緩解國內危機。她向海盜頒發“私掠許可證”(Privateering Commission),使海盜行為合法化。因此伊麗莎白一世在位時期(1558-1603)被稱為英國海盜的黃金時期,由于與海盜交往密切,她本人也被稱為海盜女王。1588年,英西海戰爆發,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約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擔任指揮官的海盜艦隊以其豐富的海戰經驗和遠程炮攻技術戰勝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這為英國打破西班牙的海上貿易壟斷地位提供了決定性的前提。所以,在伊麗莎白時代,海盜掠劫被視為抵御西班牙入侵的愛國行為,海盜們也處于英雄的地位。某種程度上來說,海盜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達到了最廣泛的一致,海盜的力量助推了大英帝國的強盛。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海盜們也將目光瞄準了中立國家船只上的貨物和財富,對其進行攻擊和搶掠, 這讓女王非常難堪。雖然從海盜崛起實屬無奈之舉,但英國還是被貼上“海盜之國”的標簽,這段不光榮的歷史十分不利于英國文明帝國形象的塑造。詹姆士一世即位后, 英國與西班牙停戰,英國宣稱所有形式的私掠行為都被視為非法。于是,大量水手失業,之后這些人憑借海上生存的經驗和受到短期發財致富欲望的驅使,很快做起了海盜。所以17世紀開始,海盜的數量龐大,而且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先進的武器。例如辛格頓的船上就有分工明確的水手、炮術長、外科醫生、工匠和木匠;從他們獲取生活資料和防御蠻夷和野獸使用的火藥、槍支、大炮也可以看出當時海盜的武器設備已經較為先進。由于海盜肆無忌憚的搶掠,各國船主和大使怨聲載道,1608年,詹姆士一世聯合議會設立委員會,專門調查海盜的活動。1616年后,英國海軍大力打擊海盜。1701年,英國政府頒布嚴格打擊海盜的法令。于是,海盜的命運開始發生轉折。
《海盜船長》創作于1720年,而此時英國政府已經下令絞殺海盜。笛福以其敏銳的社會洞察力預見了海盜之路注定無法走向光明,真正能使英國走向繁榮的是商業貿易。所以,笛福刻意塑造了完美的教友派教徒威廉這個人物,幫助辛格頓完成從海盜到商人的轉變。威廉·華爾透斯是一名外科醫生,同時也是一位買賣精明的商人,他總會在關鍵時刻幫助辛格頓解圍。當辛格頓掠劫的財物足以填滿最貪婪的溝壑時,他決定不再做海盜,搖身一變轉為商人。而他打算把搶劫來的歐洲貨物賣給中國人時,由于沒有貿易經驗,他擔心他們不愿意與之交易,威廉告訴他:“凡是一個人,他的利害關系約束著他非對我們規矩正直不可,那我就馬上對他信任,有如信任一個受道德原則約束的人一般。”在經驗豐富的商人威廉的引導下,雙方很快建立商業信任感,辛格頓成功銷售六十來噸香料和兩百多包歐洲貨物。這讓他意識到不靠野蠻暴力的手段,掌握商業貿易的法則依然可以獲得財富。最后,辛格頓威廉的幫助下,擺脫了海盜的身份,變成一名文明虔誠的英國商人,過著富足的生活。在此過程中,威廉除了充當海盜的“引路人”這一角色,其身份也有深刻的寓意。他是教友派的教徒,而“教友派”是1650年意大利人喬治·福克斯所創的一個基督教宗派,反對使用強力,自稱為“教友會”,這反映出笛福不贊同再使用蠻力掠奪,應該以文明人的方式獲取財富。他以此來啟示海盜們:目前國家的局勢已經發生大變,如果繼續強取豪奪,就會陷入黑暗的深淵;如果像辛格頓那樣誠心懺悔,采用經商的正當手段獲取利益,將會過上幸福的生活。即使辛格頓做過那么多蠻橫殘忍的事情,最終依然全身而退。英國將從海盜之國轉為商業之國,只要順應英國社會的發展,放棄海盜的身份,必然可以重新踏上光明之路。
18世紀的英國處于工業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英國社會各方面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其中英國性的構建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笛福也在小說中參與了英國民族身份的討論,通過對比英國與其他歐洲民族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方面的差異,彰顯了英國清教徒的文明虔誠。從海盜到商人的轉變,體現出笛福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認識,英國未來發展方向的超前意識。從歷史和社會意義上來說,海盜傳統到商業貿易的轉變影射出英國不同時期經濟、文化的變化與進步,也寄托了笛福本人對英國從海盜國家向商業國家轉型的期望。
參考文獻
[1]Ackroyd, Peter. 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2.
[2]Emerson, Ralph Waldo. English Traits[M]. Boston: Hard Press, 1856.
[3]Langford, Paul. Englishness Identified: Manners and Characters1650-1850[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Scruton, Roger. England: An Elegy[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0.
[5]Smith, Zadie. White Teeth[M]. Harmondsworth: Penguin, 2001.
[6]Wilson, Kathleen. The Island and Race: Englishness, 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2003.
[7]陳兵. 笛福與現代英國民族身份構建[J]. 國外文學, 2020(01):51-60.
[8]丹尼爾·笛福. 海盜船長[M]. 張培均、陳明錦譯.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
[9]郭海霞. 英國海洋小說中的海盜書寫與重構[J]. 外國語文,2018 (05):81-86.
[10]李煒. 海盜與1588年英西海戰[J]. 安徽文學(下半月),2008(05):190.
[11]蘇珊·羅納德. 海盜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和大英帝國的崛起. 張萬偉、張文亭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2]王卉、姚振軍. 《白牙》中對“英國性”的重新定義. 世界文學評論[J]. 2010(2):78-83.
[13]約翰·赫斯特. 極簡歐洲史. 席玉蘋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14]楊明卓. 海盜對于近代英國的貢獻[J]. 重慶與世界,2018(10):98-99.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