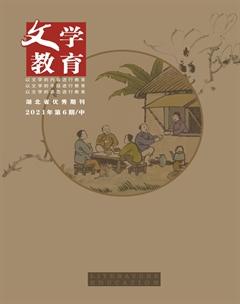《世界的詞語是森林》中的主奴關系倒置
沈佳靜
內容摘要:美國科幻小說作家厄休拉·勒古恩的代表作之一《世界的詞語是森林》(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講述了被地球殖民成為“奴隸”的艾斯珊人如何通過暴力抗爭推翻地球殖民者“主人”統治的故事。艾斯珊人與地球人“主人/奴隸”的關系倒置折射出殖民侵略活動對殖民者和受殖民者帶去的雙層影響。因此,本文擬從后殖民主義視野中的主奴關系倒置入手研究《世界的詞語是森林》中主人和奴隸的轉換關系,分析兩個互為“他者”的文明形成主奴關系的表征以及其權力話語倒置的轉化過程。
關鍵詞:《世界的詞語是森林》 厄休拉·勒古恩 主奴關系 后殖民主義
《世界的詞語是森林》(以下簡稱《世森》)是美國科幻小說作家厄休拉·勒古恩代表作“黑暗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厄休拉·勒古恩以未來書寫當下,將對現實的隱喻投入到她的科學幻想中來。這部創作于1968-1969的小說中充斥著對越南戰爭的反戰情緒以及對美國在越南開展毫無人道主義屠殺的諷刺,作者敏銳地洞察到了殖民擴張對第三世界國家民族性的影響。哈羅德·布魯姆對勒古恩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她超越了托爾金,將奇幻文學提升到經典文學的地位,因為她筆下的追尋者從未拋棄我們必須生活的世界,一個以弗洛伊德式現實為原則的世界(Bloom 9)。
在地球人的外星殖民活動中,地球人與艾斯珊人形成了主人/奴隸的關系范式,這正是后殖民批評長久以來致力于消解的對象。在《后殖民身份認同話語研究》一書中,羅如春教授結合黑格爾哲學中的主奴辯證法以及薩特的“暴力凝視”理論闡釋了“他者”在“主體自我”的壓迫下產生的主奴認同關系,他指出“主體之間的關系并不完全確定,而是隨著凝視位置的不同而發生轉移甚至倒置——變成了一種互為主奴的關系(49)。” 因此,本文擬從后殖民主義視野中的主奴關系倒置入手研究《世界的詞語是森林》中主人和奴隸的轉換關系,分析兩個互為“他者”的文明形成主奴關系的表征以及其權力話語倒置的轉化過程。
一.“他者”的奴隸
“他者”的定義是“被主體壓抑與排斥的異質因素或者是人為構建起來的他性(otherness)(羅如春 42)。”值得一提,隨著科幻小說批評的進一步發展,學界逐漸關注到來科幻小說中開拓宇宙空間的情節與后殖民主義批評之間的關系。張娜(2017)指出“科幻小說與后殖民主義研究都聚焦于空間的接觸和變化帶來的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轉變”,并且在想象中常伴隨著與非地球人的他者接觸,“將殖民行為移植到不同的時空中去,后殖民文化概念常常通過異化的他者形象得以再現(79)。”因此,在科幻小說中,在占據主導地位的“自我”角度下,“他者”就通過隱喻置換為非地球人的外星人。《世森》在結構上就巧妙地展現了地球文明與艾斯珊人的二元對立關系。勒古恩采用非全知視角的方式,一個章節即一個人物的獨白。讀者只能在人物有限的視角以及個人的獨白了解各自所代表的文明。全書共8個章節,其中地球人代表戴維森占據了1,4,7三個章節,艾斯珊人代表塞維爾則占據了2,6,8三個章節,而地球人中研究艾斯珊文明的科學家留波夫則在剩余的第3和第5章節。這種寫作方式將地球人和艾斯珊的心聲放大,讓讀者深切感受到戴維森的傲慢狂暴,塞維爾所代表的森林文明睿智與理性,以及留波夫作為中立知識分子游移與軟弱的一面。在人物內心獨白的描寫下,人物本身敘述的掩蓋性以及處于相對立的立場無疑放大了兩個文明之間的對立與沖突。這一點在地球殖民軍團代表戴維森上尉獨斷的敘述中顯得尤為明顯。
戴維森上尉的語言沒有灰色的模糊地帶,他將一切事物視為自我世界與他者的對立。在他眼中艾斯珊人是一種“身高一米、渾身長滿綠毛”智力低下的非人類生物。他輕蔑地將他們命名為“睽嗤”(creechie),把他們比作“綠猴子”,“老鼠”和“蛇”,輕視為沒有生命的機器人,低賤的蟲子。他抱著延續地球文明的崇高目標將自己稱為“世界馴服者”,將其他文明視為異類是自己馴服的對象。于是,以他為代表的地球人大肆奴役愛斯姍人,將它們視為自己的奴仆讓他們成為為自己提供生活服務的“信差、挖掘工、廚子、清道夫、男雜役、女仆”并將他們偽稱為“自愿本土勞工人員(115)。”身為奴隸的艾斯珊人則無法言說自己的聲音,只能被動的順從。諷刺地是,盡管戴維森不承認艾斯珊人與自身文明的同等性,卻強奸了一名被自己認為是非人類的艾斯珊女性。
“自我意識對于現象世界最基本的關系表現為欲望,是一種占有并否定對象客體的純粹意志”,這種欲望也是主奴意識的起點,即通過否定他者來承認肯定自身(羅如春 43)。以戴維森為代表的人類就采取一種以“殺戮、強奸、驅逐和奴役”的暴力表征的方式鞏固自己的主人地位。強迫艾斯姍人對自身的認同,滿足自身殺戮與擴張的欲望。這種暴力的方式為艾斯姍人帶來了極大的苦難,使他們處于長期恐懼中,進入了一個“充滿流亡,恥辱與痛苦”的壞時代。主人和奴隸的不平等關系由主人利用恐懼的威懾建立而來(46)。在語言不通的事實面前,艾斯姍人無法言表的痛苦,在戴維森眼里都是艾斯姍人木訥,蠢笨的象征。戴維森以主人的姿態任意處置著艾斯姍人的生死,只有他最為懂得如何驅使這些“懶惰”的奴隸工作,在營地里他為其他馴服艾斯姍人的下屬建議到給他們注射迷幻劑,因為“他們對這些東西怕的要死(14)。”通過生理與心理途徑的威懾,戴維森樹立起了自己身為主人的意識。然而,這種主人奴隸的對立在艾斯姍人的反抗下顛倒了過來。
二.主奴關系倒置
主人和奴隸的關系并不是固定靜止的而是處于辯證的否定之中。當主人得到奴隸的認同時,實際上得到的是一個“作為非人沒有有價值的物的‘承認”,“而在主奴關系建立后,主人就退化成了一個物的存在,因為他驅使奴隸的勞動僅僅只是滿足自己的自然本能。”地球人認為艾斯姍人是“一個不善攻擊的亞種”,是低劣的非人生物,他們“沒有能力殺人,無論是殺人類還是殺自己的同類(58-60)。”因此,在人類獲得殖民地的統治地位之后,地球人疲于對艾斯珊人的管理,認為艾斯珊人沒有攻擊性,在滿足自己的原始本能后,地球的殖民軍隊沉溺于迷幻劑以及單純期待著女人的到來以滿足自己的原始欲望。其身為“主人”的存在從而被消解了。
地球人對艾斯珊人的膚淺認知也因“神靈”塞維爾的出現而被打破。塞維爾也是一名在殖民營地中的奴隸,他特有的聰慧使他快速掌握了人類的語言,他與科學家留波夫交好,協助留波夫進行對艾斯姍星球的研究。他目睹了自己的妻子被戴維森強奸之后死去,在憤怒悲傷的沖擊下,奮起反擊,帶領九百位艾斯姍人反殺了殖民營地內的兩百零七位人類殖民者并以艾斯姍人獨有的唱歌方式羞辱了戴維森。盡管奴隸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成為主人的物,但他仍然是一個自我意識,他注定要揚棄自己的依附性成為獨立的意識。艾斯珊人自身的文明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社會,與他們所居住的森林一樣亙古恒定,“他們是靜態、穩固、整齊劃一的社會。他們沒有歷史。他們完全融為一體,沒有任何進步(68)。”而對地球殖民者暴力統治的接納與反抗,等同于他們對自身文明的揚棄。反抗者塞維爾教會了艾斯珊人使用暴力,他們在一天夜里偷襲了一個殖民營地,為了防止地球人的繁殖,殺害了所有的女人,俘虜了包括最高指揮官在內的殖民地軍人,將他們如同奴隸一樣關入了囚禁營,“睽嗤曾經的圍欄(133)。”此時,主人與奴隸的關系發生了轉換,艾斯珊文明與地球文明互不相見的隔膜被打破,地球人真正的開始認識到了這個身高不足一米的“綠猴子”。然而,暴力的反抗也帶走中立知識分子留波夫的生命,兩個文明得以溝通的橋梁不復存在。遭遇苦難的現實使艾斯珊人報以仇恨偏見的眼光看待地球人,他們使用同樣的方式奴役地球人,將他們關入擁擠的棚屋,不提供清潔的水和充足的食物。當新的主人和奴隸的關系構建完成后,艾斯珊人身為主人的獨立性也因此而消解。他們采用的暴力手段也改變了他們自身的民族特性,即使塞維爾取得了勝利,面對大肆屠殺人類女性的本族人,處在殺戮中心的他開始質疑所處的這一切,“我把羽曼們說成時瘋子。我自己是不是瘋子呢?(141)”他也以敏銳的直覺,預見了之后本族之間互相屠殺的可怕后果,之后一直處在慚愧悲傷的情緒中,卻無力改變現狀。
在黑格爾這里,奴隸的身上潛藏著無限的生命力,它是一個不斷致力于創造和解放的勞動者與奮斗者的形象(羅如春 48)。當艾斯珊人接納了地球殖民者的暴力統治,并應用它反作用到自身文明身上去,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一方面,艾斯珊人也開始走上了地球人殘忍殺戮的老路,失去自身文明那些溫和理性的成分,但是另一方面,艾斯珊人所學到的暴力手段也使他們一成不變的文明得以發生激蕩,產生了進化的可能性。當然,這種暴力帶來的創傷是雙重性的,它不僅給艾斯珊人帶來了無盡的苦難,對殖民者地球人而言也是一段揮之不去的噩夢。
《世界的詞語是森林》作為一個特殊時代背景下誕生的科幻小說,它延續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后殖民主義語境下對民族身份認同的思考,用科幻小說對未來之景的暢想書寫當下的故事。它講述了一個在地球人殖民壓迫下成為“奴隸”的艾斯珊人利用暴力反抗的方式顛倒了地球殖民者“主人”的身份,當然,主奴權力關系的轉換也使艾斯珊人喪失了自己本民族溫和、愛好和平民族特性,引入了“暴力”這一后殖民影響因素。厄休拉·勒古恩雕琢了這面在宇宙深處的鏡子,折射出她對現實越南戰爭的反戰思考,批判了美國發動的這場毫無人道主義精神的戰爭。
參考文獻
[1]Bloom, Harold. Ursula K. Le Guin[M].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2]厄休拉·勒古恩.《世界的詞語是森林》[M].于國君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
[3]羅如春.《后殖民身份認同話語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4]張娜.“特德·蔣科幻小說中的后族裔敘事”[J].《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17):78-84.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