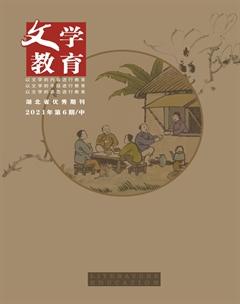在《王先霈文集》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首先,祝賀王先霈老師八卷本文集的出版!同時,我也代表王先霈老師的粉絲,感謝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能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推出這套300萬字的皇皇巨著,得以讓讀者能夠完整、全面地了解王先霈老師這一生的主要研究與創作成果。
接到周揮輝社長送我的王老師的文集,我立即想起曉蘇的《桂子山上的樹》。曉蘇曾經以這個題目在華中師大畢業生典禮儀式上做過一次高水平的演講,其中提到了王先霈老師,稱他是桂子山上眾多樹木中的一棵精神之樹。我沒有曉蘇那么幸運,能夠直接聆聽王先霈老師傳道、授業、解惑,而且能夠在沒有電燈的夜里,還能聽到王老師精彩至極的演講。我想象那時在黑暗的教室里,一定是有足夠吸引人的天籟之音,才能讓這批年輕學子如醉如癡,流連忘返。但是,我認為,作為學者、教授、作協主席、出版家的王先霈老師,不僅僅是桂子山上的樹,而是荊楚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一棵大樹。這是一棵扎根在中華大地上,汲取了五千年文明和東西方營養的知識之樹,智慧之樹,是佛陀身后的那株菩提樹。它枝繁葉茂,不僅為樹下的學子遮風擋雨,而且以它豐碩的果實,在中華大地上繁衍了一片蓊蓊郁郁的樹林。
下面,我先來匯報閱讀王老師文集的體會。
王老師文集是對其一生學術成果的系統梳理與全面集成,內容豐富、全面,可謂是博大精深。其中包括文學批評理論、中國古代小說理論、中國古代藝術心理研究、文藝心理學、小說技巧的研究,同時,還有作家作品批評,以及王老師創作的散文隨筆等。王老師著作的整體出版不僅是對他一生研究與創作成果的全面肯定與總結,而且對當代文學理論研究、中文學科建設以及創作實踐,都有著非凡的意義。王老師的書雖然過去我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工作時,拜讀過他的《徘徊在詩與歷史之間》《小說大辭典》等,在報刊上閱讀過他的一些文章,但這一次是系統地學習。不過由于時間關系,如果說學習,也只能稱得上是淺嘗輒止、浮光掠影。
一.王老師提出的圓形批評理論,對于文學批評學理論的建設,文學批評學學科的建設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王老師針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批評理論的眾聲喧嘩,對孤立的、片面的、直線的文學批評提出了批評。1992年發表了《建設“圓形”的文學批評》一文,這標志著他正式提出了頗具開拓性、建設性的新的批評理論范式——“圓形”批評。
何為“圓形”的文學批評?王老師在《建設“圓形”的文學批評》一文中寫道:“相對于以偏取勝的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線型思維支配下的文學批評,相對于片斷直感的、缺乏確定內涵的散點型思維支配下的文學批評,我們期盼的是感性與理性融合的、適合文學的審美特性的文學批評,我們稱之為圓形批評。……這里所說的‘圓形,是一種批評觀念,是對文學批評的感悟性與思辨性的一種體認,對文學批評的對象的審美性質的體認;它又是一種批評原則和一種闡釋方式,貫穿在批評活動之中,貫穿在文學批評主體對批評對象的把握過程之中,貫穿在主體思維活動的形態之中。”王老師的闡釋,即要求文學批評克服要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線型的批評觀念,通過批評主體的自諧及與不同批評流派、不同批評風格的互諧使文學批評走向一種批評的“圓形”境界。
因此,這種“圓形”批評理論對原有的社會歷史批評,或者是生吞活剝西方文藝理論或者哲學思想的批評,是一種反撥,或者說是完善。王老師的圓形批評理論,是新時期文學批評發展歷程中文學理論的重要收獲,得到了學界的肯定。有一篇發表在《文藝報》上的訪談,標題上《在中西文論的交切點上尋求創新的突破口》,這個標題基本概括了王老師研究的主要特點。他所倡導并不斷完善的圓形批評理論,不僅是文學批評的一種觀念、方法,也是一種哲學的思維方式,還是一種批評家主體所要達到的人生境界。王老師先后出版了《圓形批評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圓形批評與圓形思維》(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建設“圓形”的文學批評》(2016年6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等專著。所以我認為在王老師的文學理論大廈的建構中,最具理論創新意義,就是他創立的圓形批評理論。雖然已有些碩士以此作為論文研究的方向,并有不少研究性文章,但還需要學界深入研究并用于批評實踐,借以豐富我們的文藝批評理論的寶庫。
二是文藝心理學理論與文藝學教材的建設,王老師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86年8月,王老師與范明華合作,在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出版了《文學評論教程》,這是國內較早的一部文藝學教材。1988年,華師出版社又出版了王老師的《文學心理學概論》,后又改為《文藝心理學讀本》再版。2006年,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一書。同時,他還帶領華師文學院的老師們編寫了一系列文藝學系列教材,為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較早成為一級學科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國內的專家對王老師的文藝心理學研究曾有過很高的評價。童慶炳先生稱其文藝心理學研究“給中國古代藝術心理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中國文學理論和國學研究的一次重大收獲。”其研究具有“民族特色、充滿魅力;史論結合、系統警辟;以西釋中、功力深厚”。王老師研究論述中國古代文藝心理思想時,注意用現代西方學者和作家的相關論述來闡述中國古代先哲藝術心理思想的價值與意義。他涉獵廣泛,如在《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書中就引用了席勒、阿圖爾·叔本華、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皮亞杰、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布恩、埃克斯特蘭德、安東·埃倫茨維希等一系列大家的文藝心理學觀點,以此來證明中國傳統的文藝心理學思想的學理性與現代意義。
三是關于小說理論與技巧的研究。王老師對于小說理論與技巧的研究,用力尤深。他的20余種專著中,有四分之一是關于小說理論與技巧的。他于1986年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小說技巧探賞》,1987年與張方合著,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徘徊在詩與歷史之間》,1988年與周偉民合著的《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1991年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小說大辭典》,1992年在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說序跋漫話》。除此之外,他的其它著作中,還大量地談到小說的理論與創作。王老師的小說研究既涉及古代小說理論,也旁及中外小說不斷變化的創作實踐。他的小說理論研究,既有學理性的理論分析,也有文本解讀式的定性定量技術分析。他對中外小說技巧的分析與總結,不僅可以用于文學欣賞與文學批評,對于小說家而言,也是很有價值的學習文本。我十分驚訝王老師能夠花這多時間閱讀如此多的古今中外小說。他的上百萬字的《小說大辭典》,便是他多年浸潤于小說世界的證明。所以,王老師的小說理論研究,與其它的學者比較,更有價值的是他對于文本的仔細解讀與分析,以及從中總結出的創作規律。很遺憾我當年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時,沒有讀到王老師的這么貼地氣有實用價值的著作。
四是關于湖北文學創作的批評與指導。王老師的文集中,有一卷幾乎都是關于湖北作家作品的評論和序與跋。他1986年第2期發表在《文藝論壇》上的《親切感和深刻性》是評論方方小說的,是目前收錄在文集中最早的一篇。那時方方剛剛大學畢業不久,王老師的職稱也還只是一個副教授。但王老師注定要與湖北的作家打交道,這是不是預示著王老師后來要成為湖北文學創作的引路人,成為作家協會的當家人?湖北省凡是有影響的作家,王老師差不多都給予了提攜與引導。包括他的很多篇序與跋。有些是有影響的作家,有些還是一些無名之輩。王老師都不厭其煩,認真閱讀他們的作品,找出其中的優長之處,給以褒獎。我想,湖北的文學創作在全國取得的地位,與王老師這一代理論家的點撥是分不開的。王老師這一類的文章,無論是作家作品的評論,還是序與跋,都如促膝談心一般,娓娓道來,將自己閱讀后的感受與作者和讀者交流,其實,文中有不少真知灼見。雖然王老師采取的是商討式的方式,但作品的優缺點,王老師并不諱疾忌醫。
當然,王老師的文集中,還有關于詩學的,關于佛學的,關于美學的一些論著,因為時間關系,只能留待我以后認真系統學習。當然,我期待著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夠系統、深入、全面地研究王老師的學術思想與貢獻,這對于文藝理論的建設以及中文學科的建設,都有深遠意義。
在王老師文集的第八卷中,王老師寫徐遲,引用了《論語》中子夏的話:“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我覺得,子夏的這段話用來形容王先霈老師也十分恰切。王老師溫文爾雅,不苛言笑,讓人覺得不好接近,其實,只要與他有所交往的人,都會留下他待人溫和可親的印象。另外,王老師無論是擔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省作協主席,出版社總編輯,都一直堅守知識分子的原則性與良知,從不茍且俗流。用顧炎武的話解釋,是非觀很強。所以,我們說王老師也是一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君子、長者。他不僅屬于桂子山,而是屬于湖北,屬于中國的知識界。
王老師不知不覺已經八十有余了。在我的印象中,王老師這棵桂子山的樹一直是臨風的玉樹,瀟灑、挺拔,始終充滿青春的氣息;也是一棵雖有經年但仍葳蕤生光的大樹。這棵樹枝繁葉茂,伴隨著歲月的律動,年年為人們送來春的生氣,秋的豐富。我想,這棵樹不僅生長在桂子山上,還會伴隨著王老師的八卷大作,永遠扎根在讀書人的心田中。我祝愿王老師身健筆健,讓我們能繼續讀到他睿智、充滿靈氣的新作。
周百義,河南信陽人,作家、出版家。曾任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長江出版集團總編輯、長江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現主持編纂出版1600冊《荊楚文庫》大型文化叢書。主持策劃的有《二月河文集》《歷史小說大系》《九頭鳥長篇小說文庫》《新時期報告文學大系》等。責任編輯系列長篇歷史小說《雍正皇帝》《張居正》等。本人寫作并結集出版的有:小說集《竹溪上的筍葉船》《山野的呼喚》《黑月亮》等,古籍整理《五經七書譯注》《白話勸忍百箴》《預知·預兆·預見》,出版研究專著《出版的文化守望》《書旅留痕》《書業行知錄》等。有《周百義文存》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