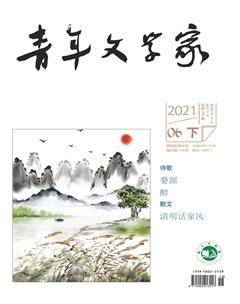《別名格蕾絲》的服飾書寫
李朋 張雅美
服飾是人們生活必需品,進入文本的服飾可以視為符號傳達更多信息。《別名格蕾絲》是阿特伍德代表作,作品講述了19世紀一樁駭人的謀殺案。作為女性主義作家的代表,阿特伍德擅長在小說中穿插大量的服飾描寫來達到文本意義的實現。在《別名格蕾絲》中,服飾書寫完善了小說敘事策略并升華了作品主題。
一、服飾書寫與敘事表達
小說雖然是虛構性質的藝術,但與現實生活相似,即時間與空間決定小說的存在方式。(申丹,8)《別名格蕾絲》使用多種敘述模式,將回憶與現實交叉并聚焦于具體空間。通過服飾書寫的研究,流動的時間與變化的空間清楚顯現并完善小說的敘事邏輯。
(一)服飾書寫與流動的敘事時間
敘事與時間的關系是敘事學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小說《別名格蕾絲》中故事情節推進并未按照時間順序,角色服飾變化從側面推動敘事時間的發展。
在文本中,服飾作為符號傳遞更多信息。服飾是展示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人物服飾的變化可以作為判斷時間變化的輔助工具。(梁琨,124)幼年格蕾絲生活拮據,衣服相當破爛。家庭困窘導致其家庭迫不得已移民加拿大謀生。她也處于懵懂狀態,對社會復雜性一無所知。在帕金森夫人家工作時,夫人讓她穿得像樣兒點,因為她看起來像叫花子。穿上合適的新裙子,格蕾絲就顯得體面些。在好友瑪麗的幫助下,格蕾絲心智逐漸成熟,敢于反抗父親并具有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然而,格蕾絲和瑪麗在加拿大度過了第一個寒冷的冬天之后,瑪麗不幸去世。摯友的逝世使格蕾絲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格蕾絲輾轉來到了金尼爾先生家,南希的華麗服飾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格蕾斯在南希身上尋找到瑪麗的影子。初始兩者的關系很好,南希會借衣物給格蕾絲穿。格蕾絲也很羨慕南希的華麗服飾,她有時候也想:“如果我能有兩只螢火蟲在我耳朵上做耳環,我根本不會對南希的金耳環眼饞的。”(阿特伍德,184)。而當格蕾絲入獄之后,她身穿獄服來展現自己犯人的身份。通過服飾書寫,小說的時間線條理清晰并展現了格蕾絲成長過程的悲慘遭遇。
(二)服飾書寫與變化的敘事空間
敘事空間是小說敘事的重要因素。在變化的空間中,服飾書寫聚焦空間重要角色來表現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等方面,并在小說敘事中承擔更多功能。對不同人物在空間內服飾描寫的詳略程度是實現人物聚焦的方式。敘述空間人物的聚焦,可作為小說家變換感情色彩的有效工具。
喬丹醫生剛出場時,作者通過格蕾絲的視角詳細描寫了他的穿著。此刻敘事空間聚焦于喬丹,引導讀者通過服飾思考新角色的特征及推動情節發展。喬丹穿著得體,戴著一條金表鏈,彰顯出他具有一定的財富和身份地位。但是,并不華麗的衣服也隱喻喬丹醫生家族破落的現狀。
格蕾絲初去金尼爾先生家,她路上遇見了眾多人物,而敘事空間首先聚焦于南希。作者詳盡描繪了南希的穿著,她身著華麗而又講究。而接下來,視角聚焦于男仆麥克德莫特,他穿著簡陋而又隨意,展現了其暴躁的氣質。在相同空間內,作者對他們的服飾都進行了詳盡描寫,空間聚焦于兩位穿著存在巨大差異的人物。兩人雖都為仆人,但南希的穿著更為華麗和優雅,使得麥克德莫特的服飾看起來似乎簡陋而又隨意。通過服飾的差別可以窺見兩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心理狀態。
二、服飾書寫與主題升華
服飾書寫不僅具有文本敘事功能,也升華了作品主題。小說中各個元素如食物和疾病的書寫都是為了彰顯作品主題,服飾書寫亦是如此。越是細致的服飾描寫,越能彰顯主題含義。阿特伍德作為加拿大女性作家代表,她的作品經常以女性主義和反映社會矛盾為主基調。
(一)女性主義的表達
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她目睹女性遭受不公正對待的經歷,促進了她的女性意識發展。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推動她的女性意識逐漸成熟,并以此來思考兩性差別。在小說中,19世紀的女性依附于男性,缺乏“話語權”,在思想觀念上完全地接受男權中心主義的“規訓”。小說中體現阿特伍德女性意識的方面頗多,不僅揭露了女性處于“被支配”的社會地位,并揭露了男女二元對立的矛盾。
身處上流社會的莉迪亞小姐和漢弗萊夫人處心積慮想要得到西蒙醫生的青睞,心甘情愿做他的附庸。莉迪亞小姐身穿緊身抹胸衣來顯示苗條身材,而漢弗萊夫人更是每次“遇見”喬丹醫生則穿著一身黑色長裙,試圖誘惑喬丹醫生來達到自我價值的實現。小說中,女性角色的服飾選擇為了取悅男性而并非自我身體的舒適感。女性作為弱勢群體,只有滿足男性主體需要才是社會主流,才是“正常”的女性。身處上流社會的女性尚且無法擺脫男性的束縛,更遑論底層的妓女。作者多次通過格蕾絲的視角刻畫了妓女的悲慘生存狀態,她們只有打扮花枝招展、穿著華麗才能吸引更多男性顧客來維持生活。她們是男性的附庸和男權社會的受害者,諷刺的是:更多男性的光顧,她們才能維持生活。這種復雜而又矛盾的心理狀態正是源于當時社會男女不平等的現實。女性作為他者和邊緣者,只能依附于男性主體才能生存。女性將自己“包裝”好,作為商品供男性挑選,商品化和物化是當時女性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阿特伍德通過服飾描寫書寫了當時社會女性的悲劇人生,揭露了男權至上的社會問題。
(二)社會秩序的反抗與消解
服飾作為身份地位的象征,體現出階層之間的差異。阿特伍德在小說中,有意通過服飾差異性將人物劃分為不同群體,來展現激烈的階層矛盾。小說中的服飾書寫一方面符合當時社會基本情況,是社會秩序的體現。另一方面,阿特伍德詳盡地描述格蕾絲和麥克德莫特在作案后的服飾變化,也旨在表達自己對社會秩序新的理解。
服飾作為身份地位的象征充滿著社會內涵,彰顯出階層間的巨大差異。小說中的莉迪亞小姐和管家南希是一類群體,她們的穿著體現了上流社會的奢華和精致。華麗的裙子和貴重的金耳環只是她們的普通裝飾。格蕾絲和麥克德莫特是一類群體,格蕾絲去金尼爾先生家里做女傭時,身穿的是過時的印花棉布裙,隨身攜帶的兩條襯裙,其中一條是縫補好的,而另一條則短到并不合身。麥克德莫特則穿著十分隨意,襯衣袖子卷著,領口敞開,褲腿塞在靴子里。兩者的穿著展現了下層社會的簡陋和粗俗。服飾的差異性也是當時社會階層之間矛盾的展現,不同的服飾穿著符合當時的社會秩序規范化的標準,底層和上流社會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界限。
服飾是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征,但阿特伍德在作品中有意地消解服飾的象征意義。作者通過格蕾絲和麥克德莫特作案后的詳盡的服飾書寫,使得服飾的傳統象征意義被消解并展現出新的內涵,這也是對傳統社會秩序的消解與反抗。
格蕾絲和男仆麥克德莫特在作案之后并沒有立即驚慌失措地逃離,而是趁機搜刮金尼爾先生的財富。然而,不約而同的是,他們換上了管家南希和男主人金尼爾先生的衣服。小說中麥克德莫特和格蕾絲穿上男主人和管家的衣服旨在打破傳統的社會身份、地位、階層界限。服飾符號作為身份地位的象征逐漸模糊,失去了其原有的象征意義。
阿特伍德在小說中一方面通過不同群體的巨大的服飾差異展現社會存在的尖銳矛盾,即上層和底層之間的對立矛盾。另一方面,通過格蕾絲和麥克德莫特換上女管家南希和金尼爾先生的服飾模糊階層之間的界限,完成對傳統秩序的顛覆和僭越。同時,以服飾來劃分群體展現階層之間的對立(上層和下層)和通過不同群體服飾的互換來模糊原有的階層界限趨向平等化。這也是阿特伍德本人對當時社會問題的反思并希望通過平等化來解決尖銳的二元對立的階層矛盾。
三、 結語
服飾書寫賦予了服飾新的功能。阿特伍德在作品《別名格蕾絲》中,借助服飾書寫這一手段,展現了服飾進入文學作品中所具有的敘事功能。通過服飾書寫展現了時空的變化也描繪了當時的社會風貌。此外,阿特伍德也借助服飾書寫來升華作品主題:對女性命運和社會階層矛盾的描繪與反思。服飾書寫已經成為阿特伍德作品的明顯風格,立足于服飾,阿特伍德完成了對加拿大歷史的書寫,體現了她個人對女性群體和國家的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