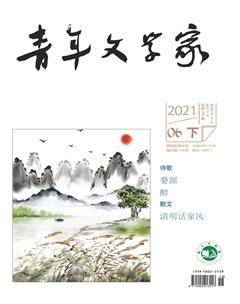蘇洵易學與散文創作
馮軼群
北宋時期,承繼漢唐學術之遺韻,易學與散文學成果斐然,交相輝映。蘇洵作為三蘇蜀學的開拓者,在易學與散文領域頗有創獲。正是這樣一位被后世敬仰的思想家、文學家,其早年卻只顧游山玩水,將科舉功名忘卻腦后。年長,幡然醒悟,曾自敘“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后名落孫山,更為奮發圖強,“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易學蘊含于六經百家之中,蘇洵與《易》結緣當在此時。而究其治《易》的狂熱期,當屬晚年,“十年讀易費膏火,盡日吟詩愁肺肝”“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余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可見易學求索伴隨蘇洵一生,其習《易》甚為用力且對成果頗為自信。蘇洵一生治《易》的心得體會,自然融入文學創作理念之中,審視其散文創作,自然會發現易學思想的光芒。
一、宇宙生成論
從古至今,闡發宇宙生成論的各家各派不勝枚舉,因而豐富了中國古代哲學體系。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打破了天為一切之最高主宰的觀念。稷下道家繼承老子思想,主張“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呂氏春秋》則秉承老子宇宙生成論思想,認為“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名,謂之太一”且“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太一”還有另外一個稱謂,即“一”,正所謂“一也齊至貴,莫知其端,莫知其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太一”同“一”一樣,均是萬事萬物的本原。
蘇洵一脈相承,在解《易》過程中逐漸形成獨特的宇宙觀。《易》言“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對立統一,合之為道,為萬事萬物生成之根本。蘇洵承繼這一理論,認為“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于一,而兩于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一”即道,“兩”即對立統一的概念,由此化生萬事萬物。“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及其用息而功顯,體分而名立,則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其中,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乾坤、男女皆為對立統一之概念,蘇洵便是借助對立統一樸素辯證法的方式,對道進行闡釋,他認為“道”存于萬事萬物之中,不同角度進行審視,具體表現雖有不同,但本質無異。
“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蘇洵認知觀念中的“道”是運動的、變化的,因此對道的形態做了闡述:
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也,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于道。”
這里的水非實物,而是形態的象征,即“無常態”。水隨外界變化而自然變化,散落于萬物之中,無時無刻不隨萬物形態而轉化。蘇洵將“道”譬喻為水,最為生動。
蘇洵以道為宗的思想,在其子蘇轍的著作中彰顯得更為明確,蘇轍言:“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以道為產生萬物的本原,萬物非道不生。換言之,從蘇轍的宇宙生成論思想中可以捕捉到其父的影子,用以佐證蘇洵思想,并非妄言。
二、義利相合觀
孔子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儒家傳統義利觀主張“重義輕利”。而《易》中明確提出了新的義利關系,認為“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與利,二者并不沖突,當相輔相成、互相成就。蘇洵對《易》所推崇的義利觀極為贊許,他認為義利相合。
“利之所在,天下趨之。”蘇洵未將“利”看作阻礙“義”形成的矛盾對立體,因而肯定了“利”的存在合理性,并獨具慧眼,認為妥善用“利”可以產生積極的社會意義。蘇洵認為圣人之所以可以奔走于天下,靠的就是“執其大利之權”,作為統治者,應以利統治萬民、管理國家。不一而足,蘇洵在建議皇帝積極納諫時所采用的比喻,就很能體現其義利觀的現實價值。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后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諫焉。
針對不同性格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統治者恩威并施,義利并重,將“義利、利義相為用”,則“天下運諸掌矣”,堪稱蘇洵政論思想的獨到見解。
“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蘇洵既然認為義利相合才是正確的思維觀念,那將“義”與“利”分開,則并非明智之舉。據此,蘇洵提出了“徒義”的概念。“徒義”即孤立的、片面的義,沒有利相輔的義。蘇洵以伯夷、叔齊為例,認為二人為義獻身的行為之所以沒有得到天下之人的悲憫與同情,沒有得到天下之人的救助,是因為“徒義之罪也”。徒義是“戕天下之器”,會“拂天下之心”。
蘇洵在鼓吹義、貶斥利的傳統思潮與社會氛圍之下,提出了更為理性的義利相合觀,其并非不尚義,只是不徒義而已。
三、趨吉避兇的憂患意識
《易經》是誕生于西周時期的卜筮之書,卜筮是古代占問吉兇的方法,旨在趨吉避兇、妥善行事。故此,“吉”“兇”是整部《易》的關鍵字眼,并且無處不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上六,比之無首,兇”,試舉幾例,窺一斑而知全豹。吉、兇顯現自然可以依循行事,但吉、兇未現又該當如何呢?因此,能夠預先知曉萬事萬物發展趨向,做到“知幾”,最為重要。《周易·系辭下》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是吉兇禍福的預兆,“知幾”就是了解事物發展的趨勢,而做到有備無患。
治《易》有所得的蘇洵,自然深諳趨吉避兇之道,未雨綢繆,繼承了易學“知幾”的思想,針砭時弊,于散文中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
宋王朝“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然而世人皆認為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養尊處優,緣由之一便是“見其安不見其危”。蘇洵則憑借清醒的頭腦和對家國的熱愛,于《上韓舍人書》中概括性指出大宋江山隱藏的危機之處,“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可謂一針見血。
籍貫蜀地的蘇洵,對家鄉的情況當了如指掌。“夫蜀有三患,其二將形,其一既萌”。人性驕侈,窮民惡盜覬覦財貨,為禍一方;疲兵怯弱,畏避強敵,潰不成軍。二者為將形之患。將形之患雖未能提前發現,扼制于萌芽之中,但既萌之患尚可。“郡縣欲廣其備具,多其戍役,則民不堪”。勞民傷財之事尚未開展,須提前解決,避免此事發生。倘若既萌之患形成,則將形之患會同其一道興起,“其勢如大鼎弱足之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蘇洵所言,當對蜀地官員大有裨益。
蘇洵《嘉祐集》開卷即為《幾策》,此中關聯,不言而喻。蘇洵在《審敵》一文中重新討論了宋朝對遼的外交政策,“憂在外者,末也”。雖然每年以歲幣安撫遼國,但如此只能解一時之憂,且給人民造成了嚴重的賦稅重擔,痛斥官僚以“息民”為名,實則是“愛其死而殘其生”。故蘇洵預見性的主張,應斷絕歲幣貿易,與遼開戰。尚不論宋遼開戰,宋朝是否有戰勝遼國的勝算,但是蘇洵獨具慧眼,明確外敵才是最大隱患、單純依靠進貢僅能維持虛假的和平這一觀點,則建設性十足。
總之,蘇洵善于見微知著,敏銳地捕捉政治上的憂患萌芽,學習圣人,能“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轉危為福”,這與其學習易學以及處事經歷都有關。《易》言:“知幾其神乎?”蘇洵的神明之處,名副其實。
四、結語
蘇洵憑借“十年治《易》”的收獲創立了屬于自己的易學體系,用以觀照現實實踐,裨補時事之缺漏,發人深省。最是《名二子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預判蘇軾、蘇轍二子人生軌跡,令人嘆為觀止。蘇洵本人雖未能官居高位以施展宏圖偉業,亦未能將易學思想完全撰寫成書以衣被后世,但蘇轍有言“先君(蘇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蘇軾)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其易學精華有幸得以保留在二子的著作與評述之中。蘇洵的易學思想,令后世朱子三嘆,其思想價值,不言而喻。探討蘇洵易學,不但有利于深入理解蘇洵的為人處世,更可以找到蘇氏蜀學的內在精神。
基金項目:本成果受北京語言大學院級項目資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21YJ15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