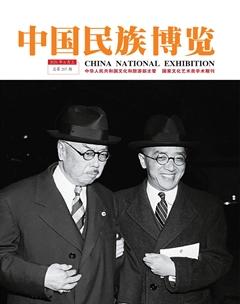戰國秦漢時期平涼地區農業文化之考察
【摘要】本文以平涼市博物館館藏農業文物為支點,結合歷史文獻資料及考古發現成果,對平涼地區戰國秦漢時期的農業發展情況做一系統梳理,建構這一時期平涼地域農業文明的基本面貌。
【關鍵詞】戰國秦漢;平涼地區;農業文化;陶倉;鐵犁鏵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11-195-03
【本文著錄格式】寇少麗.戰國秦漢時期平涼地區農業文化之考察——以平涼市博物館館藏文物為中心[J].中國民族博覽,2021,06(111):195-197.
戰國、秦漢時期,我國傳統的北方旱作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系逐漸形成,步入新的發展階段,黃河流域農業生產進入全面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平涼作為農牧交錯地帶和重要的邊防重地,在歷代統治者的苦心經營下,農業不斷發展繁榮。
《史記·周本記》記載:“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據《平涼古代史考述》作者祝世林先生考證,“戎狄之間”應為渭北高原至六盤山以東今平涼、慶陽部分地區。這一地區居住著土著的昆夷、西戎、犬戎等戎族,還有密須、共、阮等方國,以經營牧業為主,農業生產較為原始。夏末,周先祖不窋活動于涇河流域,不窋及其后世子孫在今平涼地域內不斷開拓經營。公劉教民耕種,恢復農業生產;文王伐密須,筑靈臺祭天,可以說這里曾經是周王朝事業的起根發苗之地,極大的促進了當地傳統農業的萌芽和發展。
戰國時期,社會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重大變革,促成這種變革的根本動力,是當時農業經濟的迅猛發展,尤其是農業生產工具的進步,即鐵質農具和牛耕的使用和普及。鐵質農具與牛耕的出現和使用,使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與青銅相比,鐵器的造價低廉,制作簡易,容易在農業中廣泛推廣,戰國中期,鐵質農具就已經在黃河中下游普及開來。牛耕在商代就已經出現,春秋時就有牛耕的準確記載,戰國開始流行,但直到西漢中期才得到普及。
戰國時期,平涼地區為秦與戎的接壤地帶,至周貞定王八年(公元前461年),秦厲公滅大荔之戎,取其地,隴山以東就只剩義渠戎了,地區轄境六盤以東大部屬義渠。《史記·秦本紀》記:“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在義渠置縣,義渠臣服于秦。這一時期,義渠對本地區有著深遠的影響。義渠雖為戎族,但和秦長城以北過著游牧生活的匈奴有著很大的差別,史籍記載義渠筑有城郭,僅秦惠文王時一次戰爭即奪取義渠25城,可知義渠是定居民族,應以農業為主,畜牧業占有很大的比重。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滅義渠,置隴西、北地、上郡,今平涼東部五縣(市、區)境屬北地郡,西部二縣屬隴西郡,從此結束了戎族政權,進入了秦的統治范圍。此時,平涼既是秦征伐六國的后方基地,又是北防匈奴的戰略前線,勢必會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開發經略,并且在秦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下,當地農業生產力勢必會大大提升。《史記·秦本紀》載:“始皇二十七年巡幸隴西、北地、出雞頭、過回中焉。” 秦統一六國后,秦始皇便在次年(公元前220年)出巡這一地區,足以說明這一區域對秦國整個西部邊防戰略的重要性。秦統治時期,筑長城,修馳道,移民墾邊,帶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極大的促進了平涼地區傳統農業的發展。
衡量農業生產力變化發展最直接的標志和證據就是農業生產工具。農具的發展變化不僅對當時農業生產發展有直接促進作用,而且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也有深遠影響。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農業是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的發展關系到國力的強盛,制約著整個國家的發展。平涼市博物館收藏多件本地區出土或采集的戰國、秦時期的鐵質農具,其中有1件戰國鐵犁鏵、1件秦鐵犁鏵和2件戰國鐵鏟。
戰國鐵犁鏵呈120°的“V”字型,整體長19.2厘米;寬31.0厘米,底面平直,背面拱起,中間起脊,開“V”字形銎,兩翼開刃,犁翼很窄。對比后期出土的鐵犁鏵,此時的犁鏵沒有犁壁,能破土劃溝,還不能翻土做龔。原始的犁應是木質的,有的則可能是木犁身、石犁鏵。戰國時期,在木犁鏵上套上“V”形鐵刃,俗稱鐵口犁。犁是用動力牽引的耕地農具,也是農業生產中最重要的整地農具。牛耕在戰國時期并不普遍,目前我國出土于這一時期的鐵犁也為數甚少。據葉申《春秋戰國時期秦國農具研究》一文對2016年以前發表的各種數據統計,戰國時期,秦地域內出土的鐵犁鏵僅有3件,都集中在陜西臨潼一帶。犁可以算作是最早的農機具,它的出現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此件戰國鐵犁鏵,反映了鐵犁牛耕在平涼地域內的流行和使用情況,表明戰國時期平涼地區在農業生產技術革新方面是走在前列的。鐵犁牛耕是傳統農業的典型形態,預示著這一區域此時已進入以使用畜力牽引或人力操作金屬工具為標志的傳統農業時代,這種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一直延續到了近現代。
秦鐵犁鏵,比戰國時期通用的V形鏵冠型號大,翼長41.0厘米,翼寬36.0厘米,稱雙翼鏵,翻土比戰國V形鐵冠犁鏵要深。秦統一六國后,推廣鐵犁牛耕,改進鐵犁構造,進一步開荒拓地,開墾農田,使耕地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平涼市博物館收藏的兩件戰國鐵鏟,其中一件殘長11.1厘米,銎長6.0厘米,寬2.6厘米。鐵鏟大部分已殘,但還留存了其大致形態,圓直肩,肩部中央有方形銎,可插柄使用。另外一件長12.0厘米,刃寬9.3厘米,刃部殘損。鐵鏟可直接插入土地當中翻土整田或用于田間除草,大型鐵鏟用來翻土,屬于整地農具,小型鏟用來中耕鋤草。鐵鏟是由石鏟和青銅鏟演變而來的,在商周時期稱為“錢”“镈”,是早期布幣的原型,可見其在農業生產中的普及性和重要性。據葉申《春秋戰國時期秦國農具研究》一文對2016年以前發表的各種數據統計,戰國時期,秦地域內出土的鐵鏟也僅有5件,而且大部分也集中于陜西臨潼一帶。這兩件鐵鏟的發現,充分說明了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是與時俱進的,是處于當時農業的一線水平。
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革新和進步,生產力大大增強,糧食作物大量種植,產量大大提高,糧食貯藏也逐漸普遍。平涼市博物館藏多件本地區出土或采集的戰國彩繪陶倉,均有紅色彩繪痕跡,圓腹,底部呈圜底或平底,有圓錐形傘狀頂,頂沿出廓,頂端開口。其中2件頂部飾有兩至三層放射狀泥條,最低層有突出的脊,倉腹部飾有“皮帶工”,中間有方形開口。這幾件陶倉均為明器,即古代墓葬中的陪葬品,都是以現實生活中的器物為原型按一定比例縮小制造而成的,由此可一窺此時糧倉的形貌。糧倉頂部應是仿當時瓦式建筑屋頂,頂部設有通風口,倉房中腹部開有窗戶,以防濕通風。這些彩繪陶倉的出土和發現,充分印證了這一地區農業生產的繁榮景象。

另外,戰國、秦時本地區的畜牧業也十分興旺。《史記·貨殖列傳》載:“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以谷量牛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奉朝請。” 倮,人名,是見于史書記載最早的畜牧家。烏氏,地名,烏氏縣屬秦時北地郡,在今平涼轄境內,據懸泉遺址出土的里程簡,其治所應位于今平涼崆峒一帶。充分證明該地區尚有以谷量牛馬的廣闊牧地。牛是耕田的主要畜力,大量牛的畜養,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地區牛耕的普及。
漢代以降,我國傳統農業不斷發展,進入了定型和成熟階段。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工具的進步,田間耕作技術及田間管理的水平的提高,水利灌溉工程的不斷修建,農作物品種的不斷引進和改良,糧食作物產量的不斷增長。平涼市博物館館藏數十件本地區出土或采集的漢代鐵質農具,其中包括鐵斧、鐵镢、鐵犁及鐵犁構件等。館藏漢代鐵犁主要有三種樣式,如下圖漢鐵犁Ⅰ式、Ⅱ式、Ⅲ式,這些犁鏵長、寬均在35厘米—40厘米之間,屬于大型犁鏵。西漢初期,主要流行戰國時期延續下來的V形鐵犁鏵(Ⅰ式),套裝在木葉犁底上使用。漢代中后期,鐵犁鏵主要流行三角形(Ⅱ式)和舌形(Ⅲ式)兩大類。三角形鏵,鏵面和銎部斷面大致呈等腰三角形;舌形犁,犁面呈舌形,犁鋒部尖圓,前低后高。這些鐵犁清晰的記錄了漢代平涼地區鐵質農具及農業生產技術不斷改進和發展的軌跡。
漢初文景之時,地區轄境處于北地郡南部,為漢與匈奴的交界地帶,是漢王朝北面的邊防重地。據《史記·文帝紀》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大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匈奴久為邊患,使地區農牧業受到了嚴重破壞。漢武帝時期,數次北擊匈奴,帝國版圖不斷擴大,地區轄境從國家的邊防地帶轉變成為接近京師長安的心臟腹地。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安定郡,六盤山以東屬之。漢武帝曾六巡安定郡足以說明這一地區的戰略地位和重要性,它這是拱衛京畿的邊防線、屯蓄重兵的根據地、繁育軍馬的大后方。
武帝之后百余年沒有外患,這為地區農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數次大量移民,屯田戍邊,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栽培技術,農業出現了新的發展局面。據《史記·匈奴傳》:“于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安定郡北部乃是新拓匈奴舊地,也應是移民重點地區。《漢書·平帝紀》載“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懸泉漢簡:“明昭哀閔百姓被災害,困乏毋訾,毋以自澹(贍),為擇肥壤地,罷安定郡呼池苑,為筑廬舍。”“呼池苑”屬安定縣,在今地區華亭一帶,應設立于漢景帝之后,是西漢六牧師苑之一,設苑監以牧養馬匹。平帝時,罷苑置縣,大規模移民進行農業生產。持續性的大規模移民和農墾開發為地區社會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以致郵亭驛置相望于道,成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北線的重要節點,對平涼歷史文化發展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7.
[2]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
[3]祝世林.平涼古代史考述[M].平涼:平涼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97.
[4]李根蟠.中國古代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5]陳文華.農業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6]孫機.中國古代物質文化[M].北京:中華書局,2014.
[7]平涼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平涼地區志[M].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8]葉申.春秋戰國時期秦國農具研究[D].鄭州:河南師范大學,2016.
[9]劉興林.漢代鐵犁安裝和使用中的相關問題[J].考古與文物,2010(4).
[10]張馳.兩漢西域屯田的相關問題——以新疆出土漢代鐵犁鏵為中心[J].貴州社會科學,2016(11).
[11]張多勇、李并成.義渠古國與義渠古都考察研究[J].歷史地理,2016(1) .
[12]張德芳.漢帝國在政治軍事上對絲綢之路交通體系的支撐[J].甘肅社會科學,2015(3).
[13]劉芮搏.秦漢皇帝出巡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5.
[14]張德芳.漢簡確證:漢代驪(革干)城與羅馬戰俘無關[N].光明日報,2002-05-19.
作者簡介:寇少麗(1986-),女,甘肅平涼,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博物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