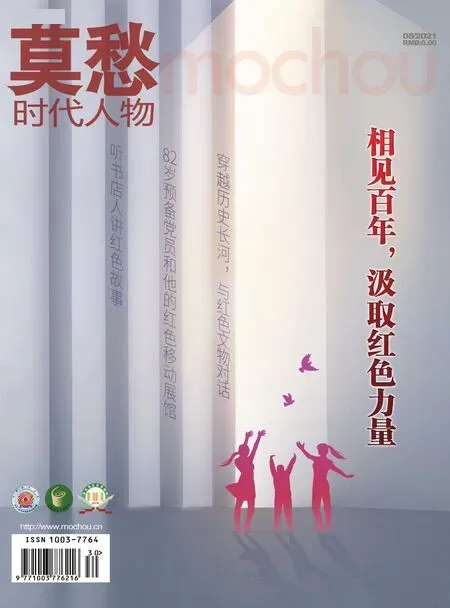達維德·迪奧普:打破緘默的“詞語音樂家”
文/文心

達維德·迪奧普
“在夜里,所有的血都是黑的。”小說《靈魂兄弟》的英譯名《夜晚血液都是黑的》取自書中第三章結尾的這句話。2021年6月,法國作家達維德·迪奧普的這部小說榮獲2021年國際布克獎,這是法國作家首次獲得該獎項。
雙重的文化敏感
1966年,迪奧普出生于法國巴黎。迪奧普的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塞內加爾人,兩人在巴黎的大學里相識,而后生下了迪奧普。但迪奧普的童年是在塞內加爾達喀爾度過的,直到學齡后回法國讀書。
1998年,迪奧普成為法國波城大學的文學講師,后成為該校藝術、語言和文學系系主任。迪奧普主講18世紀文學,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18世紀有關非洲的各種表述,尤其是出自旅行者的說明與影像。“我對各種有助于表述他者的信息來源頗有興趣,不論是非洲還是亞洲的他者。”他說。
在法國,迪奧普以善于揭露偏見的運作機制而著稱。201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歷史小說《1889》,講述了一名前往巴黎參與1889年世博會的塞內加爾代表的故事,該書的靈感便來自有關19世紀“人類動物園”以及歐洲的黑人“奇觀”的歷史記載。而2018年他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學術著作《18世紀的黑人修辭》,則涉及18世紀旅行寫作和廢奴主義文本中對非洲人的描述。
打破戰爭后的緘默
迪奧普的外曾祖父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在戰爭中因德國人的毒氣受傷,雖然沒犧牲在戰場上,但很早就去世了。
曾有約13.5萬名非裔步槍兵在歐洲參與了一戰,其中至少3萬人戰死。這些士兵的籍貫涵蓋了整個西非地區,包括塞內加爾、馬里、尼日爾和布基納法索,他們從未在法國歷史教材里得到應有的尊崇。非裔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出生入死,薪資卻很微薄,退伍補助也少得可憐,這一不正義現象不乏文獻記載,但他們在歐洲戰場的鮮活體驗卻從未真正被講述過。“因為我有雙重的文化敏感性。”迪奧普說。他開始打算虛構一些士兵信件來填補這一空白。
在閱讀與研究中迪奧普發現,與法國青年士兵不同,當年參加一戰的塞內加爾年輕人沒有留下多少文字材料——文化水平和語言隔閡隱沒了他們的聲音,而在“敵對方”德國的記錄里,他們甚至被丑化為野蠻人。隨著創作的進展,迪奧普改變了想法,把信件寫成了一部小說,《靈魂兄弟》由此誕生。這是一部以塞內加爾青年士兵為視角的小說,主人公是塞內加爾小村莊的農民之子,他輾轉于戰爭的無主之地,親見好友之死,也親手制造更多的死亡,殺戮、思考、瘋狂同時發生。
在接受BBC(英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迪奧普說:“外曾祖父從未對妻子或我母親說起過他的經歷。這就是為什么我總對這件事感興趣,這些故事和描述能讓人們以一種親密的方式了解那場特殊的戰爭。”
迪奧普希望能捕捉到戰爭造成的驚人緘默這一主題。來自法國西南部某村莊外曾祖父,在參與一戰期間不慎吸入毒氣后,“回到家后他什么也沒說。”迪奧解釋道:“他,包括非裔士兵在內的其他士兵,對此事都三緘其口,不愿回憶這些難言之隱,以免驚嚇到家人。而我希望這種緘默能被一種聲音所填滿,這種聲音是不可被聽見的,因為它是思想之聲、內在之聲。”
小說在法國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甚至有讀者會攜帶曾祖父的來信以及親戚在戰爭期間與非洲步槍兵微笑合影的照片來參加簽名活動,不少人后悔自己以前沒能多關心親人的經歷。

達維德·迪奧普和《靈魂兄弟》中文版譯者高方
將韻律編織在語言里
“非裔士兵在法國又被譽為祖國的救星,其大男孩一般的形象曾出現在巴納尼亞牌巧克力飲料的廣告上……黑人面對敵人是野蠻而嗜血的,回到法國后他們又成了勇敢的士兵并有一種特別的天真爛漫。”迪奧普說。這一切都被深深地編織進了他的語言里,以此在小說風格上取得巨大的成功,這一點被小說所有獲提名項目的評委提及。
2018年,小說《靈魂兄弟》在法國瑟伊出版社出版。雖然迪奧普寫意識流的時候用的是法語,但語言的韻律卻透露出主角恩嘉耶是以沃洛夫語(沃洛夫人的民族語言,也是塞內加爾使用最廣的語言)來思考的。迪奧普以這種方式來凸顯這名男青年的內心聲音。這種豐富的內心獨白的復雜性表現出一種荒謬性:殖民地部隊專門學了一些初級水平的法語,方便在戰壕里執行命令。
迪奧普曾讀過一本1916年的指南,內容是如何把這種散碎的基礎法語教給非裔士兵。“導論中提到,由于非洲人的語言極其‘貧乏’,教授給他們的法語也得貧乏一點……許多軍團士兵認為這種做法把他們低幼化了。有步槍兵回憶稱,他們說這種法語的時候會遭到嘲笑。”
“野蠻的是戰爭,而不是士兵。”迪奧普說道。他稱自己筆下的主角為“怪物”,但轉而又補充道:“與此同時,他又是如此地有人性,這也許是我們所有人的真實狀況。我們分享著他的思考,我們也分享著他的親密,但他也是一個極度暴力且飽受戰爭創傷的人,正如許許多多的士兵一樣。”
布克獎評委會主席露西·休斯-哈萊特表示:“這個關于戰爭、愛和瘋狂的故事具有可怕的力量。咒語般的文字、既黑暗又燦爛的景象穿透了我們的情緒,震動了我們的靈魂。”評委貝爾納·皮沃認為它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原創的、令人驚異”的作品,并將迪奧普形容為“詞語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