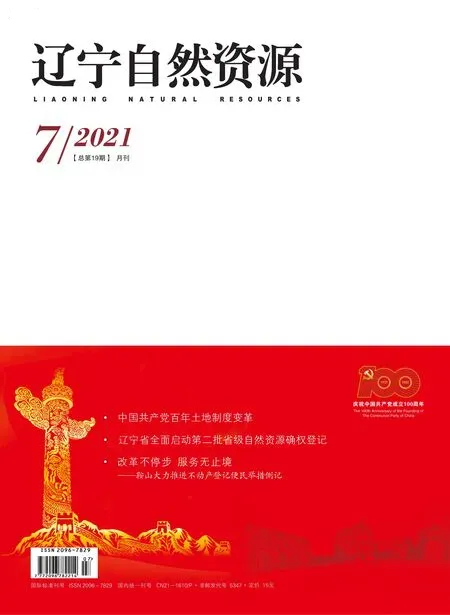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 保障了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村發(fā)展

公有化改造完成以后,廣大的農(nóng)村地區(qū)基本實現(xiàn)了集體化生產(chǎn)。然而,由于組織管理的缺陷,尤其是產(chǎn)權(quán)與利益、責任的不對等,必然導致生產(chǎn)效率的急劇下降,民生受到極大的威脅。加之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及1959-1961年連續(xù)旱災,出現(xiàn)“三年困難時期”。緊接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階級斗爭為綱”,生產(chǎn)力繼續(xù)下降,導致農(nóng)村地區(qū)極度困難。廣大農(nóng)民,為了生存,不得不探尋新的生路。
最著名的案例是安徽小崗村。1978年底,小崗村18戶農(nóng)民秘密簽署了一份包產(chǎn)到戶的協(xié)議,私自決定包產(chǎn)單干。到1979年秋收之季,這些農(nóng)民所獲得的糧食遠高于鄰村,引起一些鄰村的農(nóng)民也紛紛效仿。隨后引起各級領(lǐng)導關(guān)注,尤其是引起中央領(lǐng)導的重視,并最終得到國家政策改革認可,全國推行,并通過法律予以確立。
實際上,自1951年合作社運動開始一直到1979年,全國不同地區(qū)的廣大農(nóng)民一直處于“合作化能夠?qū)崿F(xiàn)生產(chǎn)大發(fā)展、快速進入共產(chǎn)主義的良好愿景”與實踐中的生產(chǎn)力低下、忍饑挨餓的抗爭之中,并不斷付出艱苦的努力與探索。早在小崗村包產(chǎn)到戶的兩年之前,四川省蓬溪縣群利鎮(zhèn)九龍坡村就進行了類似的嘗試。1976年9月的一天晚上,公社黨委書記鄧天元召集一小群干部商討如何提高糧食產(chǎn)量。經(jīng)過漫長而激烈的辯論,一致同意采用包產(chǎn)到戶的方式來解決生產(chǎn)積極性問題。考慮到面臨的政策風險,他們決定先把處在邊角的土地分配到其中兩個生產(chǎn)隊的家庭,其余地方則仍然保持集體耕種不變。結(jié)果年終那些邊角耕地的糧食產(chǎn)量比集體耕種的肥沃土地的產(chǎn)量高出了3倍。第二年就將更多的土地進行包產(chǎn),更多的生產(chǎn)隊加入到包產(chǎn)到戶的行列。由于存在違反政策的風險,當?shù)卣冀K被蒙在鼓里,這屬于“只干不說”。
國家政策層面的變革也是十分曲折的。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認為是改革的轉(zhuǎn)折點,但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依然強調(diào)“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chǔ)的制度,穩(wěn)定不變”。1979年9月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guān)于加快農(nóng)業(yè)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依然明確規(guī)定“不許分田單干”,但也開了個口子“除某些副業(yè)生產(chǎn)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qū)、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chǎn)到戶。”

盡管如此,由于實踐中,像安徽小崗村、四川九龍坡村等各種名目的包產(chǎn)到戶、包干到戶在全國各地暗中蔓延,一些有識之士(包括官員、學者等,如萬里、胡耀邦、杜潤生等)積極推動,1980年春末包產(chǎn)到戶得到部分中央領(lǐng)導的首肯,尤其鄧小平明確肯定安徽肥西縣的包產(chǎn)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指出“農(nóng)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chǎn)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chǎn)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jīng)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chǎn)到戶的地方,……只要生產(chǎn)發(fā)展了,農(nóng)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fā)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正式的政策變化,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zhuǎn)《全國農(nóng)村工作會議紀要》(第一個“一號文件”),指出“農(nóng)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yè)承包聯(lián)產(chǎn)計酬,聯(lián)產(chǎn)到勞,包產(chǎn)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責任制。”第一次通過中央文件形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jīng)營制度。直到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進一步加強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工作的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tǒng)分結(jié)合的雙層經(jīng)營體制作為我國鄉(xiāng)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wěn)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
農(nóng)村集體土地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改革,作為當時農(nóng)村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第一步,突破了當時“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過程的個人付出與產(chǎn)出分配直接掛鉤,使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大增,解放了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同時解放了勞動力。總體來看,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責任制,一是實現(xiàn)了土地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與經(jīng)濟關(guān)系的對應。即給予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明確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并基于這一土地權(quán)利進行土地利用,獲得土地產(chǎn)出,實現(xiàn)了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與經(jīng)濟關(guān)系的對應,符合科斯定理。二是堅持了土地的生產(chǎn)要素屬性。通過包產(chǎn)到戶,讓農(nóng)民通過生產(chǎn)增加產(chǎn)出,不僅吃飽了肚子,還由于生產(chǎn)率的提高,及家庭生產(chǎn)的自主性,產(chǎn)生了剩余勞動力,為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城市化發(fā)展也提供了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