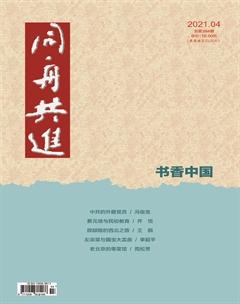“其所得將無限也”:近代著名學人的讀書與治學
王學斌

清末民初,正值天下大變之時,胸懷天下與蒼生的知識人們迫切需要從各類書籍中覓得救世良方。較之古人,其讀書習慣遂多了一分時代的屬性。
以梁啟超為例。作為彼時思想傳播的領頭羊,他的筆鋒常常自帶“魔力”,深深影響了一眾青年學子。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回憶:“梁氏簡潔的文筆深入淺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穎或困難的問題。當時正需要介紹西方觀念到中國,梁氏深入淺出的才能尤其顯得重要。梁啟超的文筆簡明、有力、流暢,學生們讀來裨益匪淺,我就是千千萬萬受其影響的學生之一。我認為這位偉大的學者,在介紹現代知識給年輕一代的工作上,其貢獻較同時代的任何人為大,他的《新民叢報》是當時每一位渴求新知識的青年的智慧源泉。”青年毛澤東博覽群書,對《新民叢報》印象深刻,“這些書刊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那時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梁的文章“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可知梁文深深影響了幾代知識人。
然倘若細思,讀新式報刊確實會給人耳目一新甚至醍醐灌頂之感,但報章文字畢竟因其題材與功用所限,價值尚淺。知識人要想濟世,恐怕還要從扎扎實實閱讀一本本經典或專著入手,打好底子,充實自我,具備真學問,養得大氣象。早在清末,梁啟超便直言:“學問之道,未知門徑者以為甚難,其實則易易耳。所難者莫如立身,學者不求義理之學以植其根柢,雖讀盡古今書,只益其為小人之具而已。所謂藉寇兵而赍盜糧不可不警懼也。”可知在民國學人心中,讀書之本意與路徑,看似稀松平常,實則極為講究。
【讀書之始,須立讀書之志】
為何要讀書?這恐怕是彼時每位學人都曾自我追問的終極問題。
揆諸時人回憶,錢穆先生的經歷堪稱耐人尋味。十歲那年,還在家鄉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求學的錢穆,一天遇到體操老師伯圭先生,此君是錢氏同族且參與過革命活動。伯圭先生一把攬住錢穆的小手問道:“聞汝能讀《三國演義》,然否?”錢答然。伯圭師謂:“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后正該學它們”。
對于一名小學生而言,這番話無異于“巨雷轟頂”,錢穆自道“余此后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換言之,錢穆一生讀書治學所欲達致之境界,“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
錢穆明曉讀書之本意,憑的是他人啟迪,著名史學家蔣廷黻靠的則是自我領悟。早在少年時期,蔣廷黻已立下為改變中國落后局面而奮起讀書的宏愿。赴美求學期間,蔣對政治的高度熱情便初現端倪。在專業選擇上,他原本想鉆研政治學,以便將來在中國政壇馳騁一番,但后來又發覺政治學太過于理論化,不切實際,“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于是他專攻歷史學,主修政治史。但他又不僅僅為歷史而歷史,而是為了致用而研究歷史,“學習歷史以備從政之用,此一見解倒是深獲我心。在過去,不分中外,許多歷史學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適例”。強烈的入世乃至用世的沖動,是蔣廷黻轉而攻讀史書的緣由所在。
歷史往往多有巧合。待到蔣廷黻執教清華后,為了喚醒學子們對“九一八”事變的關注與警惕,他于事件發生后第四天,特意在清華校內發表題為《日本此次出兵之經過及背景》的演講,青年學子夏鼐去現場聆聽。由于受國難刺激而激發的憂患意識以及蔣氏演講所產生的號召力,夏發覺歷史可以照進當下與未來,并不“空虛”。此后兩月內,他一氣讀完李劍農的《最近三十年之中國政治史》、劉彥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及樊仲云《最近之國際政治》,最終下定決心“進軍”歷史系,拜在蔣廷黻門下。
因看中夏鼐學史之意愿所在,蔣廷黻對其的培養頗具特色。蔣深知夏的史學功底較薄弱,于是命他多讀史料、多寫書評。半載后,尚不知學界這潭“水”深淺的夏鼐,興沖沖地將所寫書評匯集成冊,希望老師推薦出版。蔣通篇閱畢,告知夏撰寫歷史著作非常艱難,此書評集過于稚嫩,“非同時兼閱其他參考書不為功”,況且“以中國對于純學術的著作殊難求銷路之廣,書店不敢出版恐致折本”。蔣師此番點評如同一盆冷水,將夏心中旺盛的熱情驟然澆滅,禁不住在日記里道:“我知道自己入歷史系是弄錯了,嗚呼!今日中國之出版界!”
其實,此舉不過是蔣“欲揚先抑”之策,目的在于祛祛夏身上的虛驕之氣。待夏倍受挫折后,蔣適時開出一份三十多部的書單,令其逐一精讀。沒了浮躁,夏讀書自然心平氣和,加之他天資不錯,很快便“上道”。兩年內,在蔣悉心指導下,夏發表三篇論文及一篇書評,可謂成果頗豐。
如上三例,不難發現讀書之始,須立讀書之志,否則恐流于囫圇吞棗,徒為一兩腳書櫥而已。
【梁啟超叫板胡適】
既知需讀書,那要讀何書?讀書的范圍與目錄,民國學人不乏各種討論。最有名的,莫過于胡適與梁啟超受《清華周刊》所邀開列國學書目及二人之間引發的意見分歧。
1921年,在創辦《讀書雜志》的緣起一文里,人氣甚旺的教授胡適強調此刊物的一大初衷,即在于“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
那到底何類書籍算是好書?有沒有一份堪稱權威的書目可供參考?兩年后,《清華周刊》記者邀請胡適、梁啟超等學者擬定一份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適一馬當先,開了一張洋洋灑灑達190余部典籍的書單。依照胡氏本意,他擬這個書目的時候,“并不為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也就是說,這些書應是針對零門檻的普通人而定,是最基礎的入門材料。
就如何研究國學,當時尚沒有系統可循的規范路徑,那些作出成績的人大都要下死工夫,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學的門徑。對初學人而言,須先引起他們的真興趣。所以胡適想了一個方法,“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這個書目便是依著這個觀念做的。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這意味著,該書目并非一盤散沙,而是內含著胡適精心置入的閱讀邏輯,如能按部就班,自然能登堂入室,掌握國學。如此看來,胡適本人對書目還是頗為自得的。
奈何支起了一大口熱鍋,迎來的卻是一盆盆涼湯。先是清華學子不買賬。他們回信反映,第一,這次所說的國學范圍太窄了,在文中并未對國學下定義,但由所擬的書目推測起來,似乎只指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但思想史與文學史便能代表國學么?第二,先生(指胡適)所談的思想史與文學史──談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認定清華學生的國學最低限度,應要顧及兩種事實:第一是他們的時間,第二是他們的地位。“我們清華學生,從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學一年止,求學的時間共八年。八年之內一個普通學生,于他必讀的西文課程之外,如肯切實的去研究國學,可以達到一個什么程度,這是第一件應該考慮的。第二,清華學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教育家對于一班留學生,要求一個什么樣的國學程度,這是第二件應該考慮的。先生現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為書目太多,時間太少”。他們希望胡適另擬一份真正適合學子們實際情形的書目。
礙于情面,胡適后來特意撰文解釋,最終他還是壓縮了數量,圈出了一份所謂的“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
然而畢竟這個破綻已是顯露于眾,素來喜歡叫板的梁啟超此次“黃雀在后”,不僅補交了一份書目,還寫了篇《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與之商榷。身為學界前輩,且后來出手,梁氏自然不會客氣,他開篇徑直認為,“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原因何在?梁啟超認為,胡適致誤之由,第一在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為立腳點。當時胡適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這個書目正可以表明他的思想路徑和所依據的資料。但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這里頭的書便十有七八可以不讀;真要做哲學史、文學史家,這些書卻又不夠了。其次,胡適之失誤在于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殊不知青年學生,正苦于跑進圖書館里頭不知讀什么書才好,不知如何讀法,你給他一張圖書館書目,有何用處?何況私人購書,談何容易?這張書目,如何能人人購置?結果還不是一句廢話嗎?”
此外,胡適在前述書目里自稱是隱含內在邏輯可供遵循的,梁啟超卻認定此邏輯并不通。比如“連《史記》沒有讀過的人,讀崔適《史記探源》,懂他說的什么……”可見胡并沒有考慮到讀者的實際知識儲備,更多是憑個人想象。

其實,時人已注意到胡適治學與讀書的某些習氣并不值得推廣。如夏丏尊就曾提醒學子們,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確實是好書,但在未讀過《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原書的人去讀,實在不能得很大收獲。知道了《春秋》《左傳》《論語》等原書的大概輪廓,然后去讀《哲學史》中的關于孔子的一部分,讀過幾篇《莊子》,然后再去翻閱《哲學史》中關于莊子的一部分,才會有意義。
如此看來,給他人開書單,并非易事,且茲事體大,一來能否符合對方實際需求,二來個人經驗能否放大為普遍做法,也需認真考量。否則到頭來不免有南轅北轍、誤人子弟之虞。
其實梁啟超這般細致地挑錯,并非有意針對胡適,而是真心希望學子們能讀到應讀之書。故后來他又專門寫了《治國學雜話》,為學子們打氣。在他看來,人生“隨時立刻可以得著愉快的伴侶,莫過于書籍,莫便于書籍”。中國的古籍有許多沒有經過整理,十分難讀,這是人人公認的,但會做學問的人,覺得趣味恰在這里。雖然很多年輕人一讀便是一個悶頭棍,每每打斷興味,這是壞處,然而如果逼著自己披荊斬棘,從甘苦閱歷中磨煉出智慧,那可是莫大的好處。梁先生對年輕讀書人的諄諄教誨,躍然紙上。
【讀書貴在勤、恒、毅】
有了合適的書,又當怎樣讀呢?
對此問題歸納較早的,還要屬“好為人師”的胡適。1925年,胡適撰寫題為《讀書》的文章,刊于《京報副刊》。根據個人經驗,胡提出讀書的兩個要素:“精”與“博”。
何為“精”?胡適看來,可用“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來概括。“眼到”是要個個字認得,不可隨便放過;“口到”則是一句一句念出來——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兩遍以上,方能明白;“心到”是體會每章、每句、每字意義如何,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而是要靠外面的設備及思想的方法的幫助,如使用字典、善于比較、要會“于不疑處有疑”等。“手到”就是要勞動勞動“貴手”。胡適以為,吸收進來的知識思想,無論是看來的還是聽來的,都是模糊零碎的,算不得我們自己的東西。必須經過加工——或做提要,或做說明,或做討論,自己重新組織過,申敘過——那種知識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
胡適還特意舉了得意門生顧頡剛的例子。胡曾勸顧頡剛標點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起初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讓顧補貼家用。原以為他一兩個星期就可以標點完了,哪知顧一去半年,還未交卷。原來他于每條引的書,都去翻查原書,仔細校對,注明出處,注明刪節之處等。動手半年之后,顧頡剛告訴老師,《古今偽書考》不必付印了,他現在要編輯一部疑古的叢書,叫“辨偽叢刊”。一兩年之后,更進步了,顧頡剛索性要自己創作了。胡適認為顧頡剛將來在中國史學界的貢獻一定不可限量,他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他“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沒有動手不勤快而能讀書的,沒有手不到而能成學者的”。
那何為“博”?胡適概括為兩個意思:“第一,為預備參考資料計,不可不博。第二,為做一個有用的人計,不可不博。”一言以蔽之,要打開涉獵范圍,“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一書。多讀書,然后可以專讀一書”。
總而言之,胡適心目中理想中的學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博大要幾乎無所不知,精深要幾乎唯他獨尊,無人能及。故他對讀者的期望,遂用一句口號表達:“為學要如金字塔, 要能廣大要能高。”雖寫得粗淺,倒也生動貼切。
胡適這篇談讀書的文章,啟迪后人之余,仍失之于泛泛。因此后來史學大家嚴耕望先生曾特意做了幾點補充,其中與讀書緊密相關的,可總結為“勤”“恒”“毅”。
“勤”,這是學術工作者所應具備的起碼條件,不能勤,根本談不上做學問,做其他的事,恐怕也不會有多大成就。單就閱讀而言,嚴氏認為,閱讀要精讀、粗讀、檢讀、泛覽兼具并行。
“恒”,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難做到。就讀書來說,無論職業怎樣忙,年輕人畢竟精力旺盛,每天抽出兩小時讀書,絕不困難,只要減少無謂的交際應酬與消遣,便可做到。每天兩小時雖不多,但十年累積就很可觀。若能堅持十年以上,一定會有相當成就。
“毅”,沒有堅強的毅力,如何能永恒地工作下去?再者,毅力在另一方面表現是耐性。長期讀書,耐性極重要。因為工作有時不免繁重,或遭遇困難,非用無比的耐性加以克服不可。而有了堅強的毅力,無比的耐性,問題也一定會獲得解決,很少白費功夫。
嚴耕望先生的補充,使得讀書這項事業,除卻趣味,多了幾分精神。
【“橫通”者,移動的“四腳書柜”而已】
如上關于讀書的心得,更多還是關乎方法和門徑,尚未言及境界問題。
一番深邃鉆研、博覽群書后,學人的境界當是怎樣?其實一字便可概括之:“通”。古人所追求的治學化境之一,即“通”,故學識淵博之輩,常被譽為“通人”。
民國以來,西方的現代學術體制大舉入主中華,分科由強力貫徹到形成慣例,逐漸為社會習以為常。然科目區分,初衷不外乎便于大學建立科層式的學術體系,利于學術研究的細化與深入。不過這種高度分工現象的背后,往往易于形成壁壘自立的觀念,“專家”涌現便是最佳證明。即使在民國時期,“專家”一詞也并非褒義。于是在諸學科各砌城墻、森嚴對峙之際,偶有數人可探出城外,說幾句其他門類的“內行話”,遂被目為通人,頗受追捧。只是他們究竟“通”什么,如何“通”,仍是值得琢磨的。
故此處的“通”,又有“縱通”與“橫通”之別。縱通,大致指學問已貫通古今、涵蓋四科(經、史、子、集)之境界,似毋須贅言。至于“橫通”,錢鍾書先生將其解釋為“參考書式的多聞者”。錢雖以博聞強記聞名于世,但其實他認定“參考書式的多聞者”距離“通人”甚遠,“大學問家的學問跟他整個的性情陶融為一片,不僅有豐富的數量,還添上個別的性質;每一個瑣細的事實,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養,長了神經和脈絡,是你所學不會,學不到的”,“反過來說,一個參考書式的多聞者,無論記誦如何廣博,你總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凈”。依錢氏之意,“橫通”者僅是可移動的“四腳書柜”而已,乏創新,缺思想,少關懷。
很多學人對此亦是心有戚戚。顧頡剛治學之初,曾以貪多求博聞名,據其自述,“到這時,天天游逛書肆,就恨不能把什么學問都裝進了我的肚子。我的癡心妄想,以為要盡通各種學問,只須把各種書籍都買下來,放在架上,隨心翻覽,久而久之自然會得明白通曉。我的父親戒我買書不必像買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買書好像瞎貓拖死雞一般的不求揀擇,但我的心中堅強的執拗,總以為寧可不精,不可不博”,一副以有涯之生追無涯之知的架勢。
然終有一日,顧氏忽而翻到章學誠的《橫通》篇,“自想我的學問正是橫通之流,不覺得汗流浹背。從此想好好地讀書”。但那時其仍限于目錄一類書籍。又過幾年,顧才“胸中有了無數問題,并且有了研究問題的工作,方始知道學問是沒有界限的……”可見若無問題意識,學問終歸流于泛泛。有了問題,學問便會做得專精,隨著研究深入,自然延及其他科目,達至觸類旁通。
陳垣先生開門授徒,便極其強調“博”與“專”關系的處理。他反復主張,研究歷史,需要知道的知識幅度很大,既要了解古今中外,又當有己之專長領域。若樣樣都去鉆研,事事皆欲過問,勢必囿于時間、精力,反使得門門都不能深、不能透。但話又說回來,只有專精,沒有廣泛涉獵,專業研究亦如沙上筑塔,難以持久。所以,無論何種專業,不博不能全面,因閱讀范圍不廣,得出孤陋寡聞、片面偏狹之結論在所難免。但若只是一味求博,便勢必淺嘗輒止,淪為“橫通”,無法攀登學問之頂峰。
其實要想接近“通”的境地,有兩種精神不可或缺。其一是讀書勿“殺書頭”。民初學者黃侃精通《說文解字》,與其讀書習慣大有關聯。黃侃讀書,喜歡隨手圈點。他圈點時非常認真,許多書都不止圈點了一遍。如《文選》圈點數十遍,《漢書》《新唐書》等書三遍。《清史稿》全書七百卷,他從頭到尾一卷一卷地詳加圈點,絕不跳脫。因此,他把讀書時只隨便翻翻、點讀數篇輒止者稱作“殺書頭”,很不以為然。
關于黃侃讀書之苦,許多學者津津樂道,但他并不以為苦事。他亦憑此方式引導弟子讀書。黃氏授徒有一套自己獨特的方法:他先命學生圈點十三經,專力章句之學,每天直到深夜方命歸寢。如此日積月累,經時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經圈點完。于是,黃侃告訴學生,繼此之后,可以把“必讀之書”增至二十四種。后黃侃又要求學生在三十歲之前一定要讀完唐以前的典籍,因為唐以前留傳下來的典籍為數不多,容易讀完,又是非讀不可的書。有了這樣的功夫,就等于摸清了中國文化的源頭,再調頭審視唐之后作品,頗有一覽山小之感。如此往后研究任何門類的中國學,就都好辦多了。
一次,黃侃與學生陸宗達閑聊,黃問陸:“一個人什么時候最高興?”陸不知道老師此問何意,就亂猜一通。黃侃聽后,只是搖頭。最后,陸問老師答案是什么,黃侃笑曰:“是一本書圈點到最后一卷還剩末一篇兒的時候最高興。”這次談話讓陸宗達終生銘記在心。
錢穆先生對此精神深有同感。年少時他喜歡四處翻書,常少定力。一日,他讀到《曾文正家書家訓》,發覺曾國藩教人讀書,“必自首至尾通讀全書”。反觀自身,則多隨意翻閱。于是錢下定決心,痛改前非,“即從此書起,以下逐篇讀畢,即補讀以上者。全書畢,再誦他書”。另外,錢氏還效仿古人“剛日誦經,柔日讀史”之例,堅持每天清晨必讀經子艱讀之書,夜晚始讀史籍,中間上下午則讀閑雜書。一直堅持到老,收獲之豐,可想而知。

其二是坐得住“冷板凳”。除卻讀書之規矩,黃侃在治學上還告誡學生不要輕易在報刊上發表文字,一則學力不充分,一則意見不成熟,徒留他人笑柄,于己無益,于世有損。黃侃更是以身作則,坐穿冷板凳,五十歲前不著書,自認從知天命之年開始,方是學術研究的收獲季節。反觀今人,不少抱著“出名要趁早”之觀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發表,以博取功名金錢。
其實,黃侃所言三十歲前不發文,五十歲前不著書,除去忠告學人要潛心讀書,做大學問、真學問外,另有一層深意隱含其間,這便是關涉學者“如何做學問”層面的問題。在黃看來,學人寫文章,一方面要立說,另一方面就是要善于藏拙。畢竟任何知識體系都不會盡善盡美,人文研究更需長時間的潛心磨練,方有可能得出些許真知灼見,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誰耐得住寂寞,誰才有可能攀上學術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須慎之又慎,因為若是讀書不夠,輕下結論,暴露自己學問不扎實之事小,而誤導后輩學子盲從之事大。
所以,學者好似闖蕩江湖的劍客,再精妙的劍術也必須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歷經百戰而不致方寸大亂。如果功利心過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寫文章著作里完全體現,甚至奢望超水平發揮,以收到八分、十分的效應,學人們往往淪為“快手”“高產學者”,一年論文一二十篇,不論質量如何,先以數量勝人。但不容忽視的是,鋒芒畢露的同時也時常意味著破綻百出。學人們將文章一并公布于世,其水平高下自然盡收于同行眼底,優劣得失判然分明。而其中之敗筆、硬傷更會讓他人記于心間。“慢工出細活”,或許做學問的真諦不過如此,又唯有如此。
【讀懂書,更需讀懂作者和時代】
綜觀民國著名學人諸多關于讀書之高論,大致而言,皆是期望后人能胸存貫通之念、并不功利、滿懷興趣且孜孜不倦地一生讀書。倘申言之,則有三條準則:第一,治學須經過放眼讀書的階段,讀者不可預設藩籬和問題,避免受到近代分科教育的局限和他人觀點的左右,努力把握學問的基本大貌,打好功底。第二,讀書要虛懷若谷,力求理解前人著述通篇之本意,切莫自設架構,戴著有色眼鏡先入為主,如此勢必斷章取義,穿鑿附會。是故唯有始終以無我狀態讀書,方能養得大氣象。第三,讀書絕非看到最后一頁即告結束。當由書見人,知人而解書,把握各類作者行事著述的慣習風格,細揣其人其學在學術史中的位置,理解彼時之時代風尚與學界時趨。總之,讀懂書,更需讀懂作者和其身處的時代。如此才能具備真學問。循此門徑,讀者或有可能逐漸登堂入室、把握來龍去脈,從而執簡御繁。于是,讀書之樂便開花結果、妙趣橫生,暢游其間,不亦樂乎。
民國學者蒙文通先生曾形容過該境界:
做學問必選一典籍為基礎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礎,與無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礎大不一樣。無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礎,讀書有如做工者之以勞力賺錢,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礎,則如為商者之有資本,乃以錢賺錢,其所得將無限也。
明確好專精、博約關系,讀書先須“善入”,一頭猛地鉆入書堆中,啃上十年八載;再須“善出”,以知識常識見識來比觀時人時勢,必妙不可言。誠可謂“其所得將無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