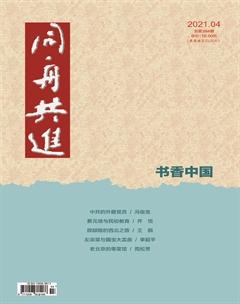書店:城市的文明之光
維舟
近年來,中國的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在物質繁榮之下,很多城市實體書店的生存空間卻頻頻引起社會關注,當然不只是因為書店本身(錄像租售行業的衰落就沒引起這么大反響),而是因為書店是一個城市文化空間的象征。
在電商、電子出版物如此發達的時代,現代城市還需要書店嗎?需要的話,是需要什么樣的書店、它們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如果沒有了書店,我們的生活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閱讀的黃金年代】
國內的書店也曾有過輝煌時期。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國人陷入全民的知識渴求,說書店是人們心目中的文化殿堂,大概也不為過。當時像成都甚至出現過通宵排隊購買中外文學名著的盛況,絲毫不亞于如今追星的狂熱。
作家毛喻原在《再見冬妮婭》一書中曾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的書店,心中感慨頗多。“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地方,我們的書店拒絕武俠小說,也拒絕流行讀物,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書店仍能盈利。比照今天的情況,真是有些不可思議”。也就是說,當時的書店還不需要迎合市場的壓力,店面租金和人員成本都不高,買書的人也多——在那個年代,連電視機都還是奢侈品,書籍幾乎是為數不多的文化消費選項之一,還未遭到電視、網絡的強有力競爭。
1990年代初,中國的書店面貌發生巨變。此前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新華書店一統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一大批風格獨具的民營書店開始密集涌現,后來各地最具代表性的書店,幾乎都創建于這十年間。如北京的萬圣書園、席殊書屋、風入松、國林風圖書中心,上海的季風書園,廣州的博爾赫斯書店、學而優書店,南京的先鋒書店,杭州的楓林晚書店,貴州的西西弗書店,長春的學人書店等。
但實際上,從大的文化發展趨勢來看,書店的式微已在醞釀中。有在文化系統任職的領導回憶,許多一度大受歡迎的劇種,在1980年代就“都不行了”,“電視開始往家庭里走,報刊發行量大增,而報紙則是極其流行……后來流行歌曲、卡拉OK、舞廳、電視都來了,戲曲就嘩啦啦地退了”。觀眾正在更新換代,其構成、趣味和選擇今非昔比,流行文化的崛起勢必會擠占閱讀的時間。只不過電視一時尚難席卷全國(全國電視普及率2000年是86%),而對中國人來說,“讀書”又具有特殊的意義,暫時還不像傳統劇種那樣受到全面的沖擊。
如今回想起來,這是在互聯網大潮涌來之前的一個閱讀的黃金年代。1997年1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了第一次統計報告,全中國僅有62萬上網用戶;兩年后,當當網問世,很快成長為威脅實體書店的一大巨頭。
其實,在網絡的威力顯現之前,電視的影響力、全民“下海”賺錢的沖動和店鋪租金上漲的壓力,已開始讓一些書店感到窘迫。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一年,中國網民飆升至近3億,當當、卓越(后來的亞馬遜中國)、京東等電商平臺憑借低折扣和送達到家的物流配送力量,影響力日漸擴大,而實體書店的困境也逐漸浮現。2013年全國工商聯書業商會調查顯示,在此前十年里,全國有一半的實體書店先后倒閉,總數多達一萬多家。
這樣的影響也波及世界各地。法國巴黎的文化地標、已有兩百年歷史的老店莎士比亞書店,受疫情影響,在2020年的下半年里,書店銷量下跌了80%,不得不在虧本經營中苦苦支撐。
雖然這一現象,在這十多年里早已屢見不鮮,但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卻眾說紛紜。新媒體閱讀的分流、網上書店的沖擊甚至“中國的年輕人不愛讀書”都曾被列舉出來作為“替罪羊”,但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書店盡管有其特殊性,但它的生存最終也跟服裝店、鞋店一樣,是一個可持續經營的商業問題。
早在2012年春,上海季風書園的創始人嚴博非在被媒體問及新店經營狀況時,就連說了三個“不好”,當時季風的營業額已銳減至全盛時的1/4,而門面租金、薪資支出卻比開店時大幅上升。雖然一些地方政府、商業機構對書店租金盡力減免,但薪資的壓力仍是實實在在的,這意味著書店必須另辟收入來源才能活下去、活得好,僅靠扶持仍無法續命。
不僅如此,這也表露出國內書店行業普遍存在的問題:大量的書店同質化競爭,既缺乏在選書、空間風格等方面的特色,賣的“商品”(書籍)又與別處無異,卻又比電商平臺貴。這是無法指望讀者們出于“情懷”而一直無條件扶持的。
然而,很多書店經營者創業的初心,與其說是為了商業經營,倒不如說是出于文化使命感——1990年代那批有代表性的民營書店老板,在他們身上,大部分是“文化人”的氣質壓倒“商人”,他們常常并不認為自己是在“賣書”,倒是在對抗消費主義。
書店要擺脫困境,說到底需要脫胎換骨的轉型,在這樣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仍試圖“以不變應萬變”是不行的,相反,必須“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書店的確不應該只是“賣書的地方”,這就觸達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為什么要去書店?書店對我們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書店存在的意義】
這個問題原本并不存在,因為它看起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書店的存在,是為了讓人能有地方買到自己想讀的書。
雖然書店在中國至少已有一千年的歷史,但直到很晚近的民國時期,它才逐漸演變為一個社會文化空間。它起初只是市場上的臨時攤位,“書店”一詞的出現,不早于清代中葉。這說明,其實書店在很長時間里并未扮演重要角色。
晚明時的胡應麟就曾記述,在省城、府城這樣的都市之外,書店是極少的,甚至幾乎沒有。這樣的情況到近代也并無多大改觀:1914年前后,30萬人口的山東省會濟南,就只有9家書店。當時真正像樣又豐富的書店,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文化中心,也只有在這些地方,書店才對新一代知識青年的精神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學者金克木曾回憶,北京的舊書店和書攤子,對年輕時的自己而言,就像是一所非正式的“大學”,可以站在那里一本一本地翻閱,“舊書店里的人是不管的,無論賣中文書的或賣西文書的都不來問你買不買。因為是舊書,也不怕你翻舊了”。
清末民初時,全國的書店都收攏在商務印書館等三大出版巨頭的龐大銷售網絡之下,尤其是通用的教科書,行銷全國。葉圣陶在小說《倪煥之》中,曾借用甪直鎮上小學教師之口抱怨,“大書店最關心的是自家的營業,余下來的注意力才輪到什么文化和教育”,商業利益的驅動多過文化使命感。
確實,當時的新書出版銷售之所以吸引了眾多懷著各種目的的文人、商人投身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通俗文學新書具有資金周轉快、利潤高、更便于短線作業、面向顧客群體更廣等特點。也正因為如此,各種小書店在當時旋生旋滅、生生不息,為新一代知識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間和物質支撐。像魯迅就經常以內山書店為據點,會客見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自視為社會的靈魂,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此種觀念的生成,與當時的小書店是分不開的。
書店作為社會文化空間的意義,盡管有過一段時間的中斷,但還是延續了下來,直到在市場化和新媒體的大浪之下受到猛烈沖擊。2011年,《南方日報》的一篇文章標題說出了人們內心的感受:“實體書店紛紛倒閉,逛書店會不會成為歷史?”不過,這與其說是在討論實體書店的經營狀況本身,倒不如說是聚焦我們社會的讀書現狀。
1992年,在第一屆臺北古書拍賣會上,著名的誠品書店曾這樣解釋:“臺北自詡為國際性大都會,購買力早已讓歐美各國稱羨,唯獨在古書業,并未隨著經濟起飛而發展,反而日趨沒落,甚至不能跟它蓬勃的出版業相提并論,無疑是此地文化界的一大缺陷。”兩岸同根生,這番話也可以用來形容這邊各大城市的現狀——沒有像樣的書店,似乎對一座現代城市來說是不相稱的。
倒不是說非要花大價錢來維持一個不賺錢的行當,而是說,這涉及現代城市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文化生活,書店又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滿足不同層次人群的不同精神需求的獨立書店,是城市文化多元的體現,因此,容納不同特色的書店,是一個城市精神生活的多元化的外在表征。就像生物多樣性一樣,每一家獨立書店的消亡,都是對公共文化多元性的一種打擊。
當然,實體書店的危機并不只是在中國,歐美、日本也同樣嚴重,很多人都在憂慮“年輕人不看書”的現象。在日本,2005年的全國實體書店總數為17153家,到2014年就減少為12793家,而日本的新書還不能打折,此舉已經減少了網上書店對實體書店的沖擊了。
這甚至還不止是閱讀的危機,美國作家阿扎爾·納菲西在《想象共和國:三本書里讀美國》中說:“并不只是書店和圖書館在消失,博物館、劇院、表演藝術中心、藝術與音樂學校——這些讓我感覺自在的地方都進入了瀕臨滅絕物種列表。”互聯網的沖擊加速了之前就已被很多學者關注到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人退回到私人的世界里自娛自樂,通過電視屏幕、網絡和遙遠的外界發生聯系,用社會學家桑內特的話說,這是“公共人的衰落”。
就中國社會的現實來說,這還具有復雜的雙重處境:一方面,知識生活未能觸及日常生活的核心地帶,對務實的大眾來說,讀書仿佛是“有文化的人”才關心的事,更樂于通過輕松的娛樂來緩解自己的壓力;另一面,電視、網絡等媒體形式又使人們的文化消費極大地豐富了,閱讀早已不再是唯一的文化生活。一如貧乏的年代里桌上沒什么菜,只能多啃主食,但日子越是豐裕,主食就吃得越少,吸收營養的渠道也變了,要再回到以往那個主食當道的年代,似乎是不可能了。
在這一意義上,書店的處境是城市文化空間的縮影,對此的關注與思考,其實遠不止關乎書店本身,而涉及城市規劃的理念,甚至是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品質。就像城市中的綠地,它可以讓人得以有一小塊地方“詩意地棲居”。
【書店如何生存】
如果要保留實體書店,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必然是:如何讓它在現代城市中生存下去?
在香港,像旺角這樣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有不少書店,然而幾乎都是“二樓書店”,因為底樓的鋪面租金太高,書店根本租不起,只有像香港三聯這樣的出版集團,才能在底樓支撐一個較大的門面。相比起來,臺灣的誠品書店則開辟了另一種模式:依托房地產綜合開發和多樣化經營,使書店變成一個文化品牌和人流聚集的樞紐節點。
出版人陳穎青曾說過,在市場的高度壓力下,如今必須懂得如何應對市場,而“一本書能不能賣,總共就是兩件事:一是書本身,二是社會的共振”。也就是說,書店就算只是賣書,需要考慮的也不只是把“貨物”擺在哪兒就結束了,甚至還需要具備策展能力,推動這些書在社會上激起反響。
對于傳統的書店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理念。上海季風書園在店面設計上就可看出差異:早先的陜西南路總店幾乎全是書,只在一個狹窄的過道里擺幾張茶幾作為休息區,一旦到了讀書分享沙龍時,這兒就擠得水泄不通。2013年遷到上圖新店,卻專門辟出一塊不小的咖啡館區域,內間還有專設的報告廳作為聚會演講的場所。其實,在這方面季風已經慢了一拍,像2006年創辦的單向街書店,從一開始就非常注重文化活動;2011年創辦的方所書店、2013年創辦的鐘書閣、2014年創辦的言幾又,無不著意于設計感和消費體驗,并以文創活動等多樣化經營來獲得多元收入來源。
這順應了后現代社會的關注重心從“消費”到“體驗”的轉換,以至于有些書店本身都變成了“景點”。2016年開業的上海大隱書局,坐落在充滿古典氣息的武康路,內部設計也十分典雅,很快成為許多文化人鐘愛的聚會場所。上海思南書局詩歌店,改建自原先的東正教堂,在2019年底開張時就引起轟動,幾天里都擠滿了慕名而來的人,他們與其說是讀者,倒不如說是游客,目光都不是在看書,而是忙著拍照。近兩年杭州、上海的蔦屋書店也是同樣的情形,以至于開張都成了網上熱議的話題,到處都能看到文藝青年去打卡后拍的照片、分享的感受,但這隨即又引起了一種不滿的聲音,質疑這樣的“網紅書店”是否違背了書店的本意。
的確,之前就有人譏諷,這樣的書店其實是“以書籍為裝飾背景的咖啡館”,但給讀者帶來更好的閱讀體驗無可厚非,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給書店帶來更多元化的收入,實現可持續經營。日本今野書店的老板就曾說,為書店客人提供咖啡,“這種模式,一是能夠讓客人放松,二是附設咖啡館會有雙重效果,書店和咖啡館的利潤率都會提高”。
在網絡的沖擊下,書店創新只能是“背水一戰”,它必須帶給人們網上所沒有的體驗——特別是面對面的對談、設計空間的感受、周到的服務等等。這樣,一家書店其實已經變身成為文化綜合體,它集書的銷售、咖啡館或茶館、文化對談空間、文創用品店、創意設計等諸多功能于一身,日本的有些書店甚至根據書的多樣性兼營雜貨,包括餐具和衣服,人們在那里可以獲得整體性的體驗,滿足不同人的需求,而網絡書店僅憑低價售書的單一功能,很難取代它。
另一種出路則是個性化。國內的書店原先是高度同質化的,圖書的品種和結構都差不多,但近年來也在不斷借鑒別國書店營銷的成功范例。比如在日本東京,每家書店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些是專注于某一門類的書,特別是珍稀的二手書和古董書,有些是在特別的地點開設特色書店(如京都在動物園內新開書店),甚至還有森岡書店這樣每周只賣一本書的書店——這些都需要強大的策展能力輔助,配合以相應的主題活動。其共同的內核在于,必須注重讀者的用戶體驗,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在特定空間下的感受。日本就曾有過測試,在專業人員改變選書、擺書方式后,平均單客購書額竟然漲了三四倍之多。
2015年,無印良品首次嘗試附設書店,結果大獲成功,賣書后客流量有明顯增加。設計師清水洋平發現,書天生就是“長尾產品”,每一本書的世界觀都很獨特,能聯系不同人,因而具有多樣性和連接性,還能幫人打發時間,因而無印良品書店可以吸引一家人購物時無處可去的男性、男性上班族等各類人群。在此,它提供的其實是“有書的生活”——這個重點在于“生活”,而不是“書”。
這樣,書店其實超越了書店自身,而融入了社會生活。在近代的西歐,咖啡館無疑就是這樣的公共空間,如果說人們去咖啡館,并不只是去喝咖啡的,那么這道理對書店也一樣,也只有真正進入到現代人的生活中,人們才會感覺離不開它、用它來滿足自己的文化生活需求,同時支撐它的生存發展。
當然,也有人會提出疑問:如果是這樣,那么書店和咖啡館、茶館的區別在哪里?在筆者看來,這既可以在功能上有所重疊(書店也可以賣咖啡、賣茶),但又要有所區隔——如果是一場新書分享活動、文化講座,那么在書店無疑比咖啡館合適得多了。說到底,就像《東京本屋》里說的,“書店就是讓一個人和一本書偶然相遇的場所。從這個角度來看,你一個人,從今天就可以開始是‘書店”。
這實際上對書店的經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迫使它具備多元綜合能力,并能調動多種文化資源,源源不斷地生產出相關的文化內容,并根據讀者的反饋,不斷加以調整改進。毫無疑問,這非常難,但也唯有如此,它才無法被輕易取代。
【書店的未來,城市的未來】
書店的生存并不只是書店自己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能做點什么呢?
造成中國書店業今日的處境,除了租金漲幅大、書價上漲令一些人望而卻步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電商平臺相對于傳統零售業特別發達,為爭奪市場份額又能虧本經營,在圖書銷售上也能不斷推出很低的折扣,這在十多年來一直使實體書店陷入苦戰。書店往往變成了一種樣本展示空間,不少人在書店翻翻書,轉身去網上下單。而日本的實體書店則沒有這樣的苦惱,因為日本規定新書一律不得打折。由于新書的毛利幾乎總是定價的22%左右,所以日本反倒是二手書店發達,因為二手書可以有自由定價權,能取得70%的利潤率。
和其它行業不同,出版、書店是極少數恪守固定價格制度的行業,每本書的定價都標注清楚,不能改動,這不像服裝,每家店都可以有自由定價權,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將價格拉高或壓低,但書的進貨、賣價很難有調整空間,這原本旨在消除書店之間的價格競爭,確保不管在哪里,買到書的機會都一樣,人們也都買得起書。
歐洲和日本一樣,在固定價格制度的基礎上,禁止電商平臺降價出售新書。20世紀初,英國書商協會和出版社共同達成《圖書凈價協議》,明文規定:除教科書外一概不得打折出售。不過,由于幾家大型連鎖書店的挑戰,英國法院在1997年裁決該協議失效,開始轉向美國式的自由價格制度。中國的實體書店面臨的則是:自己固守固定價格制度,但網絡書店卻可以自由定價來打價格戰,以至于陷入難以擺脫的被動態勢。
在政策制定和市場治理的問題上,這或許在短期內難以取得進展,但各地至少有一點是可以做的,那就是在城市規劃和城市治理上,預留文化空間,充分考慮像書店這樣的文化設施,并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因為這和圖書館、美術館等一樣,其實是給當地居民提供的公共福利。
不過,單純的扶持事倍功半,更好的選擇是如何取得各方共贏。在這方面,近些年來先鋒書店另辟蹊徑,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從2014年起,它避開大城市,而深入到各地鄉村,已先后開設皖南碧山、浙江松陽陳家鋪、福建廈地水田、云南沙溪等六家書店,幾乎每到一地,都成為引人注目的成功案例。像云南沙溪的先鋒書店,在2020年5月疫情期間逆勢而行,開業不到半年就實現了盈利,堪稱奇跡。
它為何能成功?這大體可歸結為它成功聯結了各方需求,又契合了市場痛點。本來,在中國的實體書店版圖上,鄉村幾乎是個空缺,長期缺乏高質量的書店布局,因此先鋒書店的這一規劃本身就找準了空白,“燃亮鄉村閱讀之燈”。與此同時,“先鋒書店”的品牌和一流的設計理念,結合當地的景色,嵌入地方的文化脈絡中,立刻成為當地的文化坐標,吸引了很多人不遠千里前去觀賞——他們當然不僅僅是去買書的,也帶動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像浙江桐廬的先鋒云夕圖書館,在2015年開張時,當地這個4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僅有1家民宿,但三年時間就增至24家。
在云南沙溪,當地政府幾乎是把一座廢棄的糧倉免費送給了先鋒書店,這本身就免去了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高昂的地價和租金,只是需要一點書籍的配送成本、后續的員工薪資,而這些原本也都是需要的,鑒于它帶動的巨大效應,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當然,尤為關鍵的是建筑設計。沙溪先鋒書店落成后,被廣泛譽為“全球最美書店”,很多人專程去沙溪古鎮“朝圣”,特意在沙溪停留幾日,這對當地政府而言,也絕對是一個雙贏的項目,真正把“鄉村振興”落到了實處。
像這樣的成功案例也提醒我們:中國人并不是不需要書店,或不喜歡讀書,關鍵在于能否提供不一樣的體驗。這就像一個小縣城里,平日電影院的兩個廳都坐不滿,但新開的一家大商場里,卻七個廳都爆滿——人們并不是沒有看電影的文化消費需求,而是原來簡陋的設施體驗太差,越差越不想去,以至于惡性循環。
在此,一家書店其實已是文化綜合開發項目,成為撬動當地文化生活、文化消費、創意產業、旅游景觀乃至土地增值的支點,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很難被其它設施所替代。這既需要書店方面的資本和創造力,也需要地方政府的眼光和決策,當然也離不開一流的建筑設計團隊,且能準確把握市場需求,最終將每一個項目都發展成為“文化IP”。
由此來看,國內實體書店真正的問題并不是“年輕人都不愛看書了”,而是“年輕人都變了”,如何順應時勢,挖掘新的需求,帶來不一樣的體驗,這不僅考驗經營者的市場嗅覺,也考驗各地政府能否轉變思路,甚至勇于創造機會。如果能這樣,那我們有望看到的,不僅是實體書店不一樣的未來,也是城鄉文化空間不一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