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活疫苗:終結黑色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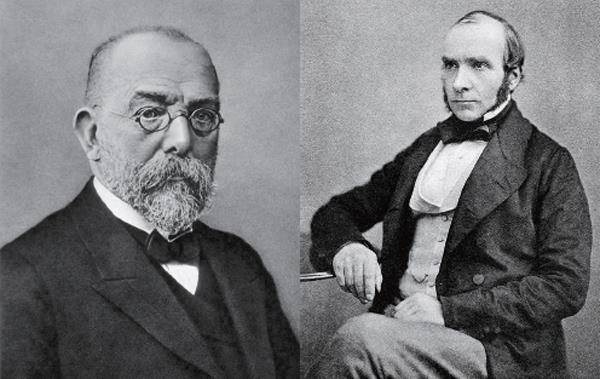
左:羅伯特·科赫 右:約翰·斯諾
“霍亂暴發時,不計其數的尸體被草草埋進萬人坑,土地像是吸滿了血的海綿,一腳踩上去,血水便會滲出來。”
—— 加西亞·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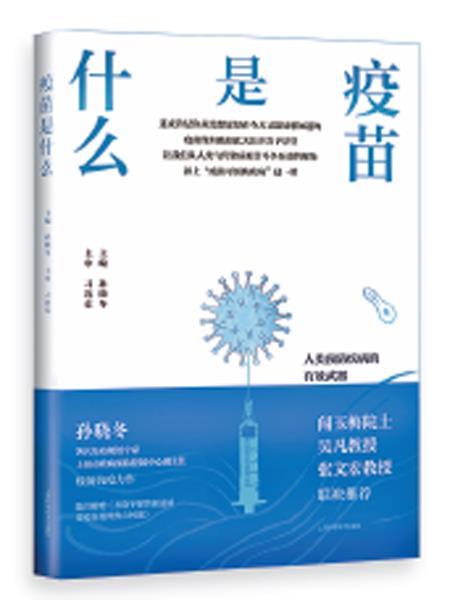
書名:《疫苗是什么》
主編:孫曉冬
主審:刁連東
出版: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同處19世紀的英國。1854年的英國,霍亂疫情空前嚴重,曾經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此刻卻被死亡腐朽的陰霾籠罩。此時,年輕的約翰·斯諾醫生在倫敦的布羅德街區已經調查了好幾天,盡管他對當時主流學派提出的“瘴氣論”頗有質疑,但關于造成霍亂流行的真正元兇至今一無所獲,這讓他感到無比沮喪。
斯諾醫生曾在1849年的《倫敦醫學報》上發表了相關論文,以解釋霍亂傳播的途徑。在這篇論文中,他發現大多數煤礦工人的死亡與食物有關,因為這些工人不管做什么都沒有洗手的習慣,導致他們中間只要出現一個腹瀉患者,那么腹瀉這種癥狀很快就會在周圍的人群中傳播開來。斯諾以此推論,霍亂的傳播與不良的衛生習慣和臟亂的環境有關。可惜的是,這篇論文的發表在當時并沒有引起重視。
直到1854 年,一場嚴重的霍亂疫情迅速在倫敦的索霍區暴發,其中布羅德街是疫區最為嚴重的街道之一。街區幸存的居民們慌不擇路地往外逃離,只有斯諾不顧勸阻,堅持前往死亡街道,一家一戶推開連他都不知道門后是尸體還是活人的房門,記錄著患者每天的癥狀和行動軌跡,最后將這些信息在地圖上匯成了一張統計圖,也就是后世著名的“死亡地圖”。
斯諾不辭勞苦地走訪了疫區13個公共水泵和578例死亡病例的位置,發現大部分的死亡病例都集中在布羅德街和坎布里格街交叉口的一處水泵周圍,而坎布里格街北面的死亡率明顯低于其他地方,因為北面的居民使用了其他水泵。且離交叉處的水泵越遠,居民的死亡率越低。盡管斯諾醫生的這一發現已經可以很好地反擊“瘴氣說”,但倫敦當局并不對這一說法買賬,原因在于當時倫敦惡臭彌漫,人們更傾向于將疫情流行歸咎于可以聞得到的瘴氣,而非看不見的水質污染。
對此斯諾醫生并不氣餒,為了更好地驗證自己的論點,他改變研究方向,將目光放到了布羅德街沒有患病的人身上。位于布羅德街附近的一家啤酒廠就這樣進入了醫生的視線,啤酒廠距離布羅德街僅180米,但啤酒廠里的工人卻奇跡般地沒有染病。一番調查后,斯諾醫生發現,因為在啤酒廠里,工人們可以喝到免費的啤酒,所以他們幾乎不喝廠外的水,自然也就在這場疫情中逃過一劫。除此之外,在離布羅德街不遠的一個監獄里的囚犯,也幾乎沒有霍亂病例,原因是監獄有獨立的水井,因此從未使用過布羅德街的水泵。
斯諾醫生將手中的資料迅速整理匯總,交給了索霍區當局,并要求關閉疑似傳染源的水泵。為了控制疫情,當地官員的頭發都快薅禿了,這回他們聽取了醫生的建議,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下令關閉了布羅德街和坎布里格街交叉口的水泵,自此肆意狂虐的病魔逐漸放慢了進攻的腳步,疫情終于得到了緩解。
約翰·斯諾將霍亂病例放置在地理網格上,并根據家庭供水來源比較霍亂發病率的方法,開創了流行病學研究的新時代,他讓流行病學調查不再局限于抽象的數字和表格,軌跡地圖的應用,至今在傳染病學、人類學等學科有著深遠的影響。
時間來到1883年,羅伯特·科赫帶領一個調查隊前往印度進行病毒學調查,他們在那里發現霍亂患者身上攜帶了相同形狀的細菌。到了1884年1月,科赫成功分離出純培養的逗號桿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O1群霍亂弧菌病原體。
而此時,巴斯德發明的雞霍亂疫苗已經打開了減毒活疫苗的新篇章。在人類首次分離出霍亂弧菌后的第二年(1885),西班牙細菌學家海梅·費蘭(1849─1929)首次使用霍亂活菌接種,試圖通過自動免疫來預防疾病。在幾千人的臨床試驗中,接種組的霍亂發病率降到了1.3%,但對比組的患病率仍是7.7%,由此可見,接種疫苗對疾病起到了一定的預防作用。但毫無疑問,活菌疫苗帶來的不良反應也是相當嚴重的。
為了提高疫苗的安全性,1888年,伽馬雷亞提出可以通過降低毒力來減少疫苗的不良反應,他把霍亂弧菌加熱至120℃來殺死菌體活性,以此獲取的疫苗在接種過后仍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力。1896 年,科勒提出使用瓊脂培養霍亂弧菌,在加熱殺死后接種使用——這一疫苗制造方法就是現今通用的“滅活疫苗”(死疫苗)的原型。(選摘:張鈺瓊)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
“不良反應”的真相
編者:蔣麗麗 審稿:紀潔
1974年1月,倫敦大奧蒙德街兒童醫院醫生威爾遜在《英國醫學雜志》上發表了一份名為《百日咳接種的神經系統并發癥》的研究報告,報告稱有36名兒童在接種了百白破疫苗后出現精神發育遲緩、癲癇性腦病等癥狀。該報告經電視紀錄片播放及報紙的報道發酵,再次引起了人們對疫苗安全性的關注和爭議,引起巨大社會反響,在英國掀起一場“疫苗恐慌”。在英國“疫苗傷害者父母協會”的推動和電視新聞持續報道下,民間抵制運動高漲,蔓延至歐洲、日本,并擴散到美國、蘇聯和澳大利亞。
盡管英國疫苗和免疫聯合委員會再三向公眾確認其安全性,并啟動了一項國家兒童腦病研究,證實了嬰幼兒的神經疾病與免疫之間的關聯度很低,但公眾的疑慮仍然難以被打消。結果,很多國家的政府迫于壓力,紛紛在這一問題上讓步。
真相或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2006年,對14例曾被診斷為疫苗相關性腦病的患兒經基因測序,發現11例是德拉韋綜合征(Dravet syndrome,鈉通道SCN1A基因突變),又叫“嬰兒嚴重肌陣攣性癲癇”。疾病名稱過于專業,我們暫且不用去記憶。我們只要知道,這是一種國際公認但是少見的嬰兒期癲癇性腦病,80%的患兒因基因突變而致病,95% 屬于患者自身基因突變而不是父母遺傳。言下之意就是,這些嬰兒已發生基因突變,無論是否接種疫苗,這個疾病早晚都會發作。接種百白破疫苗引起的腦病實際是偶合了德拉韋綜合征。
目前,國內外一系列的大型流行病學研究已證明,易發生“嬰兒痙攣癥”的患兒體內體液免疫紊亂(血清中存在的針對腦組織的自身抗體)才是“嬰兒痙攣癥”發生的根本原因。百白破疫苗因含有免疫增強劑成分,故使得接種百白破疫苗成為易發生“嬰兒痙攣癥”患兒潛在的觸發因素。因此,在百白破疫苗說明書中已將“患腦病、未控制的癲癇和其他進行性神經系統疾病”列為該疫苗接種的禁忌癥。可見,預防接種后不良反應的發生是否與疫苗相關,應當謹慎評估、科學判定。
20世紀80年代,為了引導人們重新接受百白破疫苗接種,時任英國衛生大臣的女兒和威廉王子高調接種百白破疫苗。其后,疫苗控制傳染病的效果被證實,人們逐漸恢復接種疫苗的信心。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百白破疫苗接種率提高到 93%,百日咳發病率隨之下降,逐步恢復到中斷接種前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