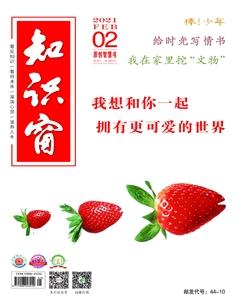用腳步慢慢打破對世界的猜想
流念珠

有一次聊天,寧卉對她的朋友說:“我是一個不規范的國際新聞記者。”
比如手機里的突發新聞提醒功能,寧卉是常年關閉的。明明只要設置一下按鍵,她就能關注到天下大事,然后侃侃而談一番,可她偏不,而是去關注一些不起眼的人和事。記者的形態有很多,可寧卉絕不是刨根究底,去尋找能夠打開“真相魔盒”鑰匙的那一種。
寧卉曾在剛果(金)港口城市馬塔迪參加過一個家宴。家宴主人是中國人老韓,他開著一家雜貨店,在剛果(金)住了十多年。那天,老韓邀請了寧卉和幾個朋友,其中有一位醫生、一位建筑承包商、一位道路工程師和一位做科技產品維護的大學畢業生。飯桌上,大家一邊吃著飯一邊侃天侃地。醫生說他來非洲是因為有個兇狠的老母親,在家里實在憋氣;承包商說他一開始覺得這個國家又窮又亂,結果待了幾年就習慣了;道路工程師來的時間最短,所以他一直問大家剛果(金)是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國家;大學生來了半年多,說不想繼續待了,下個月準備打道回府;老韓見過的人最多,他說國內競爭太厲害,根本做不成生意……
老韓家與外界隔著兩道鐵門。寧卉一邊聽他們既樸素又急切的談話,一邊在心里感慨:鐵門里的這幾個人,每個肚里都裝著不易被察覺的辛酸,所以他們需要一頓能在陌生世界里構筑安全港灣的家宴。
還有一回,寧卉在法國加萊采訪時恰好遇上一件殘酷的事情:法國政府要把一處居住著一萬多難民的叢林徹底拆掉。拆到最后,政府不想動手拆難民們自己搭建的一座教堂和一座清真寺,而是希望難民自己動手。
某一天,挖土機隆隆作響,寧卉在離挖土機不遠的地方遇到了一位來自蘇丹的難民費薩爾。此時,大多數難民要么已經離開叢林在找住處,要么已經被法國政府重新安置。費薩爾卻蹲在帳篷里,絲毫沒有要走的意思。他一身整潔,帳篷里干干凈凈,連撿來的柴火都碼放得整整齊齊,與快要成為垃圾堆的叢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寧卉問他:“這個叢林馬上要被拆光了,你擔心明天嗎?”
費薩爾蹲在地上,拿著一根樹枝攪著鍋里的米糊,面無表情地說:“我不需要擔心。明不明天的,其實無所謂……”
寧卉說,那一刻,費薩爾的波瀾不驚讓她讀懂了什么叫作絕望。
令寧卉難以忘懷的,還有馬達加斯加島上卡采皮小漁村的一個場景。那是南半球的冬天,天氣很好,海面平靜,寧卉看到海灘邊坐著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婆婆。老人說她這一輩子沒有離開過這個地方,目前家里只有三口人——她和她那已年過半百的雙胞胎兒子。兩個兒子早上四點出海,下午三點起風前才回來,但收成并不好,只捕到三條小魚和一條鰻魚,勉強夠吃,卻不夠賣。
老人一邊盯著準備燒魚的兒子,一邊對寧卉說:“50年前,我丈夫一次出海就能打到300斤魚!”旁邊一個正在修船的中年鄰居苦笑著接話:“在10年前,我每次都能打回50斤左右的魚。如今,一天只打幾斤魚也是常事了。”
寧卉問老人:“50年前300斤,10年前50斤,現在小幾斤,那以后會不會沒有魚了?”老人瞪著眼,激動地說:“大海里怎么可能沒有魚呢?”修船鄰居的妻子很堅定地對寧卉說:“捕魚靠不住,只要一有機會,我們就會離開!”
老人不像鄰居那樣對未來抱有很多期待,因為她無法想象,如此廣袤的大海可能都不會給他們安身立命的機會。想到這里,寧卉心里五味雜陳。
“那些看起來不起眼的時刻,在我的采訪中占據著很重要的位置。我很開心能夠在世界的角角落落聽到截然不同的說法和故事,它們可能都是真相,也可能都不是。”寧卉對朋友說,“我少時看過一部意大利電影,里頭一個老人對一個懵懂少年說:‘你不要一直留在這里,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會以為這兒就是全世界。我很認同這句話。我會繼續遇到世間不同角落里的老人和懵懂少年,因為我想當一名用腳步慢慢打破對這個世界的猜想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