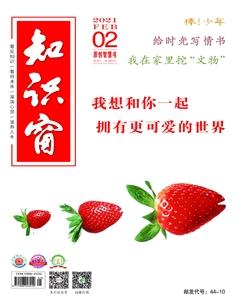燈火可親
沈慶保

“家人閑坐,燈火可親”,這是汪曾祺先生回憶家鄉(xiāng)燈火的語句。仔細(xì)品味,當(dāng)年如豆的燈火,也曾一度照亮并溫暖我們的童年。
點(diǎn)燈熬油,對于貧寒之家純屬一種奢望。所以,那時(shí)的鄉(xiāng)下,一家老小往往天黑即睡,只想能省則省,不點(diǎn)燈最好。有時(shí)煤油緊缺,人們就用柴油代替。但是用柴油點(diǎn)燈,捻子易燒焦,光線較暗且易冒煙,用不了多久鼻孔就會(huì)被熏黑。據(jù)說,當(dāng)代著名作家周克芹先生在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時(shí),白天勞作,晚上點(diǎn)起油燈伏案寫作,在隨風(fēng)搖曳的文學(xué)光焰照耀下寫啊寫,直寫得鼻孔發(fā)黑,鬢發(fā)斑白,歷盡艱辛,作品于1982年榮獲首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
我至今難忘第一次感受汽燈的欣喜和好奇。當(dāng)時(shí),母校北馮場小學(xué)辦起了初中,開始有了初一和初二年級。聽說初中要點(diǎn)汽燈上晚自習(xí),正讀小學(xué)三四年級的我比初中生還興奮,急忙和幾個(gè)小伙伴趕了過去。學(xué)校沒有院墻,初中教室均在學(xué)校南面的第一排,前面有個(gè)小樹林,再向南還有一條水溝。冬天,水溝干涸,我們就躺在溝的南坡,煞有其事地捧起書本。汽燈果然很亮,盡管隔了一二十米遠(yuǎn),我們?nèi)阅芸辞鍟系淖舟E,只可惜光線太強(qiáng),有些刺眼。
我印象深刻的玩燈經(jīng)歷至少有五次:一是嘗試著制作電石氣燈,這種燈邊冒氣邊燃燒,確實(shí)好玩;二是元宵節(jié)端著面燈到處瘋跑,直跑得滿身冒汗,油枯燈滅;三是用煤油浸泡法桐的果球,自制一種點(diǎn)著后用腳踢著可以滾來滾去的“燈”,頻頻引來他人防止失火的大呼小叫;四是巧用廢圓珠筆芯,除掉筆頭上比油菜籽還要細(xì)小的圓珠,產(chǎn)生一個(gè)小孔,然后用嘴對著燭火吹氣,會(huì)有一絲藍(lán)瑩瑩的火苗從一端躥出,落在一枚硬幣上,熔出一個(gè)小小的洞眼;五是用針挑著黃豆在燈火上燒烤,隨著“啪啪”幾聲輕響,焦香摻和著煤油味鉆進(jìn)鼻腔,待放入嘴里咀嚼,身后土墻留下了竊笑的身影。除此之外,我還接受過父親和母親關(guān)于“凍死不烤燈頭火”的告誡,雖然懵懵懂懂,但也依稀知道,做人要有一點(diǎn)骨氣。
燈火,對于我們十分重要,可以說一輩子都離不開它。它總是與閑適恬靜的生活有關(guān),并被濃郁的世情所濡染,從而自帶穿透黑暗的鋒芒,持久散發(fā)著柔和的光輝,逼催壓抑的日子一點(diǎn)點(diǎn)退縮。
關(guān)于燈火省與費(fèi)的抉擇,曾讓我再三糾結(jié)。高三那年,我家新建的一棟房子,距離學(xué)校僅有兩三百米。因?yàn)闆]有通電,我專門買來蠟燭以備夜晚學(xué)習(xí)之用。后來,一下晚自習(xí)我就會(huì)帶一些資料回家,等到了家,考慮自己勞累了一天,晚上熬夜有些白費(fèi)蠟,不如第二天早起事半功倍。可是,惰性較強(qiáng)的我次日卻很少早起,結(jié)果一個(gè)學(xué)年也沒將那些蠟燭用完。現(xiàn)在想來,當(dāng)初高考失利,與我的懈怠有關(guān),也與疏遠(yuǎn)燈火有關(guān)。
老舍先生曾給白石老人出過“考題”,其中最有名的要數(shù)“蛙聲十里出山泉”和“凄迷燈火更宜秋”。《凄迷燈火更宜秋》的構(gòu)思十分絕妙,用兩筆直線畫了窗的一角,里面有一盞小燈,火苗是紅的,被風(fēng)吹得略歪,窗外飄來一片楓葉,慢慢地落在燈火上方。窗下一片空白,約占全畫四分之三。白石老人屬鼠,他愛鼠,也愛燈,一生畫了許多幅《燈鼠圖》,每一幅都極具情趣。
燈火可親,誠哉斯言。我希望,這燈火永在,持續(xù)傳遞生活的無限希冀,家人的朝夕陪伴,以及人間的暖暖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