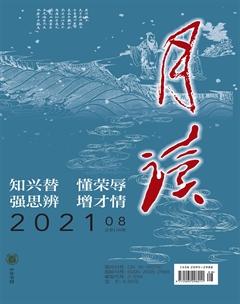尚節(jié)亭記
〔明〕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a,蓮取其出污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huán)以象b,坐右之器以欹c,或以之比德而自勵(lì)d,或以之懲志而自警e,進(jìn)德修業(yè),于是乎有裨焉。
會(huì)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jié)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jié)之亭,以為讀書(shū)游藝之所,澹乎無(wú)營(yíng)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
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fēng)雨摧折者,以其有節(jié)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f,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于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jié)言竹,復(fù)何以尚之哉?
世衰道微,能以節(jié)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jié)立志,是誠(chéng)有大過(guò)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
夫節(jié)之時(shí)義大易備矣g,無(wú)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jié),實(shí)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脈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dá)而為美植。反之,則為樠h,為液,為癭腫i,為樛屈j,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jié),節(jié)者,陰陽(yáng)寒暑轉(zhuǎn)移之機(jī)也。人道有變,其節(jié)乃見(jiàn),節(jié)也者,人之所難處也,于是乎有中焉。故讓國(guó),大節(jié)也,在泰伯則是k,在季子則非l;守死,大節(jié)也,在子思則宜m,在曾子則過(guò)n。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dāng),則不為暢茂條達(dá),而為樠、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yuǎn)哉!
《傳》曰o:“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p。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茍然哉!
(《誠(chéng)意伯文集》卷八,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本)
注釋:
a 諼草:亦作“萱草”,傳說(shuō)是一種使人忘憂的草。
b 環(huán)以象:即象牙環(huán)。《禮記·玉藻》:“孔子佩象環(huán)五寸而綦組綬。”
c 欹:即欹器,古代一種盛水器。水少則傾,中則正,滿則覆。人君常置于座右以為戒。
d 比德:同心同德。
e 懲志:警戒,鑒戒。
f 柯:草木的枝莖。
g 大易:指《易經(jīng)》。
h 樠(mán):滲出貌。
i 癭腫:樹(shù)木外部隆起像瘤子一樣的東西。
j 樛屈:樹(shù)木向下彎曲。
k 泰伯:又作太伯。據(jù)《史記·周本紀(jì)》記載:太伯和弟弟虞仲知道父親想立小兒子季歷為王,以便傳位給季歷之子昌。于是二人逃到荊蠻之地,文身斷發(fā),以讓季歷。昌就是周文王。文王卒,其子發(fā)立,遂克商而有天下。
l 季子:即季札。據(jù)《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吳王壽夢(mèng)有四個(gè)兒子,他認(rèn)為最小的兒子季札賢能,欲立他為王,但季札堅(jiān)決辭讓,于是立了長(zhǎng)子諸樊。吳人被季札的德行所感動(dòng),堅(jiān)持讓他為王,季札乃“棄其室而耕”。后來(lái),諸樊一直念念不忘弟弟季札。他留下遺訓(xùn),將王位依次傳給自己的幾位弟弟,這樣最終就能到季札手里,以實(shí)現(xiàn)父親生前的遺愿。然而,等到哥哥將王位傳給季札時(shí),他再次拒絕,歸隱而去。
m 子思:即孔伋,孔子之孫。據(jù)《說(shuō)苑》記載:子思居住在衛(wèi)國(guó),生活很困苦,穿著很薄的衣服,大半個(gè)月只吃了九頓飯。田子方聽(tīng)說(shuō)了這件事,派人送給子思白狐皮制成的衣服,還說(shuō)了一些理由。但子思不肯接受,說(shuō):“我聽(tīng)說(shuō)與其胡亂送給別人東西,還不如把東西丟到溝里,我雖然貧困,但還不愿意把自己當(dāng)作丟棄東西的溝壑。”這件事體現(xiàn)了君子固窮的理念和子思以死守節(jié)的決心。
n 曾子:曾參,春秋時(shí)期魯國(guó)人,孔子弟子。據(jù)《孔子家語(yǔ)》記載:有一次,曾子修整瓜地,不小心鋤斷了瓜苗,其父大怒,舉起大木棒就打,曾子倒地,很久沒(méi)醒。剛醒過(guò)來(lái),他就向父親請(qǐng)罪。孔子聽(tīng)說(shuō)這件事后很生氣,告訴弟子:“曾經(jīng),舜的父親輕輕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用大木棍打,他就逃跑,因此他的父親沒(méi)有背上不義之名,而他自己也沒(méi)有失去為人子的孝心。如今曾參不顧自己的身體,父親往死里打他,他也不躲避。如果真將他打死,就會(huì)陷其父于不義之中,相比于逃跑,哪個(gè)更不孝?”曾參聽(tīng)說(shuō)了這些話,說(shuō):“我的罪過(guò)很大啊!”
o 《傳》:指《禮記·中庸》。原文為:“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p 裕如:本意是豐足,后用以形容從容而不費(fèi)力。
大意:
古人栽種花草樹(shù)木是有所取義的,并非只是為了好玩。所以栽蘭花,是取它的芬芳;種諼草,是取它的名字含有忘憂的意思;愛(ài)蓮花,是取它生長(zhǎng)在污泥里,卻不染上污穢。不只是花草樹(shù)木,其他如用玉石做佩飾,用象牙做環(huán)圈,將欹器放在座位右邊也是這個(gè)意思。有的人拿它來(lái)比擬美好的德行,借以自勉;有的人拿它來(lái)約束不良的想法,借以自警。這對(duì)于提高道德修養(yǎng)是有幫助的。
會(huì)稽人黃中立喜歡種竹子,是取竹子有節(jié)的意思,因此他在竹林間建了一所亭子,起名叫“尚節(jié)亭”,作為讀書(shū)游藝的地方,淡泊而無(wú)向外鉆營(yíng)的念頭。我見(jiàn)了很喜歡。
竹子這種植物,外表柔弱,當(dāng)中還是空的,卻不會(huì)被風(fēng)雨摧殘折斷,原因是它有節(jié)。至于經(jīng)歷了冬天的嚴(yán)寒、夏天的酷熱,遭受了霜雪的侵襲,仍然枝干不改,葉子不變,顏色依舊青青,像守住大節(jié)而不能使其屈服的君子一般。的確,內(nèi)里有什么也會(huì)表現(xiàn)在外面,因?yàn)樘熨x常常表現(xiàn)在形體上。因此拿節(jié)來(lái)說(shuō)明竹子,還有比節(jié)更值得崇尚的嗎?
世風(fēng)衰敗了,道德淪喪了,能夠憑借節(jié)操立身的人也少了。堅(jiān)持原則又有才能但還沒(méi)有開(kāi)始施展,早早地因崇尚節(jié)操而立下志向,這些人真是有過(guò)人的地方,我又怎能不高興呢?
關(guān)于“節(jié)”字的含義,在《易經(jīng)》里已經(jīng)解釋得十分充分了,用不著另外尋求解釋。花草樹(shù)木的節(jié),確實(shí)是枝葉所生的地方,生氣聚集在那里,筋脈也匯合在那里。所以得到這個(gè)節(jié)的中和之道,就可以順暢茂盛,枝條通達(dá),而長(zhǎng)成美好的植物。如果得不到中和之道,就會(huì)變成流出汁液、生出贅瘤、枝干彎曲的壞草木,從而有損其生命。因此一年中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就是節(jié);所謂節(jié),就是陰陽(yáng)寒暑轉(zhuǎn)移的契機(jī)。在人生旅途中遭遇變故,人的節(jié)操就會(huì)顯露出來(lái);而節(jié)是人很難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的,于是才有合乎中庸的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所以說(shuō),辭讓國(guó)王之位,這件事是大節(jié),在泰伯就做對(duì)了,在季子就沒(méi)有做對(duì);堅(jiān)持到死而不改變,這也是大節(jié),子思這樣做就適宜,曾子這樣做就太過(guò)了。一定要看看怎樣才合乎義,不可固執(zhí)。分辨得不精細(xì),處理得不適當(dāng),就不能暢達(dá)通順,就會(huì)流出汁液、生出贅瘤、枝干彎曲。這不就差得太遠(yuǎn)了嗎?
《禮記·中庸》說(shuō):“在做事前預(yù)先計(jì)劃好,就不會(huì)產(chǎn)生困惑。”平日有所研究,一旦遇到事,處理起來(lái)就自如了。那么,黃中立取竹的含義來(lái)為他的亭子命名,且又和我們這些人交游,怎能是無(wú)意義的呢?
【點(diǎn)評(píng)】
這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文章。首段中,作者以古人種植蘭草、諼草、白蓮,以及用玉作為佩飾,于座位旁置欹器為取義象征,意在自警自勵(lì),并提出“進(jìn)德修業(yè)”的目標(biāo)。
隨后,作者談及黃中立植竹建亭,并將亭命名為“尚節(jié)”之事,意在引出竹子的品格,以映襯人的節(jié)操。
竹子枝干挺拔、修長(zhǎng),既有梅花凌寒傲雪的鐵骨,又有蘭花翠色長(zhǎng)存的高潔,故與“梅蘭菊”并稱四君子,又與“梅松”并稱“歲寒三友”。古今文人墨客愛(ài)竹誦竹者甚多,像王徽之就說(shuō):“何可一日無(wú)此君邪!”蘇東坡則說(shuō):“寧使食無(wú)肉,不可居無(wú)竹。無(wú)肉令人瘦,無(wú)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yī)。”
黃中立和劉基更看重竹子的“節(jié)”。竹節(jié)象征著人的堅(jiān)毅和骨氣。作者所經(jīng)歷的元朝末年,吏治腐敗,社會(huì)風(fēng)氣大壞,所以他在文中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世衰道微,能以節(jié)立身者,鮮矣。”既揭露和抨擊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弊病,又表明自己以節(jié)立身的決心。接著,作者對(duì)“節(jié)”做出進(jìn)一步論述,提出“節(jié)”很難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應(yīng)該合乎中庸的標(biāo)準(zhǔn),即應(yīng)審時(shí)度勢(shì),立大節(jié),重大義。最后,作者以“行前定則不困”加以總結(jié),認(rèn)為這是妥善處理和應(yīng)對(duì)事情的前提和基礎(chǔ)。
縱觀全文,我們不僅領(lǐng)悟到作者立節(jié)重義的決心,也學(xué)習(xí)到了“行前定則不困”的處事方法。如此看來(lái),劉基能夠成就“韜略似孔明”的名臣業(yè)績(jī),是有原因的。(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