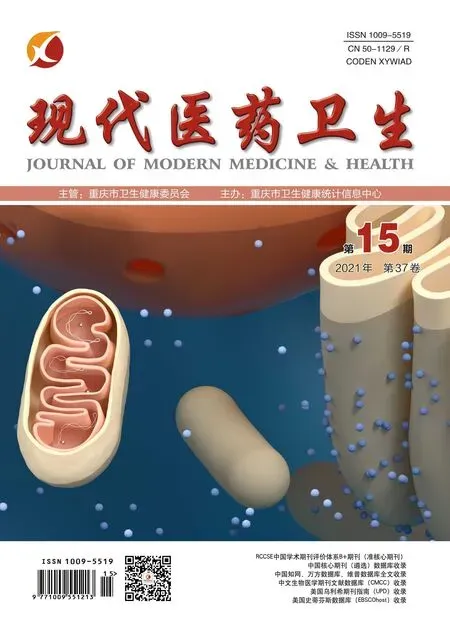經皮腎鏡取石術致胸腔積液2例
黃小龍,潘俊呈,溫 鵬,張思州
(重慶市合川區人民醫院泌尿外科,重慶 401520)
泌尿系結石是泌尿外科疾病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病率在泌尿外科住院患者中居首位[1]。經皮腎鏡取石術(PCNL)作為一種微創術式,在鹿角形腎結石、復雜性腎結石、上段輸尿管結石的治療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隨著PCNL技術的推廣和普及,其相關并發癥的文獻報道也隨之增多,其中以出血、感染、尿膿毒血癥、集合系統損傷為常見并發癥[2]。胸腔積液屬PCNL后少見并發癥,相關文獻報道尚少。本院2017年6月至2020年9月開展PCNL 270余臺次,其中2例患者術后并發胸腔積液,總結其診治體會,以期對該并發癥引起重視,并為臨床醫師提供參考和借鑒,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典型病例
1.1.1病例1 患者,男,46歲。因反復右側腰部不適2年余,體檢發現右輸尿管結石10 d收治入院,既往體健,入院后CT尿路造影檢查示右輸尿管上段結石伴右腎重度積水(結石大小1.0 cm×1.2 cm ×2.4 cm)、右腎多發小結石(較大者直徑約0.6 cm)。見圖1A。胸部正側位數字X線攝影(DR)片檢查示心、肺未見明顯異常。相關術前評估無手術禁忌證,遂在硬膜外麻醉下通過B超引導經第12肋下右腎中盞入路行PCNL,手術順利,手術時間85 min,術中出血約80 mL,術中患者血壓及氧飽和度無明顯異常;術后患者無畏寒、發熱,以及明顯咳嗽、咯痰等,手術前后生化檢查結果示清蛋白均無明顯異常。術后第7天患者訴胸悶不適,右肺聽診呼吸音低,行胸部DR片檢查示右側胸腔中等量積液。見圖1B。在B超胸腔積液定位下行右側胸腔穿刺抽液術,共抽出約650 mL淡黃色液體,胸腔積液送細胞學檢查及抗酸桿菌檢查均無陽性發現,一般細菌培養結果陰性,抽液術后1周復查胸部DR片未見明顯異常。

A.CT檢查示右側輸尿管上段結石、右腎結石及右腎積水;B.胸部DR片檢查示右側胸腔中等量積液。圖1 病例1的術前泌尿系CT及術后胸片檢查結果
1.1.2病例2 患者,男,69歲。因右側腰部反復脹痛不適6年余入院,有高血壓病史1年余,血壓控制尚可。入院后泌尿系CT檢查示右腎鑄形結石。見圖2A。胸部正側位DR片檢查示心、肺未見明顯異常。術前相關檢查無手術禁忌證,遂在硬膜外麻醉下通過B超引導經第12肋下右腎中盞入路行PCNL,手術順利,手術時間120 min,術中出血約100 mL,術中患者血壓及氧飽和度無明顯異常,術后患者一般情況尚可,手術前后生化檢查結果示清蛋白均無明顯異常。術后第6天患者訴右側胸悶不適,右下肺聽診區呼吸音消失,胸部DR片檢查示右側胸腔大量積液,鄰近肺組織外壓性不張。見圖2B。積極給予右側胸腔閉式引流,共引流出約1 000 mL淡黃色液體,送檢胸腔積液細胞學檢查及抗酸桿菌檢查無陽性發現,一般細菌培養結果陰性,胸腔閉式引流治療5 d后復查胸片未見明顯胸腔積液。

A.CT檢查示右腎鑄形結石;B.胸部DR片檢查示右側胸腔大量積液、鄰近肺組織外壓性不張。圖2 病例2的術前泌尿系CT及術后胸片檢查結果
1.2手術步驟 麻醉方式采用硬膜外間隙阻滯,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俯臥分腿位,常規消毒鋪巾,首先經尿道輸尿管鏡于患側輸尿管置入F4輸尿管導管,以便于行人工腎積水或防止碎石過程中結石逃逸;然后B超檢查腎臟、結石及腎臟毗鄰情況,通過B超引導經第12肋下穿刺目標腎盞,置入斑馬導絲,筋膜擴張器逐步將通道擴張至F24標準通道并放置peel-way鞘,置入腎鏡進集合系統尋找結石,使用鈥激光進行碎石,灌洗液為生理鹽水,最高灌注壓力設定為220 mm Hg(1 mm Hg=0.133 kPa),灌流流速為0.6 L/min,術畢于患側留置F6雙J管,經皮腎通道內留置F14腎造瘺管,并放置F16尿管觀察尿液顏色。
2 討 論
PCNL自問世以來因其具有創傷小、術后恢復快、清石率高、可重復性操作等優勢已成為2 cm以上輸尿管上段結石及腎結石的一線治療手段,且在鹿角形腎結石的治療方面PCNL被作為首選術式[3]。然而,PCNL的一些特殊并發癥,如胸腔積液,因其發生率低,臨床醫師往往重視程度不足,嚴重者可引起患者呼吸、循環障礙,甚至直接威脅患者生命安全,增加患者痛苦及經濟負擔。通過總結相關文獻認為PCNL后并發胸腔積液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1)胸膜損傷,灌洗液通過破口直接進入胸腔。解剖上胸膜下界內側端右側起于第6胸肋關節,左側起于第6肋軟骨,兩側均斜向外下,在鎖骨中線與第8肋相交,腋中線與第10肋相交,肩胛線與第11肋相交,終止于第12胸椎高度;穿刺位置過高是導致胸膜損傷的主要原因,據文獻報道,選擇第11肋上、第12肋上、第12肋下穿刺胸膜損傷的發生率分別為35.0%、16.0%、4.5%[4]。因此,選擇第12肋以下的中下腎盞的穿刺通道從解剖學角度可減少胸膜損傷;此外,據文獻報道,B超引導下穿刺較X線定位穿刺能有效降低胸膜損傷發生率,其理由是肺內氣體在B超引導下具有明顯的反射,可顯示肺下界的移動,從而能推測出胸膜下緣的位置[5]。(2)灌洗液外滲,在無胸膜損傷情況下,胸腔積液的發生與灌洗液外滲密切相關,按灌洗液滲出形式不同可分為直接外出和間接外出,直接外滲主要由于術中peel-way鞘在腎實質中或已退出腎臟而腎鏡仍在腎盂腎盞內,peel-way鞘與腎結石未恰當接觸以至于peel-way鞘邊緣出現空隙,灌注液在加壓條件下極易外滲至腎周,再通過胸膜滲入胸腔;間接外滲主要是由于腎盂內壓力大于40 cm H2O(1 cm H2O=0.098 kPa)時可使腎內出現逆流,灌注液將經腎盂-腎竇、腎盂-淋巴管等途徑形成腎周積液,進而滲入胸膜腔[6-7]。國內學者進行的一項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PCNL中灌注壓、灌洗時間、灌洗液量均是導致胸腔積液發生的獨立影響因素[8]。(3)尿源性胸腔積液即胸腔積液的性質實質為尿液,主要發生于PCNL后雙J管引流不通暢或阻塞的情況下,腎臟產生的尿液通過經皮腎通道與造瘺管之間的間隙外滲至腎周,進而滲透進入胸腔[9-10]。(4)低蛋白性胸腔積液,主要由于營養不良、大量失血、肝功能損害等引起低蛋白血癥,血漿滲透壓降低導致胸腔積液的發生。
本文2例患者術前均無肺部疾病及相關手術史,且均采用B超引導經第12肋下建立穿刺通道,2例患者均成功留置雙J管,術后尿量可,且尿色由淡紅色逐漸轉清,未訴明顯腰部脹痛,進而提示雙J管引流通暢,手術前后生化檢查結果均無清蛋白明顯降低,胸腔積液送檢細胞學、細菌學檢查均無陽性發現,術前胸片無陽性表現,可排除腫瘤、結核、感染性胸腔積液的可能,故本文2例患者PCNL后胸腔積液原因考慮為術中灌洗液外滲所致,因對PCNL后并發胸腔積液重視程度不足,術后1周左右當患者出現相關癥狀后才得以發現,及時給予胸腔穿刺抽液或胸腔閉式引流對癥處理后患者癥狀緩解,2例患者均未發生嚴重后果。
綜上所述,為進一步降低PCNL后胸腔積液發生率,作者通過總結分析后認為:(1)采取B超引導經第12肋下穿刺途徑可降低胸膜損傷發生率,術中盡量減小灌注壓力、縮短手術時間及控制灌洗液量,必要時可分期手術;(2)術后良好的止血可減少患側雙J管阻塞,從而減少尿液外滲致尿源性胸腔積液的形成;(3)適時監測肝功能,預防低蛋白性胸腔積液;(4)應格外重視術后胸部查體及聽診,警惕胸腔積液的發生,做到盡早發現,盡早診治,避免病情的延誤和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