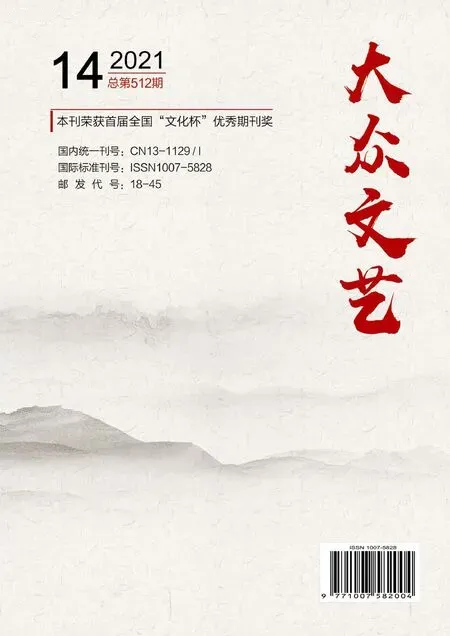新歷史主義視域下論《傾城之戀》
向潤源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傾城之戀》,以其中坎坷的愛戀、孤高絕傲的主人公形象、哀婉而略帶戲謔的筆調等特色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和讀者。不過,小說尚有更為廣闊地解讀空間:小說人物和小說創作者都置身于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中,同時,歷史(城市)也為之傾倒,戰爭被一種軟弱又不甘妥協的“蒼涼”所包裹。本文擬借助新歷史主義的部分核心理論,對《傾城之戀》做“再解讀”,以期通過文本考察滲透于其間的歷史圖景和歷史意蘊。
一、反抗的姿態與妥協的宿命
張愛玲筆下的“傳奇”找尋塵埃中的普通人或具有歷史“遺民”氣質的沒落階層,以他們在大時代中的小悲喜為創作的出發點。張愛玲小說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市井中人津津樂道的奇聞軼事,就像《傾城之戀》中白公館的三姑六婆把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情史當作談資一樣,細碎又冗長。在新歷史主義者看來,這種在時代洪流邊緣的零散插曲實則具備解構、顛覆宏大歷史和主流歷史的力量。
《傾城之戀》“小敘事”的一個突出表現就在于,小說中具有的世俗性以及真實的人性為歷史鋪就了一層民間化色彩,文本中咿咿呀呀作響的胡琴、白流蘇手中的繡鞋針、交際場中的舞姿等一系列的生活元素構成了流動于都市中的民間文化,而這些都不是一時的戰亂和硬性政策所能泯滅的。“敘事就成為解碼和重新編碼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新的比喻模式代替了原初由常規、權威、習慣所編碼的比喻模式。”如果把自抗戰以來主流的民族民主解放戰爭敘事視作“原初編碼”,那么《傾城之戀》中的“新編碼”——戰爭前的經濟問題和自由問題、戰爭中的生存問題、都市民間中根深蒂固的心理積淀——便是更貼近于生活肌理的一種形式。頗為精彩的是小說前半段,寄人籬下的白流蘇精心謀劃一場“翻身仗”,柔弱外表和野心的反差讓這個角色頓生出矛盾性和豐富性,女性的細膩心思和小市民的精打細算都是她的性格標簽。小說把市民文化鑲嵌于具體可感的歷史維度,使市民階層有了發聲的一席之地。
然而,既然社會歷史和各種社會話語等“非文本”能容納文學文本,文本之間可以共生共存,那么文本顛覆性的另一面即是支撐占支配地位的權力觀念,盡管有時候支撐性質是以無意識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民間思想文化的深層肌理實則滲透著千絲萬縷的意識形態。《傾城之戀》的男主人公范柳原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他的身份既不能帶給他以往上流社會的權勢,又無力讓他躋身于新興的市民圈層中,反抗與順應的矛盾性在他身上可以得到較好的詮釋。
范柳原是一個在英國出生的私生子——本就是一個游離于中國正統倫理社會之外的角色,不過,在他虛浮浪蕩的背后更有復雜的深意。他在白流蘇身上,他感受到了一種異乎尋常卻易于流逝的美;淺水灣飯店附近矗立的一堵高墻讓他聯想到天荒地老,但他同時又在預設文明的毀滅;電話里,他吟誦“死生契闊”之后,不無激動地感慨人在外部環境中的渺小,以及對永恒相守的追尋。在新歷史主義者看來,文本記敘的是個人語言的表達,實質上揭示的是一個集體或階層的話語。那面頹圮的高墻,象征著把他所在階級的文化包含其中的文明,而戰爭的侵擾以及社會其他外部力量的沖擊讓一些特定的文化標識化為逝去的滄海一粟。面對劇烈的社會震蕩,范柳原取消了前往新加坡的行程,他在戰爭爆發后握住白流蘇的手,即抓住了毀滅性力量沒有全然遮蔽的微光。
二、兩座城市的相互參照
四十年代,上海與香港密切的互通性和競爭性為兩者互相參照、彼此“審視”提供了契機。敘述自身便是一定信息的傳達,而當兩座城市的豐富性內蘊被容納進文本的敘述機制,它們隨即成為有著特定意義的隱喻符碼,其指示的意義甚或溢出了單一的歷史內容。下文通過小說中的四段場景及其中的對話來展開論述。
第一處是白流蘇抵達香港后,范柳原向她描述香港的飯店。“香港飯店,是我所見過的頂古板的舞場。建筑、燈光、布置、樂隊,都是老英國式,四五十年前頂時髦的玩意兒,現在可不夠刺激了。實在沒有什么可看的……”第二處是范柳原點評白流蘇的穿著:時髦的長背心和西裝都不適合這位女子,滿洲的旗袍相對更合適,可旗袍的線條難以全然展現女性的柔美。建筑的英式風格和西崽的“土洋結合”是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所散發的城市氣質,但對在英國成長的范柳原而言,這僅僅是落伍和蹩腳的城市記號。范柳原欣賞白流蘇身上的上海風韻,換言之,范柳原傾向于對上海文化,尤其是舊上海文化產生更多認同。
但是,香港也對上海“施加”了影響。小說中相關的第三處場景是印度的薩黑荑妮公主說白流蘇“倒不像上海人”。身在他鄉(香港),又收到了“異域之人”(印度公主)的評價,白流蘇唯有戲謔自己原本只是個鄉下人。著名的“張學”研究者李歐梵曾撰文《雙城記》,認為香港承受著來自英國殖民者和中國上海人的雙重注視。那么《傾城之戀》中,上海以白流蘇為符號,便承擔著來自外國和中國香港人的雙重評判。第四處場景是結尾處,上海白公館的四奶奶要和四爺離婚,原因是白流蘇離了婚再嫁,在香港竟能重新風光起來。從該處的敘寫來看,香港開放的社會風氣還是或多或少改變了當時半傳統的上海人的觀念。
根據上述摘取的四個小說場景,我們可以進一步展開推論。首先,文學文本與歷史具有“互文性”,《傾城之戀》對兩座城市形態面貌的側面呈現可以和它們的現實情況相互闡釋與補充。自19世紀40年代始,香港就歷經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化過程,其間的文化既不可能完全西方化,又比中國大陸的文化多了一些欲望元素、金錢化和娛樂性的元素。上海是一個被瓜分的通商口岸,文化領導權的爭奪促使這座城市快速裂變生長,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及公共租界等區域有聯絡又有差異。當然,張愛玲更傾向于表現上海的歷史文化底蘊。其次,即使是在同一文本內,同一地域的社會狀況也會從不同的人物視角看出不同的內涵。“文本的意義是各方話語‘談判’后形成的‘協議性’產物,對它的闡釋是一種多聲部、社會性和對話性的文本闡釋”。上海借助于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的投射的香港經歷而獲得文化意蘊,香港借助于小說中的人物情感波折而凸顯城市歷經戰火依然頑強的生命力。
三、“歷史”敘事背后的主體性
“蒙特洛斯強調能動與自主性的統一,因為主體既受歷史的制約處于歷史的長河中,又超越于歷史之外能對歷史做出深切的反思,并對歷史文化話語進行全新的創造……”《傾城之戀》觸及了一個對歷史進程有根本性影響力的主題——戰爭。戰爭對小說人物和創作者的意義不只是她們活動的背景,戰爭成全了白流蘇的婚姻計劃,戰爭給了張愛玲深沉的時代體驗,但是,《傾城之戀》并沒有成為一篇典型意義上的革命文學文本,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張愛玲在大時代中獨特的主體意識,她的歷史觀形成于別致的歷史審理視角,并結合了個人的“小歷史”。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蘇——張愛玲運用了“倒置”的歷史敘述,讓一座城市變成了歷史的主角,城市的傾覆具有強大的歷史作用,即小說強調了歷史勢能的主動性質,動蕩不安的勢能轉換囊括并影響到了瑣碎幸福實現的可能。另一方面,香港淪陷成全的“她”是一個在偌大歷史洪流里只愿追求現世安穩的女子,這就讓歷史的沖突性質有了些許調和。白流蘇曾經有的私欲、野心和周旋都隨著時光的流轉而消弭,社會現實轉變了她的生活態度,她調整生活腳步的姿態也是歷史中的驚鴻一現。誠然,張愛玲非常注重罹難之人的生命體驗,側重于描畫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市民,但這不是否定其作品的思想縱深性的依據。“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親近,和戀愛一樣是放恣的,滲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對于自己是和諧。”在張愛玲看來,歷史的廢墟上開出的花必定是經久不衰的,于是她選擇讓俗世中的人性人情留有印記,致力于記述或創造被時代飛揚情緒所忽略的深層安定力量。
正是由于歷史是諸多眾聲喧嘩的碎片的匯合,張愛玲便在此基礎上運用一定的修辭策略去闡釋歷史。“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里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白公館被描寫成有其自身“時間流”的場域。“對歷史意識、闡釋框架和語言詩意的想象和合理虛構”,營構出了白公館成員為典型的沒落門閥的精英心理圖式,時間不合常理的緩慢流逝,是歷史在文本中留給這些人物多余而虛無的烏托邦,它最終會在不動聲色的日常里幻滅為悲劇。
《傾城之戀》的內容和張愛玲的心境吻合,都透露出一種時不我與、歷史流遁于無形的荒涼感。小說中,白流蘇在白公館受氣后在鏡子前顧影自憐,同時,外面的胡琴被作者賦予深意,那些被演奏的忠孝節義的故事好似不與白流蘇同在一個時空。張愛玲塑造的“遺老遺少”形象和她個人的身份、遭際有一定關聯,胡琴與笙簫琴瑟喚醒了屬于她的時代的邈遠記憶。通過連接自我主體與歷史,歷時性的歷史脈絡被截取為共時性的片段而受到一種總體敘事的統領,張愛玲把偶然的、中斷的、非連續性的時代內容放置在一個整體文化的意義空間里,呈現滲透在相互對話的歷史情境中的文化象征意義。
四、結語
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結合新歷史主義理論主張分析《傾城之戀》,能讓小說的美學藝術價值有厚重的歷史現實依托。在既定的有關40年代的歷史知識和敘述中,階級話語和革命主題占據絕對的核心地位。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另辟蹊徑,在“小敘事”“小歷史”中鋪開文本,展現出迥異于“左翼”文學、“新感覺派”等創造的文學景觀。《傾城之戀》是戰爭和特定經濟文化形勢下的產物,這一文本在歷史的隱微處能動地構建了一個傳奇世界,給歷史真實面目的彰顯提供了一個窗口,也讓虛構和想象參與了歷史文化象征意義的塑造過程。
注釋:
①(美)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76頁.
②⑥張愛玲.《傾城之戀》.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66,49.
③孔凡娟.《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研究新論——袪魅后的文本、對話與審美》.學術界,2017(04):180-188.
④⑦王岳川編.《20世紀西方文論研究叢書 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178,204.
⑤張愛玲.《自己的文章》,陳春生,劉成友選編;特約編委陳美蘭.20世紀中國文學史文論精華:小說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