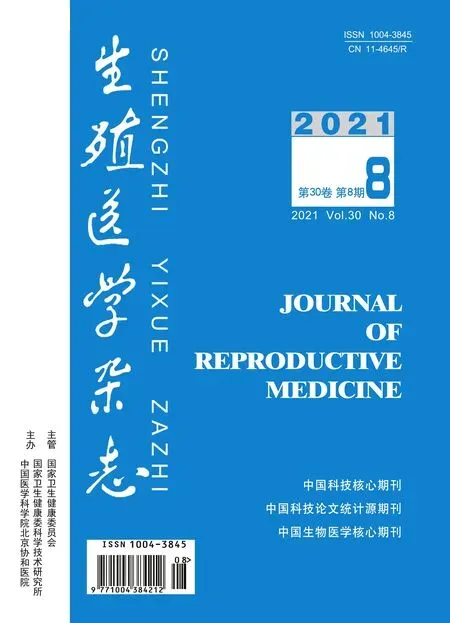miR-141調控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研究進展
謝韜,張燕,楊碧蓉,何培芝,周華*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1.婦科;2.超聲科,上海 201203)
子宮內膜異位癥(endometriosis,EMS)是婦科常見的疑難病,以子宮內膜生長在宮腔以外的部位為特征,與盆腔疼痛和不孕癥相關,常見于育齡期婦女,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1]。EMS的發病機制復雜,主要被認可的是國內學者提出的“在位內膜決定論”學說;EMS的發病遵循“3A”程序(attchment-aggrassion-angiogenesis)即子宮內膜通過粘附、侵襲、血管生成的過程在異位形成病灶[2]。微小RNA(microRNA,miRNA)是長度為20個左右堿基的小的非編碼RNA,其轉錄后可以調控基因的表達,作用于正常生理活動和疾病的病理過程。微小RNA-141(miR-141)被發現在EMS和正常內膜中表達存在差異,提示其有望用于EMS的無創診斷[3],且miR-141能夠靶向作用于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進而影響EMS的發病過程。現就miR-141與EMS發病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
一、miR-141概述
miRNA是一類內源性的小分子非編碼RNA,其長度為21~25 nt,結構高度保守。在生物體信息傳遞的過程中,其能夠結合靶mRNA分子中特定的互補序列從而抑制靶mRNA的翻譯或促進該mRNA的降解,達到下調該mRNA編碼蛋白表達水平的調節效果[4]。miRNA的加工開始于細胞核中,過程可劃分為如下幾步[5]:(1)經過RNA聚合酶Ⅱ(POI Ⅱ)轉錄形成最原始的結構:長度幾百nt到幾千nt不等、具有“莖環”(stem-loop)的原miRNA(pri-miRNA)。(2)細胞核內的RNA酶Ⅱ型核酸內切酶Drosha與雙鏈RNA結合蛋白DGCR8結合形成復合體,該復合體能夠切割原miRNA結構上的“莖環”,得到了長度為70 nt,形似發卡的前體miRNA(pre-miRNA)。(3)前體miRNA被核轉運蛋白Exportin5(XPO5)從核內轉運至細胞質中。(4)在細胞質中,RNA酶Ⅲ型核酸內切酶Dicer將“發卡”上的環形結構去除得到不對稱雙鏈miRNA(miRNA duplex),后者長度為22 nt,分別為3p鏈、5p鏈。(5)miRNA duplex載入AGO蛋白中形成前體RISC(pre-RISC)。(6)成熟RISC形成:解螺旋酶作用于pre-RISC,miRNA duplex雙鏈結構被打開,其中一條鏈被保留形成向導鏈(guidestand)結合靶mRNA形成成熟的RISC,達到抑制靶mRNA翻譯或切割降解靶mRNA的作用。
miR-141屬于miR-200家族(miR-200a、b、c、miR-141及miR-429),研究已經證實miR-141能夠作用于不同的靶點調控不同信號通路,進而調節一系列的生理過程,如細胞的生長凋亡、血管生成、新陳代謝等[6-7]。近年來研究指出miR-141與EMS的發病密切相關,miR-141在EMS中存在差異表達,且參與EMS發生發展的多個環節如增殖凋亡、組織缺氧炎癥、粘附侵襲、血管生成等[8]。
二、EMS“在位內膜決定論”
EMS發病機制復雜,曾有Sampson提出了經血逆流種植學說為主導理論,亦有上皮化生學說、遠處轉移學說、免疫激素炎癥等學說,但都無法完整地解釋EMS的現象。近年來國內專家提出“在位內膜決定論”得到廣泛的認可[9]。EMS具有類腫瘤特性,可以經過癌前的“不典型”過程最終惡變。EMS中的在位內膜相當于癌癥中的“原發灶”,在位內膜細胞經過上皮間充質轉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細胞極性發生改變因而具有轉移和侵襲性,主動或伴隨著經血逆流被動遷移至腹腔。異位內膜要在盆腹腔等處形成病灶(相當于癌癥中的“轉移灶”)必須完成“3A”步驟:(1)粘附(attachment)在盆腹腔腹膜或其他臟器表面;(2)侵襲(aggression)突破細胞外基質;(3)血管生成(agiogenesis)。“3A”程序符合EMS的臨床病理表現:早期紅色病變、典型黑色病變和后期白色病變。研究發現miR-141能夠扮演“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角色在惡性腫瘤發病機制中發揮調控作用[10-11],結合EMS的類腫瘤特性,為論證miR-141通過“3A”程序調控EMS的假說提供了思路與依據。
三、miR-141與EMS
miR-141被發現在EMS和正常內膜中的表達存在差異,且血清中miR-141結合脂類等以復合物的形式穩定存在[3],其有望用于EMS的無創診斷。陳觀盛等[12]應用TaqMan microRNA array方法對EMS患者和對照組的血清樣本(EMS組60例,對照組25例)進行檢測,發現6種miRNAs表達存在明顯差異,相較于對照組,miR-141在EMS組表達顯著下調。為了探究miR-141在EMS診斷中的價值,學者們進一步評估了血清中miRNA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OC曲線),其中miR-141截斷值對應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分別為71.69%和96.00%,具有一定的診斷準確性,提示EMS患者血清中低表達的miR-141可能作為診斷EMS的血清標志物,為臨床EMS預測、診斷及預后引入新方法。另外,Rekker等[13]指出miR-141的水平會隨采血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不論是EMS組還是正常組,清晨采集血清標本中的miR-141水平顯著低于夜間采集的標本。因此將miR-141作為生物標志物進行研究時應當考慮取樣時間。
四、miR-141參與EMS的機制
1.miR-141靶向調控TGF-β:實驗研究已經證實在EMS中miR-141靶向的下游分子是TGF-β[14]。TGF-β是人體內主要的致纖維化因子,由巨噬細胞合成并分泌,主要作用是調節細胞增殖、分化和凋亡以及組織纖維化、創傷愈合、血管生成過程[15]。TGF-β在EMS中以TGF-β/Smad信號通路的形式參與信息的傳遞[16-17],調節EMS的細胞增殖、凋亡、纖維化等病理過程。經典的TGF-β/Smad信號通路包括:(1)TGF-βⅠ、Ⅱ型受體倆倆形成的異源四聚體復合物與TGF-β結合后被激活;(2)Smad2、Smad3募集到Ⅰ型受體上被磷酸化后又脫離;(3)隨后進入胞漿中與Smad4共同形成三聚體復合物;(4)該三聚體復合物進入細胞核中與DNA上的Smad結合元件區域結合誘導轉錄;(5)轉錄結束后,Smad復合物解離,R-Smad(調節型S-mad)重新回到細胞質中,完成“Smad循環”。在EMS患者的病灶中可以觀察到腹膜、血清以及腹腔液中TGF-β的表達增強,顯示TGF-β在EMS的建立或維持中可能發揮關鍵作用[18]。
2.miR-141與EMT:上皮細胞在轉化中失去了上皮表型獲得了間質表型,因此失去了屏障保護作用,細胞運動能力增強進而更容易轉移、侵襲[19]。在EMT的過程中,細胞表面上皮標志物E-鈣粘蛋白(E-cadherin)等表達下調,間質標志物波形蛋白(vimentin)等表達上調,上皮細胞失去細胞極性,細胞間的連接被破壞,胞內肌動蛋白骨架重組。由于EMS的類腫瘤特性,近年來對EMT的研究逐漸從腫瘤領域轉移至EMS方向,子宮內膜細胞發生EMT是對“經血逆流異位種植學說”的重要補充。馬雪松等[20]分析認為EMS中存在兩種類型的EMT:2型和3型。前者主要參與慢性炎癥反應促進纖維化過程,而后者被認為是腫瘤轉移的主要發生機制,這種機制還與血管生成密切相關。3型EMT促使腫瘤細胞發生一系列具有轉移級聯特征的程序,影響內皮功能、血管通透性以及動物實驗中EMS的發展[21]。在腫瘤領域已經證實了miR-141在EMT過程中扮演抑制的角色[22]。Gregory等[23]發現miR-141抑制了E盒結合鋅指蛋白1(zinc finger E-box binding homeobox1,ZEB1)和ZEB2的轉錄過程,進而使得E-鈣粘蛋白表達下調激活了EMT。ZEB1、ZEB2是E-鈣粘蛋白mRNA的轉錄抑制分子,在細胞上皮間充質轉化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24-25]。而在EMS病理過程中,有研究指出TGF-β激活下游Smad2信號通路介導了EMT過程,miR-141的表達水平升高會抑制EMT[26]。另外有學者發現,在EMS中miR-141也可以直接靶向ZEB1、ZEB2發揮調節作用[27]。綜上,miR-141靶向作用于下游的分子TGF-β和ZEB1、ZEB2,通過抑制TGF-β/Smad信號通路或直接阻斷轉錄過程,最終造成E-鈣粘蛋白的表達下調,以此參與了EMS中EMT的發生發展。
3.miR-141與“3A”程序:TGF-β是增加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ECM)最重要的細胞因子,也是最強的致纖維化因子[28]。TGF-β能夠促進細胞粘附蛋白和粘附蛋白受體的轉錄和翻譯,提高它們對ECM的粘附,使得異位的子宮內膜細胞更易于粘附在盆腔組織等處[29]。Soni等[18]在試驗中證實當加入額外的TGF-β以促進其過表達時,小鼠EMS模型異位內膜組織中整合素(integrin)表達增強,整合素是“3A”程序里粘附(Attachment)過程的重要標志物,推測TGF-β增強整合素的表達水平進而促進了EMS的粘附過程。此外,TGF-β可以活化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使得異位內膜組織能夠在病灶周圍形成微血管,完成內膜的“異位種植”[30]。最新研究發現miR-141存在調控網絡(多條信息傳遞途徑)抑制血管的生成過程[31]。其中信號傳遞通路包括:(1)miR-141→TGF-β2→ALK1,5(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血管生成;(2)miR-141→GATA6(鋅指轉錄因子6)→TGF-β2→ALK1,5→血管生成;(3)miR-141→GAB1(接頭蛋白1)→Grb2(生長基因受體結合蛋白2)→VEGFR2→血管生成。血管生成是指在原先已經存在的血管中以發芽或非發芽的方式產生新的血管,過程涉及到微血管基底膜和ECM的降解、血管內皮細胞的遷移及增生分裂、新的原始細胞分化成熟,最后在血流的沖擊下形成了新的毛細血管。VEGF是最關鍵的刺激因子,能夠促進微血管、小血管通透性增加、血管內皮細胞分裂增殖、細胞質鈣聚集以及誘導新生血管生成,是“血管生成”(Angiogenesis)過程的標志物。miR-141通過調控這些蛋白表達,參與了多個細胞信號通路的調控,其中包括調控纖維化最重要的TGF-β/Smad信號通路,該通路促進了異位子宮內膜的粘附、侵襲和血管生成,促使異位病灶的形成。上調miR-141的表達水平能夠抑制TGF-β的活性進而抑制EMS的發生發展。
五、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以miR-141為切入點,探究其生物學功能與EMS發生發展的關系,得到假說如下:EMS中的在位子宮內膜經過EMT獲得侵襲的特性,隨經血逆流入腹腔中,經過粘附、侵襲和血管生成的過程形成異位病灶。上調miR-141的表達水平,可以靶向抑制TGF-β的活性,進而抑制了TGF-β/Smad信號通路的激活,阻止了EMS的發生與發展。然而,是否存在其他受miR-141調控的信號傳導通路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miR-141在EMS中的差異表達,使得其有望成為EMS治療的新靶點,并為臨床上EMS機制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