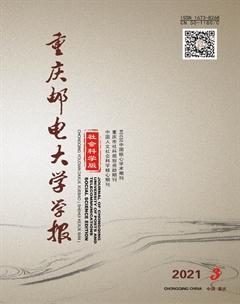戲劇性與情節性:電視劇審美接受的二元思辨
李軒
摘 要:戲劇性與情節性,是故事敘述不可或缺又相互補足的二元審美特質,共同構成敘事藝術的核心審美范疇。相較戲劇、電影,電視劇的戲劇性與情節性更豐富易感、關系更密切復雜,戲劇性與情節性的表現強弱和價值優劣,往往決定著電視劇作品藝術水準的高低。電視劇審美接受過程中,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偽劣失實、斷裂失衡、同質失趣等問題,會影響作品的敘事表達,進而造成受眾審美感知錯位。為此,須以優質互娛、動態互融、多維互生等策略意識對其予以糾偏重塑,復歸動態平衡。結合創作實踐來看,近年來,國產劇在敘事層面發生著顯著的“情節化轉向”,“戲劇性耗散”與“情節性熵增”即為其外化。針對于此,國產劇優質生產的進一步實現,既離不開戲劇性與情節性的關系重構,又應采新規、用新策、走新路。
關鍵詞:電視劇;敘事藝術;審美接受;戲劇性;情節性
中圖分類號:J9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21)03-0134-09
一出好戲的誕生,須達至“有戲”之意境,有立體可感的人物性格、激烈碰撞的矛盾沖突、意味深長的情境烘托等戲劇性場面,給人以凈化心靈的審美沖擊;也須成其“有看點”之奧妙,有合理可信的行動組織、細膩描繪的事件展演以及趣味性、懸念感等多重效果構成的情節性場景,給人以持續吸引的審美愉悅。過往相關的學術研究中,一方是就戲劇談戲劇性,另一方是就情節談情節性,因戲劇作為藝術形式和情節作為敘事單位這一概念由來上的不同,戲劇性與情節性常被分而論之。其實,戲劇性并不為戲劇所獨有,情節性也不可完全與情節混同,敘事藝術的審美接受中二者本就互融互補、對立統一,因而不能一概割裂而談。伴隨著當代藝術形式化潮流的紛涌,不少藝術樣式對戲劇性與情節性的體現已不如過往,尤其是在日趨先鋒化和實驗化的戲劇敘事和電影敘事中,戲劇性與情節性的“重量”愈發微薄。較之戲劇、電影,電視劇需要更“足量”的情節性場景和戲劇性場面,以維持內容體量、保持敘事彈性、體現作品精神主題、強化表現感染力,因而電視劇的戲劇性與情節性自然更具研究探討價值。那么,戲劇性與情節性當如何界定、電視劇的戲劇性與情節性的概念及其關系為何、戲劇性與情節性間的失位失當是怎樣影響電視劇的價值表達、當前國產劇內容生產中的相關現象又當如何解讀?為回答這一系列問題,本文在對敘事藝術中戲劇性與情節性做簡要界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電視劇藝術的發生語境,探析電視劇戲劇性與情節性間強弱與優劣的辯證關系,分析二者對電視劇種種美學癥候產生的影響,并提出與之對應的重塑意識,進而以此為理論基點解讀當前國產劇敘事的“情節化轉向”。
一、“審美接受”:敘事藝術的戲劇性與情節性
敘事藝術作品經典性的產生,離不開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共同作用。以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西游記》為例,唐僧師徒四人在西天取經過程中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劫難情境產生意味著新敘事單元形成,每一個敘事單元均須由特定情節線索和事件轉折組合推動,《西游記》的引人入勝即來自險象環生又逢兇化吉的情節性體驗。通過人物性格及沖突矛盾的塑造刻畫,《西游記》令人難忘且最為人稱道的戲劇性場面當屬“大鬧天宮”和“三打白骨精”。“大鬧天宮”中,齊天大圣孫悟空與天庭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的沖突對抗產生出精彩絕倫的擒縱斗法情節,同時孫悟空桀驁不馴、剛直不屈的性格也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三打白骨精”中,白骨精化身一家三口魅惑離間的情節驚異效果十足,由此導致大徒弟孫悟空和師傅唐玄奘的分道揚鑣讓人不免惋惜。相較于《西游記》其他章回,情節性與戲劇性俱佳的“大鬧天宮”和“三打白骨精”堪稱是傳世經典中的璀璨明珠,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何唯獨這兩個章回能在后世文藝改編中更受青睞。
(一)瞬息外現的戲劇性
人類社會中,無論是先民時期還是當下,戲劇性故事總是綿延不絕地發生。日常生活中戲劇性一詞,便常被用以形容出乎意料的轉折和飽含深意的事件。之于敘事藝術,凝練戲劇性相當關鍵,如在索福克勒斯的戲劇《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遭命運捉弄不幸陷入殺父娶母的人倫絕境,上演人與命運對抗的無奈悲劇;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阿喀琉斯因性格自大拒絕出戰導致希臘聯軍慘敗和好友身亡,暗顯出英雄性格的因果注腳。回望藝術發展的歷史長河,戲劇性諸成說更是各有所向,然而,其中關鍵還是在于把握戲劇性的“人性價值和審美內涵”[1],戲劇性“不是光在戲劇中得到體現,它還在所有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藝術門類中比如電影和詩歌文本中出現”[2],戲劇性體驗也并非受敘事媒介嚴格約束。
正如薩塞在《戲劇美學初探》中所言,不管是什么樣的戲劇作品,寫出來總是為了給聚集成觀眾的一些人看的;這就是它的本質,這就是它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3]。威廉·阿契爾亦有與之相近的觀點,他在《劇作法》中提出,能夠使聚集在劇場中的普通觀眾感到興趣就是“戲劇性”的[4]。而在《論戲劇情節》中,古斯塔夫·弗萊塔克寫道:“所謂戲劇性,就是那些強烈的、凝結成意志和行動的內心活動,那些由一種行動所激起的內心活動。”[5]關于這種內心活動,喬治·貝克在《戲劇技巧》中認為:“外部動作或者內心活動,其本身并非‘戲劇性的。它們能否成為戲劇性的,必須看它們是否能自然地激動觀眾的感情,或者通過作者的處理而達到這樣的效果。”[6]由此可見,戲劇性的生成關鍵即在于受眾審美感知,其真正達成須由體現人物內心活動的戲劇動作激起受眾的審美心理活動。
對于戲劇性的本質,黑格爾的認識及思考或許更為切近,他提出:“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一些個別具體化為生動的人物性格和富于沖突情境的抽象目的,這些目的在顯示自己和實現自己的過程中互相影響,互相制約——這一切都要在瞬息間陸續地外現出來。”[7]可以發現,作為一種審美特質的戲劇性,其本質是通過創造具有“瞬息性”特點的不同審美形態與受眾完成審美交流互動。這一“瞬息性”并非指藝術客體要在盡可能短的瞬息之間呈現沖突,而是藝術客體通過盡可能巧妙的設計令受眾可以在觀賞過程中于瞬息間捕捉到性格、沖突、矛盾、情境等內容的深層意指和象征意涵,在內爆式的敘事信息接受獲取中形成情感共鳴和情緒共振,并在體會尋味“陸續地外現”過程中對此細加品讀。
(二)漸次延展的情節性
在《論情節》中,冉欲達曾為情節正名道:“對情節曲折的戲劇、電影,以所謂的‘情節戲予以否定或貶低是不公允的,藝術作品沒有動人的情節很難塑造出真正動人的性格,真正好的作品無一不是以曲折動人的情節而征服了千百萬讀者和觀眾。”[8]一般情況下,情節堆砌會被認為是藝術性匱乏的表現,故對情節功用的普遍理解也易流于負向,而當情節尚不能獲得應有認可時,更勿論情節性。此外,因情節性與情節在一般使用上較為接近,故而使得情節性往往隱而不彰,多被視作情節的功能加以討論,較少得到重視。但事實上,在敘事藝術中,不僅情節的形式功能不容替代,情節性的審美意義亦不容忽視。
然欲辨識情節性,必先對情節有清楚認知。早在《詩學》之中,亞里士多德就提出:“情節”是悲劇中最重要的成分;組合精良的情節不應隨便地起始和結尾,而是應該符合完整劃一且有一定長度的行動模仿的悲劇構成的要求[9]88;情節有簡單和復雜之分,構思精良的情節必然是單線的且應該表現人物從順達之境轉入敗逆之境[9]97,并由情節本身的構合引發恐懼和憐憫[9]105。而對于情節的判定,黑格爾則認為:“主體性格對情境的掌握以及它所發出的反應動作,通過這種掌握和反應動作,才達到差異對立面的斗爭與消除(矛盾的解決)——這就是真正的動作或情節。”[10]結合古典理論和當前藝術實踐來看,情節不是動作而是行動,是一段完整的、由始至終的行動,且人物是構成和推動情節發展的中心;行動由人物執行,人物的性格、關系及與情境間的矛盾沖突是行動發展的動機;消除矛盾、回歸平衡秩序是人物行動的歸宿,由人物的情境反應動作形成的系列行動將產生沖突矛盾的不平衡因素完全消除,是一段情節真正完成的標志。在此,可將情節簡單定義為:以性格鮮明人物的行動為基礎,由若干行動事件組成,為沖突矛盾、因果承繼等多重因素推動,并總是處于“平衡——不平衡——平衡”的發展演進中,最終通過矛盾克服實現情節整一。
情節是一項敘事功能單位,是故事結構的基礎組成部分。情節性不完全同于情節,相較于表意功能,它代表著觀賞體驗的審美效果,非情節、反情節敘事之中亦可存有情節性。略加辨析后即可發現,無論是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同情、恐懼、憐憫,還是黑格爾意義上對立面消除產生的快感,其所指已超出情節的功能范疇,這種由情節激發的審美效果正是情節性。作為一種審美特質的情節性,其本質是通過創造漸次延展的審美體驗,提供快感享受、滿足認知意識渴求。受限于情節進展的流程脈絡,受眾難以在短時間內一窺情節全貌,只能選擇跟隨情節走向,在情節的構合與完成中得到娛樂。敘事藝術的情節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情節組成構造的特殊性,內部各具特色的新奇事件可激發觀看欲望,外部各不相同的情節主題可創造差異化的觀賞體驗;二是情節發展的整一性,首尾呼應、事件銜接、節奏控制等要素是情節成立的關鍵;三是多情節的結構性,即情節與情節之間的框架聯系,關乎故事整體的完善。
(三)訴諸審美、趨于二元
戲劇性,如同令人難忘的瞬間,充斥著象征意味且滿含詩意;情節性,如同人所必經的成長歷程,曲折發展且運動變化。戲劇性與情節性之所以能共存于不同的敘事藝術樣式,是因為它們不是特定藝術的獨門手法,而是具有情感調動力的審美特質。如朱光潛所言,審美范疇往往是成雙對立而又可以混合或互轉的[11]。瞬息外現的戲劇性與漸次延展的情節性,是敘事手法的藝術升華和受眾審美期待的產生源泉,二者共同構成敘事藝術的核心審美范疇。同時,敘事藝術中的戲劇性與情節性也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二元關系結構。一方面,基于審美特性差異,戲劇性與情節性相互區別,戲劇性注重“瞬息性”,情節性注重“延展性”;另一方面,戲劇性場面多呈點狀分布,須依托情節線索串聯才能貫通;情節性活動多呈線狀演進,須借助戲劇性張力再造新變。
二、“關系辯證”:電視劇的戲劇性與情節性
電視劇作品中的“名場面”,多是飽含戲劇性的。以電視劇《亮劍》為例,該劇最為經典的橋段當屬第14集李云龍率部“打平安縣城”,堪稱是對譚霈生先生以人物性格為中心,通過戲劇動作、戲劇沖突、戲劇情境、戲劇懸念、戲劇場面以及結構的統一性來呈現戲劇性的觀念[12]的完美詮釋。在人物性格上,李云龍選擇攻打縣城的直觀動機是救妻報仇,充分體現出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在戲劇動作上,當八路軍兵臨平安城下,日軍在城門樓上挾持李云龍妻子秀芹威脅撤軍,李云龍不懼威脅大聲下令開炮,飽含張力的動作中暗示著其內心抉擇的巨大苦痛;在戲劇沖突上,八路軍與日軍斗爭的激化,渲染出一觸即發的大戰氛圍;在戲劇情境上,抗戰時期中日雙方尖銳的民族矛盾被重點突出,符合歷史語境;在戲劇懸念上,包括李云龍能否救出妻子,李云龍部能否取勝,以及八路軍及友軍部隊能否阻敵增援;在戲劇場面上,以李云龍部為明場,其他戰斗為暗場,穿插戰役雙方的增援阻擊,側面呈現出整個晉西北戰局的劇烈波動。此外,這一段落中也不乏情節性,其中八路軍獨立團六連、縣大隊與縣小隊、孔捷部、丁偉部以及國軍楚云飛部等隊伍阻擊日軍的場面即為各具特色的情節,全部圍繞著李云龍部行動展開,以烘托戰斗氣氛、強化表現力。通過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協調搭配,《亮劍》將頑強不屈的抗戰意志和民族精神予以了完美呈現。
(一)電視劇的戲劇性
一般審美感知上,電視劇的戲劇性與其他藝術形式的戲劇性雖同構同源,但受自身藝術特征和媒介特性影響,必然具有相區隔的“電視化特質”[13]。就戲劇而言,舞臺上人物所處的時空環境相對固定,動作直觀可見,其戲劇性呈現自有其內在規律;但對于電視劇來說,若沒有蒙太奇、長鏡頭等鏡頭語言,僅是單純使用固定鏡頭拍攝,用紀實手法重現戲劇,電視劇的戲劇性就不能成立。而且,電視劇藝術的敘事時空相對廣闊,景別、構圖、調度等鏡頭語言能更好地表現人物動作的關聯意指,為戲劇性表現提供新可能。基于此,有學者將電視劇的戲劇性定義為“劇中人物在屏幕藝術情境中展開有機的動作或行動,導致各類矛盾沖突或產生新的情境,讓整個過程富有懸念,吸引著觀眾洞察人物的性格特征與精神世界”[14]。受眾對電視劇戲劇性的審美感知生成,則需由以人物動作為中心的戲劇化手法和以鏡頭語言為基礎的視聽化技巧共同作用。作為電視劇藝術的一般審美范疇,戲劇性在電視劇中主要由因果性、悲劇性、崇高性、諷刺性、批判性等審美感知形態體現,如因果性給人以揭示、悲劇性給人以凈化、崇高性給人以莊嚴、諷刺性給人以反思、批判性給人以力量等。
(二)電視劇的情節性
電視劇展現給觀眾的是可視的或可聽的行動,即由人物、環境及人物與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情節。考慮到電視媒介的傳接習性,以及它與其他藝術形式的受眾爭奪,電視劇很自然地會以對情節的進一步重視作為應對措施[15]。電視劇長篇化的敘事“高容量”,需要大量情節參與內容的構織填充。作為電視劇藝術的一般審美范疇,情節性是電視劇通俗化和娛樂化的征候,在電視劇中主要表現為生活性、傳奇性、懸疑性、對抗性等審美感知形態,如生活性細構時空環境、傳奇性強化故事魅力、懸疑性創造精神吸引、對抗性突出動作效果等。受眾對電視劇情節性的審美感知生成,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結構性,電視劇的主線情節須脈絡清晰,支線情節須枝繁葉茂、多重構合,如在懸疑劇、警匪劇等情節性依賴較重的類型劇中,多情節間的關系互動所產生的意義和價值勢必遠超單一情節,嚴謹合理有邏輯的情節結構作用突出;二是整一性,即情節構造必須是獨立完整的才能創造意義,電視劇情節刻畫的彈性空間較大,可通過鏡頭組接進行表意,也可由倒敘、閃回、拼貼等敘事形式間接呈現,或短或長的情節被賦予各異的強度、密度、曲折度;三是特殊性,電視劇情節的構成要素極為豐富,無論是劇本、畫面、音樂,還是服裝、布景、道具,任何與情節敘事有關的細節元素均可通過藝術加工表達特殊意涵,使情節別出心裁、獨具一格。
(三)強弱之分、優劣之別
電視劇的戲劇性與情節性,存在強弱、優劣的辯證關系,既指審美表現上的強弱之分,又指審美價值上的優劣之別。強與弱、優與劣,出于文本、成于受眾。戲劇性強,其審美價值可以是優,也可能是劣;情節性弱,其審美價值可能是劣,也可以是優。
其一,戲劇性強、情節性強。此類電視劇的突出特征是具有豐富的戲劇性事件素材和體量龐大的情節支線,代表類型是歷史正劇。通過對歷史史實的藝術再造賦予作品厚重史詩感,借助群像人物和系列事件增添情節性效果。
其二,戲劇性強、情節性弱。此類電視劇篇幅多精煉簡短,如單本劇、電視短劇、微型系列劇等。受限于篇幅短促,此類電視劇一般不會大量增添情節線,而是將重心放在矛盾沖突集中的重場戲和高潮點上,細加營構戲劇性。
其三,戲劇性弱、情節性強。此類電視劇以情節表現為主要敘事手段,如在系列劇中,每集一個新故事的特點,使其對新生事件及情節存在依賴。此外,懸疑劇、推理劇等以情節化為主要特征的類型劇中,隨著其情節體系和類型程度的提升完善,情節性也會隨之增強。
其四,戲劇性弱、情節性弱,此類電視劇多以藝術化、紀實化為特征,作品文藝氣息濃厚,常采用非戲劇性和非情節性手法進行敘事。事實上,電視劇并非完全與先鋒探索絕緣,通過實驗性手法創作的電視劇雖接受門檻較高,但通常也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
相較于由藝術客體本身呈現出的表現強弱,審美價值的優劣判斷更多由審美主體決定。戲劇性優、情節性優和戲劇性劣、情節性劣,代表著電視劇審美的兩極,一邊是“神作”,另一邊是“爛劇”。誠然,達到“神作”標準的電視劇作品雖是少數,可這些作品卻具有永恒的魅力與價值;而“爛劇”則不同,屬于數量沒上限、質量沒下限,因審美價值寥寥故也毋庸贅言。多數電視劇作品均存在大大小小的瑕疵和不足,故戲劇性劣、情節性優和戲劇性優、情節性劣這兩種情況較為常見,而當二者中任何一方的審美塑造出現匱乏空洞,即使另一方塑造得再完美,也注定是缺失的,整體藝術價值將大打折扣,意味著整部劇的失敗。“神作”固然不能強求,電視劇生產創作卻必須以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優質呈現為目的,通過二者和諧穩定的良性關系構建,保證電視劇的內容質量和藝術基準。
三、“問題闡釋”:電視劇內容生產的美學癥候及意識重構
電視劇的審美價值,無非是娛一時之樂,還是娛一世之樂。電視劇中,戲劇性與情節性中的任意一方所能創造的都僅是一時之樂,如由情節性主導的電視劇在表現力、審美效果、市場盈利等方面均具優勢,可惜經典性不足,多數作品僅是看第一遍時還行,看第二遍便乏善可陳,缺乏像《雍正王朝》《亮劍》《闖關東》等作品百看不厭的內涵與深度;另一方面,娛樂表達縱然路徑多元卻也有基本的底線和規律依循,對戲劇性的戲仿解構雖是無傷大雅的,但若一味嘲弄、不思建設,所迎來的必將是虛無不毛。因而,多數電視劇作品的品質失守、口碑崩壞,主因還是出自戲劇性與情節性的構造不足,或是戲劇性缺失,抑或是情節性匱乏,以及二者關系的失衡。
(一)從偽劣失實到優質互娛
偽劣失實問題,即故事內容的粗制濫造和失實構造,國產劇領域中的曾持續多年的“雷劇”現象即是此問題的典型反映。“雷劇”通過造型、臺詞、動作等方面的夸張失實效果,試圖以逆向審丑方式點燃收視爆點,可實際帶來的卻是低質粗淺的視聽效果和流俗媚俗的感官體驗。目前而言,因創作意識失格和市場規則制約,粗制濫造的電視劇難以禁絕,導致電視劇行業整體口碑下滑,優質作品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偽劣失實般的創作雖然“短平快”,卻無疑是在飲鴆止渴。內在來看,電視劇的偽劣失實問題主要體現在戲劇性與情節性層面。戲劇性上,此類問題劇是典型的外強中空、“雷聲大雨點小”,在畫面、臺詞、配樂等視聽元素上極盡夸張之能事,外在表現上看似沖突激烈,實際卻無一絲一毫效果,帶來更深的受眾審美心理落差,僅可視作“偽戲劇性”。情節性上,此類問題劇是“形式大于內容”,畫蛇添足地謀求情節的“特異性”,盡管情節看似緊湊,實則節奏拖沓、不成體系,這些冗雜繁復的情節不僅毫無情節性可言,而且會引來尷尬、氣憤、不明所以等反向觀感,僅可視作“偽情節性”。
優質互娛意識,是指通過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優質呈現創造深層次娛樂體驗。在戲劇性層面,要放棄粗劣拙技,拆解拼貼式低俗娛樂多是無意義的消解,能一時流行卻無法經典永存。當然,這并非指要放棄通俗化表達,一味追求高山流水,而是要用更精深的藝術技巧營構戲劇性場面,構建作品與受眾的接受互動,激發受眾審美心理活動。在情節性層面,易懂易感知是其優勢,可這不意味著內容創作的膚淺化,而是保持敘事活力的劇作方法和娛樂化表達的必要途徑。以奇幻劇為例,此類劇集多以異世大陸為背景,通常會面臨故事失實的風險,因而一些作品會有意識地通過情節體現世界觀設定,以細膩貼切的情節性支撐虛構域情境感知,激發物理質感,并以戲劇性事件強化精神情感勾連,以此實現整體的優質互娛。
(二)從斷裂失衡到動態互融
斷裂失衡問題,一方面是電視劇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呈現與現實社會脫節,另一方面是指戲劇性與情節性固有聯系的斷裂和比例權重的失衡。當故事內容缺乏合理邏輯支撐,戲劇性與情節性將無從談起,除荒謬外無其他,更勿論審美關照,國產劇領域中的“懸浮劇”即是此類問題的代表。“懸浮”,即飄在空中、不接地氣,在本應表現社會現實狀況和群眾日常生活的現實題材劇中尤為常見,如在某些國產行業劇或職場劇中,因創作者對于特定職業工作方式的專業性塑造不足,故事人物的工作狀態就會悖于實際,實難讓人共情,明顯違背電視劇藝術的現實性規律。此外,如果作品一味地迎合大眾的低級的無意識欲望及趣味,亦會走向“偽現實主義”[16]。
關系斷裂方面,戲劇性與情節性相互割裂、難以銜接,矛盾沖突或情節表現兩相互斥,作品如同“一潭死水”沒有活性,審美感知方面存在不容跨越的鴻溝;關系失衡方面,戲劇性與情節性之間不均衡、不協調,過重過輕的兩極化態勢顯著,缺乏串聯過渡,滋生莫名所以的觀感。此外,斷裂失衡狀態還可能瓦解戲劇性與情節性的點線結構關系,導致由點線及面的整體美感不復存在,阻礙受眾移情認同。
動態互融意識,是指通過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動態更新,回歸互融互補狀態。以國產情景喜劇為例,此類型劇在我國發展已近三十余年,雖留下一定數量的精品卻也逐漸淹沒于時間長河,究其原因還是在于一般國產情景喜劇總是固守情節性一端,疏于戲劇性表現,盡管每一集都有新故事,但流水賬似的日常生活故事實在難以討喜。斷裂狀態下,電視劇戲劇性與情節性的故事效果往往光怪陸離、不知所云,審美主客體之間的接受鴻溝會持續加深,因此須強化戲劇性與情節性的有機融合意識,首先彌補敘事層面斷裂,動態更新內容表現要素,進而縫合故事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裂隙,拓寬受眾的審美感知向度。失衡狀態下,戲劇性與情節性
的動態結構體所能創造的并非兩端互補共進的審美強化效果,而是單極壟斷效應,完全隔絕另一極審美作用發生的可能。為規避此類問題,需要針對性地完成戲劇性與情節性的互補互通,在電視劇生產的前期、中期、后期均有相關把控,最終實現由此及彼的互鑒關照和價值遞增。
(三)從同質失趣到多維互生
同質失趣問題,即由內容同質化導致故事喪失審美趣味和文化魅力,近年來國產的另類神劇便是此問題的代表。當一部劇第一次成功運用某一情節模式或戲劇手法時是創新、經典的,但當此模式出現后仍千百遍、不厭其煩地使用,就是套路化、流俗化的。電視劇市場中,一部熱播劇往往可以帶起一支題材流派,掀起同類作品制作潮流,因而容易滋生同質化問題。其實,若能把握藝術創作的“變與不變”規律,在共性上同質,于靈活處新變,是可以將同質化控制在合理范圍內的,可惜知易行難。電視劇的同質失趣,可見于內容的各方面,從人物形象到劇情發展,每一處情節及沖突的雷同都是難以遮掩的。敘事層面拼貼復制和表意元素重復出現,會消耗故事內在的原創價值,令其所關涉的戲劇性或情節性受到波及,降低作品內在趣味性,影響審美活動發生。簡而言之,內容同質的直接結果便是美感同質。
多維互生意識,是指通過戲劇性與情節性表現的多維向度,促進審美意義互生。電視劇同質失趣問題的主因是過度重復,其針對性應對策略即增強內容原創性。故事原創,講求的是舊瓶裝新酒,而非換湯不換藥。電視劇領域中,某些創作者為避免同質化會選擇走捷徑式的刻意求新,為此就產生了諸如“抗日神劇”中武俠高手、逆天暗器、耍帥裝酷、時空穿越等不合常理的奇觀元素及惡俗橋段,其初衷雖是為創造效果,但卻違背了戲劇性與情節性的產生規律,與其美學范疇不相兼容。電視劇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多維互生,須堅持創新原則,積極開拓美學邊界,從劇作技巧、人物表演、鏡頭畫面、配音配樂、敘事剪輯等多重維度強化敘事文本的審美意涵,緊緊圍繞核心人物展開創作,升華作品整體美感。
四、“現象讀解”:當前國產劇敘事的“情節化轉向”
2018年暑期檔,電視劇《延禧攻略》熱播一時。該劇講述了魏家次女魏瓔珞為替姐姐復仇選擇進宮,在后宮中歷經艱險,最終完成復仇并成為皇后的故事。不同于一般宮斗劇中后宮女子“白蓮花”式的惺惺作態,魏瓔珞更像是一朵“黑蓮花”,她敢于反擊、絕不吃虧,面對接連不斷的生存危機,均憑借自身的機智勇敢化險為夷。“攻略”,原為攻城略地的簡寫,后衍義為游戲過程中的問題解決方案,指玩家在關卡設定中需通過特定的行為操作或方法指南完成通關。《延禧攻略》即魏瓔珞的后宮生存攻略,該劇正是放棄了傳統宮斗劇在人物、矛盾、情境等方面的復雜鋪陳,轉而采用游戲攻略式的副本結構法則,選擇在新事件開端簡略交代背景,快速拋出人物行動目標,任務完成后隨即切換另一任務,循環往復。當人物戰勝和消除對立客體的一系列行動成為電視劇審美效果的主要來源時,情節化即可視作其關鍵的敘事特征,這一特征在近年來的國產劇創作中日漸流行,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可惜的是,當前國產劇敘事的“情節化轉向”,雖然情節性得到高揚,但卻更多是以戲劇性的失位為代價,即外化為“戲劇性耗散”與“情節性熵增”。
(一)“戲劇性耗散”的成因
當前國產劇的“戲劇性耗散”,并非指戲劇性的消失,而是指戲劇性審美價值的大幅缺失。當作品的戲劇性表現呈“外強中干”“劣多于優”時,縱使行業整體的內容供給能力再充足,也難以抵御深描不足帶來的根基失穩。其成因主要出自四個方面:一是演員表演,電視劇戲劇性產生的核心要素是人物,而人物塑造歸根結底還是要依靠演員表演,但近年來國產電視劇領域內“小鮮肉”“流量明星”等演技普遍低于及格線的演員當道橫行,“老戲骨”等經驗豐富、演技精良的演員群體則頻頻遇冷,當表演不足以支撐人物形象時,自然就會導致戲劇性弱化;二是劇情構造,此前國產劇領域的“雷劇”“懸浮劇”以及另類“神劇”現象即是明證,“狗血”“套路”“媚俗”等劇情設置問題,明顯影響著國產劇的戲劇性審美體驗;三是視聽呈現,電視劇的戲劇性需要由畫面、聲音、造型等視聽藝術手段的融合予以呈現,而在某些國產劇中,環繞、升格、降格等鏡頭的濫用比比皆是,花式配樂、人物BGM(背景音樂)等音樂效果密布雜亂,夸張、多余的視聽表現直接影響著作品的戲劇性呈現,流于俗套、為人詬病;四是市場環境,在當前國產劇生產和收視市場中,作品價值的衡量標準還是以作品的預期收視和可能回報為中心,若利潤獲取相比無幾,市場自然傾向選擇周期短、見效快的情節化、娛樂化路線。
(二)“情節性熵增”的成因
當前國產劇的“情節性熵增”,表征為敘事段落內情節數量占比的增加、情節性程度的不斷遞增以及情節性效果的大幅提升。其成因主要出自三個方面:一是長篇化,國產劇的長篇化趨勢屬主導因素,目前國產劇平均集數已近40集,一些大劇形成60~80集的內容體量已是常態,敘事情節的數量需求也促進著情節性的提升,如《軍師聯盟》《慶余年》等劇集即是如此,但由此趨勢引發的內容“注水”問題亟需重視;二是類型化,國產劇的類型化路線屬輔助因素,特定情節元素集群是類型風格的必要條件,類型化程度與情節完善度成正比,如武俠劇需要有比武打斗、仙俠劇需要有修功練法等情節,而情節化敘事的高強度表現和高密度銜接,也有利于受眾情節性體驗的增強;三是網感化,國產劇的網感化走向屬刺激因素,由網感化帶動的內容情節性暗含著主體欲望幻想的意向性滿足,以《回到明朝當王爺之楊凌傳》為例,該劇的故事發展與原著小說的情節主線近似,主人公楊凌從普通秀才到異姓王爺的成長過程無比順遂,上至朝堂、下至戰場均無往不利,打怪升級般的情節模式雖提供出密集“爽感”,但不合常理、不合邏輯的因素也由之放大,因此該劇情節性雖強但審美價值卻有所欠缺。
(三)戲劇性與情節性的關系重構
電視劇的戲劇性與情節性具有動態平衡的耦合關系,當其中一方有所疏漏乏匱時,即便另一方被呈現得非常完美,也注定無法掩蓋作品整體審美價值的缺憾。短期內,由一方弱化留出的審美空洞會由另一方填充,即“戲劇性耗散”在一定程度上會助推“情節性熵增”。如演員表演上,以情節性為主導的國產劇對于演員演技的依賴度較低,人物只需要做出符合情節發展邏輯的行為動作,即可創造情節性效果;劇情構造上,情節性相對容易出新,不會重復“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雷雨”等千劇一面的戲劇性套路,可以用“新穎、奇怪、特別”的“新奇特”手法博取關注;視聽呈現上,對于情節性手法要求相對簡易,無需精致的畫面和配樂,成片難度較低;市場環境上,《白夜追兇》《長安十二時辰》《隱秘的角落》等以情節性見長的國產劇集已受到市場認可和大眾歡迎。客觀而言,“情節性熵增”并非國產劇娛樂化發展的惡果,而是其在一段時間內的主導審美風格,是劇作觀念、受眾審美、市場選擇等因素共同作用的階段體現。然而,從長遠角度看,國產劇的“情節性熵增”卻是弊大于利的,如果內容生產一味地向單方傾斜,那么整體的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必將無法實現有機統一。因此,國產劇優質生產的進一步實現,必須重視創作層面戲劇性與情節性的關系重構。
五、結 語
戲劇性與情節性的品質呈現和動態平衡,是電視劇藝術敘事精進的必經之途。一方面,通過經典敘事手段與現代視聽方法的結合,以人物命運或際遇為主線的深描勾畫,于各類沖突場面中持續激發戲劇性;另一方面,通過對人物傳記式、視點化的表現,展示人物的個體行動、組合行動和交織行動,構織細密的情節網絡,用豐富的情節演繹強化情節性。而對電視劇戲劇性與情節性的作用及關系的歸納、思辨、闡釋,既可為電視劇藝術研究增添新的觀察視角,也可為電視劇創作實踐提供方向參照。未來國產劇的發展,可從戲劇性與情節性的角度出發,“采新規、用新策、走新路”。“采新規”,即依托政府及有關部門關于行業發展的頂層設計和制度規劃,如2020年2月6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劇網絡劇創作生產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下發,通知中強調要加強源頭引導、強化制作備案管理、反對內容“注水”、規范制作成本配置等,意在轉變當前的劇集生產觀念、壓縮內容“水分”、規范演藝市場,對于重塑國產劇創作生態意義重大。“用新策”,即以“拋棄偽劣失實,走向優質互娛;避免斷裂失衡,強調動態互融;警惕同質失趣,倡導多維互生”為中心策略展開。“走新路”,即在回歸戲劇性與情節性并重的基礎上,向戲劇和電影學習探索性的現代敘事手法和哲理性的文化辯證邏輯,吸取過往及當前熱播劇集的創作經驗,創作出具有新興意蘊的故事內容。
參考文獻:
[1] 施旭升.反思“戲劇性”:一段問題史[J].文化藝術研究,2009(5):47.
[2] 濮波.對戲劇性的再認識[J].文化藝術研究,2009(5):183.
[3] 薩塞.戲劇美學初探[M].聿枚,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257.
[4] 威廉·阿契爾.劇作法[M].吳鈞燮,聶文杞,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44.
[5] 古斯塔夫·弗萊塔克.論戲劇情節[M].張玉書,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10.
[6] 喬治·貝克.戲劇技巧[M].余上沅,譯.上海:上海戲劇學院戲劇研究室編印,1961:5.
[7] 黑格爾.美學:第3卷 下冊[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42.
[8] 冉欲達.論情節[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142.
[9] 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0]黑格爾.美學:第1卷[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28.
[11]朱光潛. 審美范疇中的悲劇性和喜劇性[M]//朱光潛文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325.
[12]譚霈生.論戲劇性[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267.
[13]涂彥.電視劇的戲劇性研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108.
[14]涂彥.電視劇的“戲劇性”辨析[J].現代傳播,2009(4):86.
[15]李勝利.電視劇敘事情節[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80-81.
[16]孫海龍.符碼化與景觀生產——東北鄉村喜劇的偽現實主義特點研究[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131.
Dramatic and Melodramatic: The Dual Dialecticalof the Aesthetic? Acceptance Dual of TV Series
LI Xuan
(School of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indispensable and complementary dual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story narration are dramatic and melodramatic quality, which constitute the core aesthetic category of narrative art. Compared with drama and film, dramatic and melodramatic TV series are richer and easier to feel,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s closer and more complex. The strength and value of drama and plot tend to determine the artistic level of TV series. In the process of aesthetic acceptance of TV series, the dramatic and melodramatic problems such as inferior lack of truth, imbalances, homogeneity and disinterest, will affect the narrative expression of the works, and thus cause the audiences aesthetic perception dislocation. Therefore, it must be reversed and remold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ciousness of high quality mutual entertainment, dynamic mutual integr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mutual generation to return to dynamic balan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reative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TV series have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melodrama turning” in the narrative level, with “dramatic dissipation” and “melodramatic increase” as their explicit characteristics. In view of this, the further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production of Chinese TV series requires not on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ma and plot, but also the adoption of new rules, new policies and new ways.
Keywords:
TV series; narrative art; aesthetic acceptance; dramatic; melodramatic
(編輯:李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