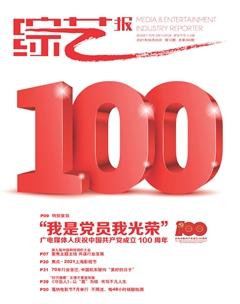影視教育與產業:教學相長還是漸行漸遠?

未來三五年,中國可能會有十余所“電影學院”拔地而起,同時卻又面臨著行業專才缺乏的局面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影視產業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流媒體平臺在內容發行上的重要性凸顯,平臺未來對于內容的數量需求勢必加大。與此同時,最近全國各地紛紛建立電影學院,仿佛這些應運而生的“電影學院”正順應了內容制作的數量需求似的。
事實上,中國的電影教育和產業之間一直存在著“疏離感”。說起電影教育,很多人首先會想到北京電影學院。這所參照蘇聯體系建立起來的專門院校,專業全而細。圍繞電影拍攝所需要的所有崗位,該校幾乎都開設了對應的系或者專業。譬如在攝影大類下又細分為燈光、圖片攝影專業;電影美術大類下也包括電影化妝等專業。
對比英美國家的電影教育體系架構,不難發現這些國家的電影教育基本分兩大類,即電影研究和電影制作。“電影研究”側重理論、史論和批評,對拍攝制作有關的內容涉及較少。“電影制作”則是全流程學習,它不像北京電影學院那樣再細分攝影、錄音、導演等系,更不會有剪輯、電影工程等細之又細的專業設置,但學生往往會在實踐中逐步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特長,最終選擇專攻某個專業。
英美綜合性大學幾乎都有電影研究專業,卻少有電影制作專業。恐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制作類課程需要器材、設備、機房、攝影棚,更需要有拍攝經驗的老師授課、指導實踐。英美比較著名的教授電影制作的大學,也都類似于北京電影學院,為純粹的獨立電影院校。
由于電影拍攝和制作的特點,課程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上手實踐和掌握,往往只能小班教學,費時費力。因此數百學生在大階梯教室由一名老師授課的方式,在電影制作類的學校里幾乎不存在。
20世紀90年代,電影學院人數最多的班約17人,部分專業全班只有8人的情況并不罕見。這樣的比例,堪稱精英教育中的精英,但幾乎無法支撐教育產業化。
從影視產業角度看,影視及其他視頻類內容制作人才需求最大的往往是攝影、剪輯、燈光、調色、視效后期、錄音、美術、服裝、化妝等工種。因為無論什么題材、什么制作級別的片子,這些崗位都是必需的。換言之,以年產量700部電影計,不算電視劇、網絡劇、網絡電影及中短視頻,電影學院的“產量”也遠未能滿足。何況很多“子專業”,如美術系的化妝專業、導演系的剪輯專業等,并非年年都招生。
那么,眼下各地紛紛建立電影學院是否就能解決問題了呢?當然不是。因為上述專業無一例外,都是需要“動手”才能學會的;而有經驗又善傳授的教師,并不會因為突然冒出來幾十家電影學院就能立刻湊齊。
目前,全國電影學院的辦學主體背景差距很大,對于“電影學院”的辦學理念也有所不同。大多數業外人士熱衷于表演和導演兩個專業。但即使在招生人數很少的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真正“出名”或一直有片子拍的畢業生數量可能不足一個班的二分之一。有趣的是,很多公認的好演員(如周迅、張曼玉等)卻從未念過表演系,這種“天才型”演員在全世界還有不少;再看看世界知名導演的教育背景,諾蘭(英國文學)、詹姆斯·卡梅隆(物理)、奉俊昊(社會學)、彼得·杰克遜(高中畢業)……
未來三五年,中國可能會有十余所“電影學院”拔地而起,同時卻又面臨著行業專才缺乏的局面。也許是時候打破現有的“北電模式”了:將電影教育分為學歷教育(本科、碩士、博士)和證書課程,并借鑒國外電影教育的學科劃分方式,劃分電影制作、表演、視效/游戲制作三個技能和訓練體系反差較大的方向。其中,電影制作依然是小班教學;表演則完全可能像英國的戲劇教育那樣“從娃娃抓起”,使其既成為素質美育教育的一部分,也可由此發掘有潛質的人才;視效后期在技術上和游戲制作幾乎可以共通,雙方可以相互依托,形成更大的教育平臺。比如,國外知名的溫哥華電影學院,即以其動手能力強的一年制課程享譽美加影視制作領域。而系統的理論研讀探討、電影批評等專業,則是學歷教育的主打方向。
希望這一輪遍地開花的電影學院,能避免資源浪費、重復設置、定位不清的誤區,能真正教學相長,為產業發展培育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和實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