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擴(kuò)招能夠改善工資扭曲嗎?
蔡思遠(yuǎn) 陸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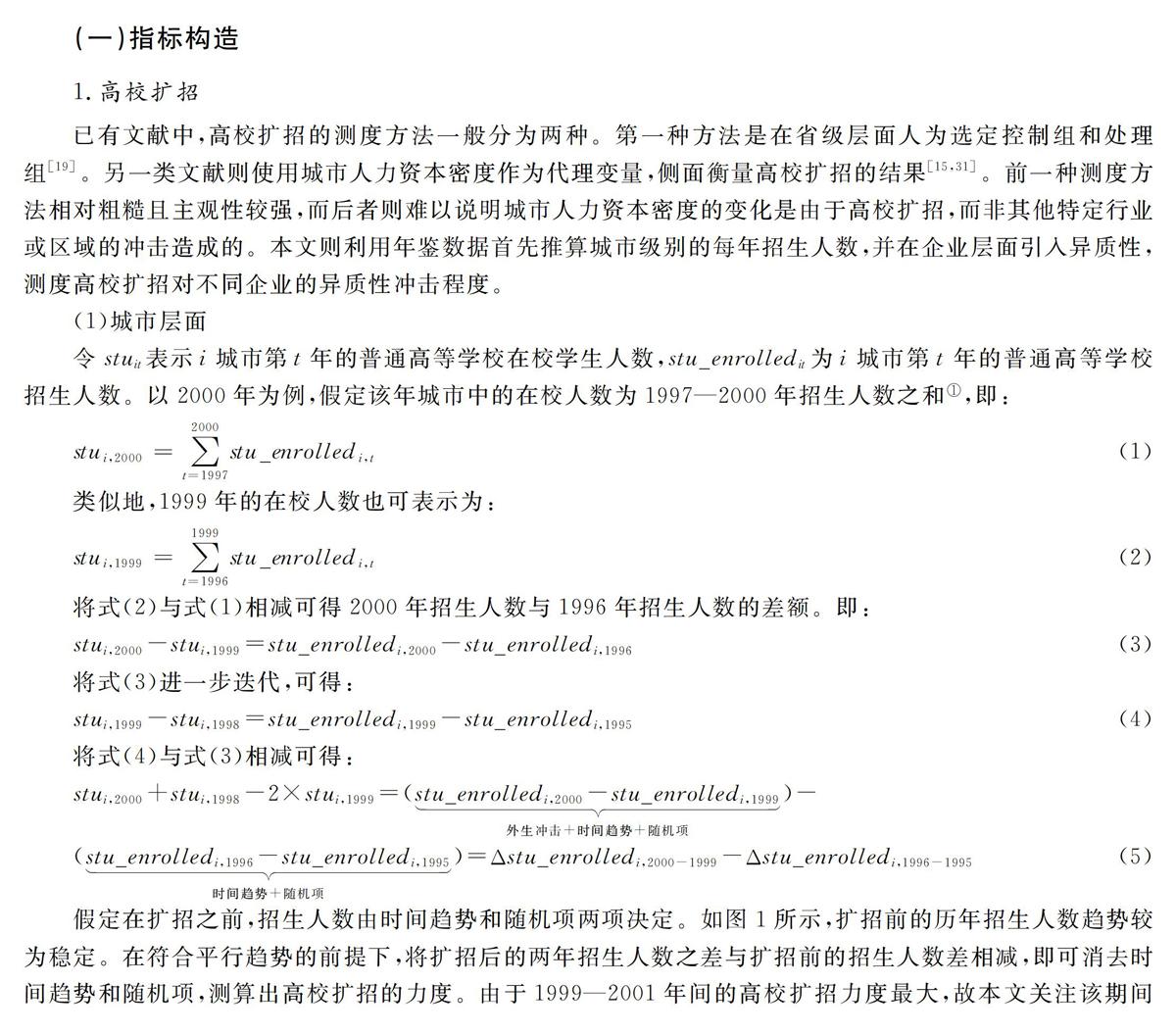


摘要:勞動(dòng)力供給對(duì)工資扭曲影響的相關(guān)研究往往受限于內(nèi)生性問題,難以得到可靠的結(jié)論。本文將高校擴(kuò)招視為勞動(dòng)力供給的外生沖擊,創(chuàng)新性地構(gòu)造高校擴(kuò)招的測(cè)度指標(biāo),采用雙重差分法評(píng)估了這一政策對(duì)工資扭曲的因果效應(yīng)。結(jié)果顯示:高校擴(kuò)招顯著降低了工資扭曲程度。機(jī)制檢驗(yàn)表明:“規(guī)模效應(yīng)”和“空間效應(yīng)”是兩個(gè)重要機(jī)制;“規(guī)模效應(yīng)”表現(xiàn)為高校擴(kuò)招吸收潛在過剩勞動(dòng)力,降低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程度所致的工資扭曲效應(yīng);“空間效應(yīng)”表現(xiàn)為人口流動(dòng)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會(huì)隨著城市規(guī)模提升由抑制轉(zhuǎn)為促進(jìn)。異質(zhì)性檢驗(yàn)表明:相比于其他類型的企業(yè),高校擴(kuò)招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的工資扭曲抑制作用更為顯著;而在城市層面,中間規(guī)模城市的工資扭曲下降最多。
關(guān)鍵詞:高校擴(kuò)招;工資扭曲;人力資本;人口流動(dòng)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8482021(04)013112
一、引言與文獻(xiàn)綜述
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指出,要素報(bào)酬應(yīng)當(dāng)?shù)扔谄溥呺H產(chǎn)出。但在中國(guó),勞動(dòng)力工資水平往往低于邊際產(chǎn)出,即存在“工資扭曲”的現(xiàn)象[1-2]。工資扭曲可能使得勞動(dòng)力要素被過度使用,阻礙技術(shù)升級(jí)。過低的工資也限制了勞動(dòng)收入占比的提升,擴(kuò)大國(guó)民收入差距,破壞社會(huì)的穩(wěn)定與和諧[3]。盡管工資扭曲與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供需狀況密切相關(guān),但由于供給和需求相互影響,供需的單方面變化對(duì)工資扭曲的因果效應(yīng)難以進(jìn)行識(shí)別。一個(gè)重要的問題是,勞動(dòng)力供給在規(guī)模和空間上的變化是否會(huì)對(duì)工資扭曲造成顯著影響?
幸運(yùn)的是,中國(guó)20世紀(jì)末的高等教育擴(kuò)張為回答上述問題提供了機(jī)會(huì)。具體而言,本文將1999年發(fā)生的高校擴(kuò)招視為勞動(dòng)力供給的外生沖擊,探究勞動(dòng)力供給的變化如何影響工資扭曲。本文將勞動(dòng)力供給變化的影響分解為“規(guī)模效應(yīng)”和“空間效應(yīng)”。其中,“規(guī)模效應(yīng)”表現(xiàn)為高校擴(kuò)招吸收潛在剩余勞動(dòng)力對(duì)工資扭曲的抑制效果,“空間效應(yīng)”表現(xiàn)為人口流動(dòng)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會(huì)隨著城市規(guī)模提升由抑制轉(zhuǎn)為促進(jìn)。本文通過系統(tǒng)揭示兩者的傳導(dǎo)機(jī)制,為相關(guān)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jù)。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現(xiàn)反復(fù)、內(nèi)需不足的背景下,碩士研究生和專升本的招生將再次擴(kuò)大,本文的研究結(jié)論更具現(xiàn)實(shí)意義。
本文與兩類文獻(xiàn)相關(guān)。第一類文獻(xiàn)關(guān)注要素價(jià)格扭曲的成因及影響。宏觀上中國(guó)的資本和勞動(dòng)力價(jià)格普遍存在負(fù)向扭曲。一般認(rèn)為要素價(jià)格扭曲的主要原因是偏向型的發(fā)展戰(zhàn)略。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要求壓低農(nóng)產(chǎn)品與資本投入品的價(jià)格、限制人口流動(dòng)、實(shí)施匯率限制并抑制利率[4]。故要素市場(chǎng)上存在著行政壟斷、地方保護(hù)等現(xiàn)象,進(jìn)而使得要素價(jià)格被扭曲[5]。而要素價(jià)格扭曲將導(dǎo)致企業(yè)生產(chǎn)效率降低[6]、失業(yè)率上升[7]和創(chuàng)新績(jī)效下降[8]。學(xué)界關(guān)于勞動(dòng)力價(jià)格扭曲影響的研究目前較少。已有研究表明工資扭曲將對(duì)企業(yè)創(chuàng)新產(chǎn)生抑制作用[9-10],但能夠促進(jìn)企業(yè)出口規(guī)模的擴(kuò)大[11]。
另一類文獻(xiàn)則與高等教育擴(kuò)張政策影響的評(píng)估相關(guān)。目前學(xué)界對(duì)高校擴(kuò)招政策的評(píng)價(jià)分歧較大,且以負(fù)面評(píng)價(jià)居多。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高等教育擴(kuò)張利于發(fā)揮規(guī)模效應(yīng),提高教育資源利用率[12],促進(jìn)人才培養(yǎng)多元化[13]。高校擴(kuò)招還能夠進(jìn)一步提升人力資本積累[14],促進(jìn)城市制造業(yè)出口升級(jí)[15]。而反對(duì)者則認(rèn)為過度招生不但降低了教育質(zhì)量,還使得勞動(dòng)力受到過度教育[16],與勞動(dòng)力需求失配,降低高等教育的溢價(jià)水平[17]。由于區(qū)域和階層之間存在異質(zhì)性,因此高校擴(kuò)招的受益群體不同還會(huì)加劇社會(huì)不公平[18]。高校擴(kuò)招還會(huì)對(duì)勞動(dòng)力的空間分布產(chǎn)生影響,例如促進(jìn)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實(shí)現(xiàn)更快速的城市化,進(jìn)而推動(dòng)房?jī)r(jià)上升[19]。
本文的邊際貢獻(xiàn)如下:首先,結(jié)合年鑒數(shù)據(jù)與企業(yè)微觀數(shù)據(jù),測(cè)度企業(yè)層面受到的高校擴(kuò)招影響。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對(duì)高校擴(kuò)招的測(cè)度更為精細(xì)。其次,以往研究往往沒有很好地解決勞動(dòng)力供給的內(nèi)生性問題。而本文利用高校擴(kuò)招這一準(zhǔn)自然實(shí)驗(yàn),評(píng)估勞動(dòng)力供給的外生沖擊對(duì)工資扭曲的因果效應(yīng),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內(nèi)生性問題,為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經(jīng)驗(yàn)證據(jù)。最后,在機(jī)制層面,將高校擴(kuò)招的影響分解為規(guī)模效應(yīng)和空間效應(yīng),并分別考察兩類效應(yīng)對(duì)工資扭曲的作用機(jī)制是否成立。研究通過梳理兩類機(jī)制的作用路徑,揭示高校擴(kuò)招改善工資扭曲的微觀作用機(jī)制。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從“規(guī)模效應(yīng)”和“空間效應(yīng)”維度分析高校擴(kuò)招對(duì)工資扭曲影響的理論機(jī)制;第三部分詳述指標(biāo)構(gòu)造及實(shí)證策略;第四部分匯報(bào)實(shí)證結(jié)果,并進(jìn)行一系列穩(wěn)健性檢驗(yàn);第五部分檢驗(yàn)本文所提出的兩個(gè)機(jī)制;最后是研究結(jié)論與未來展望。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工資扭曲的原因可分為內(nèi)生性扭曲和外生性扭曲兩類[20]。內(nèi)生性扭曲指由于非完美信息、外部性等市場(chǎng)失靈因素造成的要素價(jià)格扭曲[21]。過剩的勞動(dòng)力供給將使得工資向下扭曲。勞動(dòng)力和資本的區(qū)域間流動(dòng)則能夠緩解錯(cuò)配,從而降低工資扭曲[22-23]。而外生性扭曲指外部環(huán)境變化或特定政策和制度所導(dǎo)致的要素價(jià)格扭曲,例如最低工資法、勞動(dòng)合同法和環(huán)境規(guī)制,會(huì)降低勞動(dòng)力需求,促進(jìn)工資扭曲[24-25]。已有研究通常集中于探討單個(gè)因素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但卻無法系統(tǒng)地解釋這些因素為何導(dǎo)致價(jià)格機(jī)制失靈,出現(xiàn)工資扭曲,對(duì)于中國(guó)普遍的工資扭曲現(xiàn)象的成因也語焉不詳。
本文認(rèn)為,已有解釋往往忽略了中國(guó)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市場(chǎng)分割。當(dāng)工資小于邊際勞動(dòng)力產(chǎn)出時(shí),理應(yīng)出現(xiàn)兩種情形:要么勞動(dòng)力流向工資更高的地區(qū)。這樣工資扭曲高的地區(qū)勞動(dòng)力供給減少,工資上升。要么企業(yè)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崗位,即企業(yè)數(shù)量更多或者企業(yè)規(guī)模更大。但如果存在要素市場(chǎng)分割,這兩個(gè)價(jià)格調(diào)節(jié)機(jī)制都將失效。首先,中國(guó)存在普遍的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分割現(xiàn)象。過剩的勞動(dòng)力無法充分流向勞動(dòng)力缺乏的地區(qū),從而加劇工資扭曲現(xiàn)象[26-27]。其次,中國(guó)長(zhǎng)期以來人為壓低資本的價(jià)格,以優(yōu)先支持工業(yè)發(fā)展。壓低的資本價(jià)格使得企業(yè)更偏向于使用資本而非勞動(dòng)力,導(dǎo)致就業(yè)崗位創(chuàng)造不足[28]。同時(shí),資本更多流向國(guó)有企業(yè)和大型企業(yè),而作為吸收過剩勞動(dòng)力主體的民營(yíng)企業(yè)與中小企業(yè)則面臨融資約束。因此中小企業(yè)數(shù)量不足且規(guī)模較小,第二個(gè)機(jī)制也難以起效[29]。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guó)工資扭曲的成因在于,在要素市場(chǎng)分割的背景下,勞動(dòng)力無法根據(jù)價(jià)格機(jī)制進(jìn)行供需調(diào)整,實(shí)現(xiàn)最優(yōu)的一般均衡。盡管價(jià)格對(duì)供需的影響因?yàn)槭袌?chǎng)分割并不充分,但供需對(duì)價(jià)格的影響機(jī)制依然生效。既然要素價(jià)格受到勞動(dòng)力供給的影響仍然成立,那么就為外生的勞動(dòng)力供給沖擊影響工資扭曲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作為準(zhǔn)自然實(shí)驗(yàn),高校擴(kuò)招可以視為對(duì)中國(guó)勞動(dòng)力供給的一次外生沖擊。理論上,本文認(rèn)為高校擴(kuò)招對(duì)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供給可能存在“規(guī)模效應(yīng)”和“空間效應(yīng)”的雙重影響。
高校擴(kuò)招的“規(guī)模效應(yīng)”體現(xiàn)在,在“下崗潮”的背景下,下崗工人需要與適齡的應(yīng)屆畢業(yè)生競(jìng)爭(zhēng)有限的就業(yè)崗位。而高校擴(kuò)招能夠?qū)е轮袑W(xué)畢業(yè)生繼續(xù)接受教育,吸收過剩的潛在勞動(dòng)力,降低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競(jìng)爭(zhēng)程度,從而緩解工資扭曲。這一機(jī)制主要發(fā)生在低技能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如上所述,受限的崗位擴(kuò)張和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不暢共同惡化了工資扭曲。而高校擴(kuò)招能夠吸收潛在的剩余勞動(dòng)力,降低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程度,從而改善工資扭曲。因此,本文提出假說1與假說2。
假說1:高校擴(kuò)招在整體上降低了工資扭曲程度。
假說2:高校擴(kuò)招具有“規(guī)模效應(yīng)”,表現(xiàn)為高校擴(kuò)招吸收潛在剩余勞動(dòng)力,降低就業(yè)競(jìng)爭(zhēng),改善工資扭曲。
高校擴(kuò)招的“空間效應(yīng)”體現(xiàn)在,高校擴(kuò)招使得大量學(xué)生去往異地求學(xué),促進(jìn)區(qū)域間的人口流動(dòng)。高校擴(kuò)招能夠影響人口總體遷移的模式,高校生的臨時(shí)遷移數(shù)量大增。至2009年,每100個(gè)城鎮(zhèn)常住人口中就有1個(gè)高考招生實(shí)現(xiàn)的遷入人口[30]。而在畢業(yè)后,相當(dāng)一部分的學(xué)生將選擇留在當(dāng)?shù)鼐蜆I(yè)。除了學(xué)生群體自身的流動(dòng),人口遷移還存在乘數(shù)效應(yīng)。遷移學(xué)生對(duì)服務(wù)業(yè)等相關(guān)行業(yè)的需求,也會(huì)引致更多人口流入。高校數(shù)量較多的城市規(guī)模也通常更大。總之,高校擴(kuò)招促進(jìn)了人口進(jìn)一步向大城市流動(dòng)。
理論上而言,勞動(dòng)力集聚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存在兩個(gè)渠道:集聚效應(yīng)和競(jìng)爭(zhēng)效應(yīng)。因此,隨著兩類機(jī)制的相對(duì)作用力大小變化,勞動(dòng)力集聚對(duì)工資的影響呈現(xiàn)出倒U型結(jié)構(gòu)。在集聚初期,集聚效應(yīng)占據(jù)主導(dǎo),此時(shí)勞動(dòng)力集聚能夠通過相互學(xué)習(xí)和知識(shí)溢出、勞動(dòng)力與崗位之間更好的匹配等機(jī)制提升工資溢價(jià),減緩工資扭曲程度。隨著集聚程度增加,競(jìng)爭(zhēng)效應(yīng)占據(jù)主導(dǎo),此時(shí)勞動(dòng)力集聚對(duì)工資扭曲呈現(xiàn)出促進(jìn)作用。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勞動(dòng)力供過于求。大城市中的勞動(dòng)力將面臨更為激烈的競(jìng)爭(zhēng),阻礙工資扭曲的降低。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3:高校擴(kuò)招具有“空間效應(yīng)”,表現(xiàn)為促進(jìn)人口向大城市流動(dòng),從而影響工資扭曲。由于集聚效應(yīng)和競(jìng)爭(zhēng)效應(yīng)的相對(duì)力量變化,勞動(dòng)力集聚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呈現(xiàn)出先抑制后促進(jìn)的作用。
三、指標(biāo)構(gòu)造與實(shí)證設(shè)定
(一)指標(biāo)構(gòu)造
1.高校擴(kuò)招
已有文獻(xiàn)中,高校擴(kuò)招的測(cè)度方法一般分為兩種。第一種方法是在省級(jí)層面人為選定控制組和處理組[19]。另一類文獻(xiàn)則使用城市人力資本密度作為代理變量,側(cè)面衡量高校擴(kuò)招的結(jié)果[15,31]。前一種測(cè)度方法相對(duì)粗糙且主觀性較強(qiáng),而后者則難以說明城市人力資本密度的變化是由于高校擴(kuò)招,而非其他特定行業(yè)或區(qū)域的沖擊造成的。本文則利用年鑒數(shù)據(jù)首先推算城市級(jí)別的每年招生人數(shù),并在企業(yè)層面引入異質(zhì)性,測(cè)度高校擴(kuò)招對(duì)不同企業(yè)的異質(zhì)性沖擊程度。
(1)城市層面
令stuit表示i城市第t年的普通高等學(xué)校在校學(xué)生人數(shù),stu_enrolledit為i城市第t年的普通高等學(xué)校招生人數(shù)。以2000年為例,假定該年城市中的在校人數(shù)為1997—2000年招生人數(shù)之和[專科的學(xué)制為3年。但由于城市層面普通本科與專科的比例難以獲得,故均使用4年進(jìn)行計(jì)算。],即:
stui,2000=∑2000t=1997stu_enrolledi,t(1)
類似地,1999年的在校人數(shù)也可表示為:
stui,1999=∑1999t=1996stu_enrolledi,t(2)
將式(2)與式(1)相減可得2000年招生人數(shù)與1996年招生人數(shù)的差額。即:
stui,2000-stui,1999=stu_enrolledi,2000-stu_enrolledi,1996(3)
將式(3)進(jìn)一步迭代,可得:
stui,1999-stui,1998=stu_enrolledi,1999-stu_enrolledi,1995(4)
將式(4)與式(3)相減可得:
stui,2000+stui,1998-2×stui,1999=
(stu_enrolledi,2000-stu_enrolledi,1999外生沖擊+時(shí)間趨勢(shì)+隨機(jī)項(xiàng))-
(stu_enrolledi,1996-stu_enrolledi,1995時(shí)間趨勢(shì)+隨機(jī)項(xiàng))=
Δstu_enrolledi,2000-1999-Δstu_enrolledi,1996-1995(5)
假定在擴(kuò)招之前,招生人數(shù)由時(shí)間趨勢(shì)和隨機(jī)項(xiàng)兩項(xiàng)決定。如圖1所示,擴(kuò)招前的歷年招生人數(shù)趨勢(shì)較為穩(wěn)定。在符合平行趨勢(shì)的前提下,將擴(kuò)招后的兩年招生人數(shù)之差與擴(kuò)招前的招生人數(shù)差相減,即可消去時(shí)間趨勢(shì)和隨機(jī)項(xiàng),測(cè)算出高校擴(kuò)招的力度。由于1999—2001年間的高校擴(kuò)招力度最大,故本文關(guān)注該期間的總沖擊大小。本文用2001年各城市的招生人數(shù)數(shù)量作為分母,測(cè)算招生人數(shù)提升比例(Expansion),用以衡量高校擴(kuò)招在城市層面的沖擊大小[2001年前,城市層面的高等學(xué)校招生人數(shù)并不完整,因此無法使用基期,即1998年的招生人數(shù)作為分母。]。表達(dá)式如下:
Expansioni=Δstu_enrolledi,2001-1998-Δstu_enrolledi,1997-1994stu_enrolledi,2001(6)
(2)企業(yè)層面
即使位于同一城市,若生產(chǎn)過程中勞動(dòng)力越重要,那么高校擴(kuò)招對(duì)該企業(yè)的影響就越嚴(yán)重。因此本文使用企業(yè)的勞動(dòng)產(chǎn)出占比來構(gòu)造企業(yè)異質(zhì)性。假定企業(yè)的生產(chǎn)函數(shù)如式(7)所示。其中,Y為工業(yè)增加值,A為全要素生產(chǎn)率,K和L分別為資本和勞動(dòng)力投入[在工業(yè)增加值數(shù)據(jù)缺失的年份,本文使用會(huì)計(jì)準(zhǔn)則估算工業(yè)增加值:工業(yè)增加值=工業(yè)總產(chǎn)值-工業(yè)中間投入+增值稅。]。
Y=AKαLβ(7)
兩邊取對(duì)數(shù)后,企業(yè)的勞動(dòng)產(chǎn)出占比可表示為:
L_pro=βlnLlnY(8)
對(duì)α和β進(jìn)行回歸估計(jì)后,即可求出每家企業(yè)的勞動(dòng)力占比[在估計(jì)參數(shù)時(shí),本文考慮了行業(yè)和年份的異質(zhì)性,但沒有考慮參數(shù)的城市異質(zhì)性。如果這么做,一些城市企業(yè)的樣本將會(huì)不足。]。最后,將城市層面的擴(kuò)招力度與企業(yè)層面的異質(zhì)性相乘,即可得到企業(yè)層面受到的異質(zhì)性沖擊大小(HEE)。
HEE=Expansion×L_pro(9)
2.工資扭曲
本文遵循以往文獻(xiàn)做法,將工資扭曲定義為工資與勞動(dòng)邊際產(chǎn)出的偏離程度,如式(10)所示。如果工資扭曲程度大于1,則表明工資存在向下扭曲的情形。
Distort=MPLwage(10)
為了保證實(shí)證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參照以往研究,本文使用3種不同的方法對(duì)MPL進(jìn)行測(cè)度:C-D函數(shù)法[10]、超越函數(shù)法[25]和LP法[32]。而工資的計(jì)算方法如下:首先計(jì)算出企業(yè)的總工資支出,包括應(yīng)付福利費(fèi)總額、勞動(dòng)失業(yè)保險(xiǎn)費(fèi)總額以及應(yīng)付工資薪酬總額三個(gè)部分;然后除以全部從業(yè)人員年平均數(shù),得到企業(yè)的平均工資。在全部從業(yè)人員年平均數(shù)缺失的年份中,本文使用年末從業(yè)人員數(shù)進(jìn)行代替。
(二)實(shí)證設(shè)定
本文使用Nunn等[33]提出的連續(xù)型雙重差分法進(jìn)行估計(jì)。與標(biāo)準(zhǔn)雙重差分模型相比,該模型中的處理變量是連續(xù)變量,優(yōu)勢(shì)在于可以更好地捕捉組別間處理強(qiáng)度差異所導(dǎo)致的結(jié)果差異。具體的模型設(shè)定如下:
Distortit=α+βHEEit×postt+Γ∑Xit-1+μ1City×year_FE+μ2Ind×year_FE+
μ3Type×year_FE+μ4ID_FE+εit(11)
其中,因變量Distortit為第t年企業(yè)i的工資扭曲程度。β是感興趣的關(guān)鍵系數(shù),Γ為控制變量的系數(shù)向量,μ1~μ4分別為高維固定效應(yīng)的相應(yīng)系數(shù)向量,ε為隨機(jī)誤差項(xiàng)。由于第一批擴(kuò)招的學(xué)生需要在4年后再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因此若年份早于2003年,post為0,否則為1。為了控制企業(yè)層面、行業(yè)層面和城市層面的影響,回歸方程中加入了個(gè)體固定效應(yīng)ID_FE、行業(yè)與年份固定效應(yīng)的交互項(xiàng)Ind×year_FE以及城市與年份固定效應(yīng)的交互項(xiàng)City×year_FE。回歸式中還加入了企業(yè)登記注冊(cè)類型的啞變量與年份固定效應(yīng)的交互項(xiàng)Type×year_FE,用以控制不同企業(yè)類型的時(shí)間趨勢(shì)。Xit-1為企業(yè)維度的一系列控制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jì)報(bào)告在表1中。
本文將所選取的控制變量均滯后一期加入回歸,以確保其外生性與前定性。具體選取依據(jù)如下:
(1)勞動(dòng)產(chǎn)出占比(L_pro):勞動(dòng)產(chǎn)出占比越高,該企業(yè)越依賴于勞動(dòng)力,受到的外部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沖擊也將越嚴(yán)重,從而影響工資扭曲程度。
(2)出口占比(export):部分研究指出,企業(yè)的進(jìn)出口行為將影響其與勞動(dòng)力的議價(jià)能力。Dobbelaere等[34]利用法國(guó)企業(yè)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出口企業(yè)的工資設(shè)定能力更差,即工資扭曲更低。
(3)企業(yè)規(guī)模(size):已有文獻(xiàn)探討了城市規(guī)模與行業(yè)規(guī)模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27,34]。類似地,企業(yè)規(guī)模越大,越有可能使用先進(jìn)生產(chǎn)技術(shù),提升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增加工資扭曲程度[27]。
(4)利潤(rùn)率(pf):工資扭曲程度還受到市場(chǎng)勢(shì)力的影響。如果企業(yè)所在的行業(yè)競(jìng)爭(zhēng)程度更高,則要素價(jià)格越趨近于完全競(jìng)爭(zhēng)市場(chǎng)下的定價(jià)。
(5)政府補(bǔ)貼(subsidy):獲得政府補(bǔ)貼意味著企業(yè)一方面弱化了生產(chǎn)過程中的成本約束,使得企業(yè)能夠支付更高的工資。但另一方面,政府補(bǔ)貼往往具有指定用途。魏下海等[35]認(rèn)為政府補(bǔ)貼還反映出企業(yè)可能具有更多的政治資源。獲得政治資源變相提升了企業(yè)的壟斷勢(shì)力,使得勞動(dòng)力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資。
一個(gè)可能的問題是高校擴(kuò)招與工資扭曲的逆向因果關(guān)系。首先,高校擴(kuò)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刺激經(jīng)濟(jì)、提升人力資本與緩解就業(yè)壓力[高校擴(kuò)招源于時(shí)任亞洲開發(fā)銀行首席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湯敏與妻子左小蕾提交的《關(guān)于啟動(dòng)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有效途徑——擴(kuò)大招生量一倍》建議書,將擴(kuò)張招生作為刺激經(jīng)濟(jì)、擴(kuò)大內(nèi)需的手段。從標(biāo)題即可看出,該提議的初衷是為了刺激經(jīng)濟(jì)。另外,高校擴(kuò)招利于提升人力資本。時(shí)任國(guó)務(wù)院副總理李嵐清指出,實(shí)施高校擴(kuò)招的原因主要是“持續(xù)快速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需要更多的高素質(zhì)人才”[36],目的是突破高等教育瓶頸,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提供良好的基礎(chǔ)。在緩解就業(yè)壓力方面,湯敏的建議書中也提到了這一理由。1998—2001年間,國(guó)有企業(yè)下崗職工總量達(dá)到2552.4萬人。而高校擴(kuò)招在4年中能夠給下崗工人騰出500~600萬個(gè)工作機(jī)會(huì),從而降低就業(yè)競(jìng)爭(zhēng)[37]。可見,高校擴(kuò)招的初衷并非是為了緩解工資扭曲現(xiàn)象。],因此對(duì)于工資扭曲而言,高校擴(kuò)招可以被視為外生的準(zhǔn)自然實(shí)驗(yàn)。其次,擴(kuò)招力度是通過教育部來進(jìn)行調(diào)節(jié)和控制的,很難認(rèn)為高校擴(kuò)招規(guī)模由當(dāng)?shù)氐墓べY扭曲程度決定。最后,本文使用1998年的城市平均工資扭曲程度與高校擴(kuò)招規(guī)模進(jìn)行回歸,結(jié)果顯示兩者的相關(guān)性并不顯著,因此潛在的逆向因果對(duì)本文的估計(jì)結(jié)果影響較小。基于以上理由,本文認(rèn)為沒有證據(jù)表明HEE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是通過高校擴(kuò)招以外的因素引起的[感謝審稿專家提出的相關(guān)意見。回歸結(jié)果限于篇幅限制不再匯報(bào),若有需要可來信索取。]。
(三)數(shù)據(jù)來源與其他說明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國(guó)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進(jìn)行研究。數(shù)據(jù)處理步驟如下:
(1)按照Brandt等[38-40]的做法,對(duì)數(shù)據(jù)庫中的樣本進(jìn)行預(yù)處理,并剔除了關(guān)鍵指標(biāo)缺失、職工人數(shù)小于8人、與基本會(huì)計(jì)準(zhǔn)則相違背的樣本。
(2)以1998年為基期,產(chǎn)值類數(shù)據(jù)使用工業(yè)企業(yè)產(chǎn)品出廠價(jià)格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工資數(shù)據(jù)使用消費(fèi)者價(jià)格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資產(chǎn)類數(shù)據(jù)使用固定資產(chǎn)價(jià)格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
(3)剔除了部分平均工資低于當(dāng)年的最低工資標(biāo)準(zhǔn)的企業(yè)。
(4)為了排除企業(yè)進(jìn)入或退出的樣本選擇問題,只保留了10年間至少存在8期觀測(cè)數(shù)據(jù)的企業(yè)樣本。
(5)為了排除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剔除了工資扭曲程度前后各5%的數(shù)據(jù)。
本文城市層面的數(shù)據(jù)均使用市轄區(qū)口徑,普通高等學(xué)校在校學(xué)生人數(shù)數(shù)據(jù)來自歷年《中國(guó)城市統(tǒng)計(jì)年鑒》,省屬高校比例為筆者手動(dòng)整理計(jì)算得到,剩余數(shù)據(jù)均來自中國(guó)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
四、實(shí)證結(jié)果
(一)基準(zhǔn)模型
本文首先考察高校擴(kuò)招對(duì)工資扭曲程度的整體影響。基準(zhǔn)模型的回歸結(jié)果如表2所示,單變量回歸中,高校擴(kuò)招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均顯著為負(fù)。在引入控制變量后,系數(shù)的顯著性依舊沒有降低。此外,控制變量的系數(shù)也符合總體預(yù)期。勞動(dòng)產(chǎn)出占比越高,工資扭曲程度越低。 同時(shí),利潤(rùn)率與企業(yè)規(guī)模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也與預(yù)期一致。政府補(bǔ)貼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表明企業(yè)獲得的政府補(bǔ)貼可能對(duì)工資扭曲呈現(xiàn)負(fù)向影響。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是,出口占比與工資扭曲關(guān)系并不顯著,其原因仍需要進(jìn)一步的研究探討。結(jié)果表明高校擴(kuò)招能夠顯著改善企業(yè)的工資扭曲程度。
(二)穩(wěn)健性檢驗(yàn)
1.平行趨勢(shì)檢驗(yàn)
使用雙重差分法的前提之一就是處理組與控制組具有共同的時(shí)間趨勢(shì)。本文以2002年作為基準(zhǔn)年份,使用回歸法檢驗(yàn)平行趨勢(shì)是否成立。回歸方程如下,其中yeart在第t年時(shí)取1,否則取0。回歸結(jié)果如表3所示。
Distortit=α+∑βtHEEit×yeart+Γ∑Xit-1+μ1City×year_FE+μ2Ind×year_FE+μ3Type×year_FE+μ4ID_FE+εit(12)
除了1999年的交互項(xiàng)系數(shù)顯著為正外,2003年之前的交互項(xiàng)系數(shù)均不顯著,表明平行趨勢(shì)的原假設(shè)沒有被拒絕。同時(shí)2003年之前的交互項(xiàng)系數(shù)為正,而之后開始顯著為負(fù),轉(zhuǎn)換趨勢(shì)較為明顯,表明高校擴(kuò)招這一外生沖擊確實(shí)對(duì)工資扭曲產(chǎn)生了顯著的影響。交互項(xiàng)系數(shù)在2003年并不顯著,表明高校擴(kuò)招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存在滯后效應(yīng)。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畢業(yè)生群體需要在工作一段時(shí)間后,才能將自身工資扭曲的下降傳遞給整個(gè)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另一方面,單獨(dú)一屆擴(kuò)招學(xué)生的數(shù)量可能不足以影響整個(gè)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而在第二年后,累積起來的高技能勞動(dòng)力供給擴(kuò)張開始產(chǎn)生顯著的影響。
2.其他穩(wěn)健性檢驗(yàn)
(1)大城市的極端值影響
在大城市中,勞動(dòng)力供給沖擊導(dǎo)致的工資變化可能更明顯,因此本文觀測(cè)到的工資扭曲下降可能是由于特定城市引起的。Che等[31]指出北京市與上海市相比于其他城市,集聚程度明顯更高。為了排除極端值對(duì)因果效應(yīng)估計(jì)的影響,本文將樣本中位于北京市與上海市的企業(yè)剔除。如表4中第(1)—(3)列所示,回歸系數(shù)依舊保持顯著,且大小基本保持一致。該結(jié)果表明大城市的極端值也并非工資扭曲下降的原因。
(2)測(cè)量誤差
在計(jì)算工資扭曲時(shí),工業(yè)增加值作為關(guān)鍵變量直接決定了工資扭曲測(cè)度的精確與否。由于2004年的中國(guó)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中缺少工業(yè)增加值數(shù)據(jù),本文使用會(huì)計(jì)準(zhǔn)則進(jìn)行推算補(bǔ)齊,因此2004年的數(shù)據(jù)可能存在一定的測(cè)量誤差,從而影響結(jié)論的可靠性。在表4第(4)—(6)列中,本文將2004年的數(shù)據(jù)剔除進(jìn)行回歸。結(jié)果顯示系數(shù)依然顯著為負(fù),表明可能的測(cè)量誤差并未改變基準(zhǔn)回歸的結(jié)果。
(3)加入世貿(mào)組織
在樣本期間內(nèi),除了高校擴(kuò)招外,中國(guó)還加入了世界貿(mào)易組織(WTO)。理論上,我國(guó)部分勞動(dòng)密集型行業(yè)的出口因加入世貿(mào)組織得到了提升。相關(guān)企業(yè)將對(duì)勞動(dòng)力有更大的需求,進(jìn)而降低工資扭曲水平。同時(shí),外資進(jìn)入也利于工資扭曲的改善[22]。因此這一事件的發(fā)生可能影響對(duì)高校擴(kuò)招的因果效應(yīng)估計(jì)。
為了排除出口企業(yè)對(duì)勞動(dòng)力需求增加的影響,本文只使用當(dāng)年出口占比為0的企業(yè)進(jìn)行回歸。結(jié)果顯示工資扭曲程度在1%的水平上顯著下降,且系數(shù)均小于基準(zhǔn)回歸中的結(jié)果[回歸結(jié)果限于篇幅限制未匯報(bào),若有需要可來信索取。]。這表明非出口企業(yè)的工資扭曲下降程度要大于出口企業(yè)。同時(shí)本文排除了“服裝及其他纖維制品制造業(yè)”以及“通信設(shè)備、計(jì)算機(jī)及其他電子設(shè)備制造業(yè)”這兩類中國(guó)出口占比最高的行業(yè)中的企業(yè)。結(jié)果顯示排除掉這兩類行業(yè)后,其余行業(yè)的工資扭曲仍然顯著下降。因此,中國(guó)加入世貿(mào)組織并非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整體工資扭曲下降的主要原因。總之,所有穩(wěn)健性檢驗(yàn)均表明,沒有證據(jù)顯示工資扭曲的下降是由于高校擴(kuò)招以外的事件所導(dǎo)致的,故假說1得到驗(yàn)證。
(三)異質(zhì)性檢驗(yàn)
1.企業(yè)類型異質(zhì)性
本文首先考察高校擴(kuò)招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是否存在企業(yè)異質(zhì)性。在中國(guó),勞動(dòng)力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有著顯著的偏好。尤其是在20世紀(jì)90年代,私營(yíng)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規(guī)模不大的背景下,國(guó)企崗位的競(jìng)爭(zhēng)最為激烈,導(dǎo)致工資扭曲程度較高。因此,高校擴(kuò)招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工資扭曲的影響應(yīng)當(dāng)較為顯著。同時(shí),高校擴(kuò)招還可能存在擴(kuò)散效應(yīng),即吸收部分原本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人口,降低私營(yíng)和外資企業(yè)崗位的競(jìng)爭(zhēng)。因此,私營(yíng)企業(yè)與外資企業(yè)的工資扭曲程度也可能有所下降。
為此,本文引入企業(yè)登記注冊(cè)的類型與處理變量的交互項(xiàng),考察其異質(zhì)性是否顯著。由于數(shù)據(jù)庫的登記注冊(cè)類型分類較細(xì),本文對(duì)企業(yè)進(jìn)行了重新分類[“國(guó)有與集體聯(lián)營(yíng)企業(yè)”“國(guó)有企業(yè)”“國(guó)有獨(dú)資公司”“國(guó)有聯(lián)營(yíng)企業(yè)”歸類為國(guó)有企業(yè),“私營(yíng)合伙企業(yè)”“私營(yíng)有限責(zé)任公司”“私營(yíng)獨(dú)資企業(yè)”“私營(yíng)股份有限公司”歸類為私營(yíng)企業(yè),“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資(獨(dú)資)企業(yè)”“港澳臺(tái)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港澳臺(tái)獨(dú)資企業(yè)”歸類為外資企業(yè),剩余類型則歸類為其他企業(yè)。]。如表5第(1)—(3)列所示,僅有國(guó)有企業(yè)虛擬變量與處理變量的交互項(xiàng)顯著為負(fù),其余交互項(xiàng)均不顯著。回歸結(jié)果表明,國(guó)有企業(yè)的工資扭曲下降程度相比于其他企業(yè)類型更高,這一結(jié)果與預(yù)期相符。而私營(yíng)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則與其他企業(yè)類型的工資扭曲下降程度不存在顯著差異。
2.城市規(guī)模異質(zhì)性
城市人口規(guī)模直接決定了勞動(dòng)力競(jìng)爭(zhēng)的激烈程度。高校擴(kuò)招影響在不同城市規(guī)模下可能存在異質(zhì)性的邏輯在于:高校擴(kuò)招能夠促進(jìn)人口向大城市集聚,降低工資扭曲程度。但隨著城市規(guī)模的擴(kuò)大,勞動(dòng)力的競(jìng)爭(zhēng)效應(yīng)逐漸提升;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效應(yīng)大于集聚效應(yīng)時(shí),高校擴(kuò)招帶來的工資扭曲下降程度就將減弱。因此,本文考察在不同規(guī)模的城市中,高校擴(kuò)招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程度是否存在異質(zhì)性。本文按照2014年的《關(guān)于調(diào)整城市規(guī)模劃分標(biāo)準(zhǔn)的通知》,將城市規(guī)模分為三類:常住人口小于500萬,即大城市及以下;常住人口大于500萬小于1000萬,即特大城市;常住人口大于1000萬,即超大城市。
類似地,本文也引入城市規(guī)模的啞變量與處理變量進(jìn)行交互,加入回歸并檢驗(yàn)其顯著性。交互項(xiàng)的回歸結(jié)果如表5第(4)—(6)列所示,相應(yīng)組別的交互項(xiàng)系數(shù)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比于大中城市,特大城市與超大城市的工資扭曲下降程度均顯著更高。特大城市的交互項(xiàng)系數(shù)更高表明,該組別的工資扭曲下降程度最為明顯。倒U型的系數(shù)分布結(jié)果從側(cè)面印證了假說3。
五、機(jī)制檢驗(yàn)
(一)低技能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與工資扭曲
首先,本文考察高校擴(kuò)招吸收潛在剩余勞動(dòng)力,降低低技能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程度的“規(guī)模效應(yīng)”路徑。本文使用差分法(Long Difference Method)進(jìn)行檢驗(yàn)。其邏輯在于,如果觀察到低技能勞動(dòng)力工資扭曲的下降幅度與相應(yīng)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減緩的程度呈現(xiàn)出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同時(shí)相應(yīng)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程度的變化又是由于高校擴(kuò)招所導(dǎo)致的,那么這一機(jī)制就能夠得到驗(yàn)證。本文將低技能勞動(dòng)力企業(yè)工資扭曲的變化幅度視為低技能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程度的體現(xiàn)。換言之,如果一家企業(yè)只雇傭低技能勞動(dòng)力,那么其在2003年以前的工資扭曲改善就是由于低技能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規(guī)模效應(yīng)”導(dǎo)致的,因?yàn)閿U(kuò)招的勞動(dòng)力尚未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本文首先將低技能勞動(dòng)力定義為大專以下學(xué)歷的勞動(dòng)力。利用2004年的數(shù)據(jù),本文只使用大專學(xué)歷率為0的企業(yè)進(jìn)行回歸。由于2003年以后可能還存在“空間效應(yīng)”的干擾,故這一部分只使用1999—2003年的樣本進(jìn)行回歸。回歸式如式(13)所示。
ΔDistorti=α+βExpansioni×ΔL_proi+Φ∑Xi,1999+Γ∑ΔXi+μ1Ind_FE+μ2Type_FE+
μ3City_FE+εi(13)
回歸結(jié)果如表6所示,第(1)—(3)列中只使用了大專學(xué)歷率為的樣本進(jìn)行回歸。所有系數(shù)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高校擴(kuò)招顯著降低了低技能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工資扭曲情況。高校擴(kuò)招力度越大,工資扭曲的下降幅度將會(huì)越大。第(4)—(6)列為使用全樣本的回歸結(jié)果。結(jié)果表明高校擴(kuò)招的規(guī)模效應(yīng)對(duì)總體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影響不顯著,而只作用在低技能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上。這與動(dòng)態(tài)DID檢驗(yàn)中的平行趨勢(shì)結(jié)果相呼應(yīng),證實(shí)了平行趨勢(shì)的有效性。因此假說2得以成立。
(二)人口流動(dòng)與工資扭曲
其次,本文考察高校擴(kuò)招導(dǎo)致的空間效應(yīng)。由于無法直接觀測(cè)城市中擴(kuò)招的學(xué)生有多少來自異地,本文使用城市省屬高校的比例(ssbl)作為代理變量衡量這一指標(biāo)。選取這一指標(biāo)的邏輯在于地方(省屬)高校更
多地招收本地或省內(nèi)學(xué)生,而央屬與部屬高校的擴(kuò)招則輻射全國(guó),使得該城市流入更多異地的學(xué)生,故對(duì)當(dāng)?shù)氐膭趧?dòng)力市場(chǎng)沖擊更大。除了學(xué)生群體自身的流動(dòng),人口遷移還存在乘數(shù)效應(yīng)。遷移學(xué)生對(duì)服務(wù)業(yè)等相關(guān)行業(yè)的需求,也會(huì)引致更多的人口流入來滿足。因此,城市中省屬高校比例越低,央屬高校與部屬高校比例越高,招收異地學(xué)生越多,人口流入也就越多。
由于在理論分析部分,本文認(rèn)為人口流動(dòng)與工資扭曲的關(guān)系是非線性的,因此本文在回歸方程中加入了省屬高校比例的一次項(xiàng)與平方項(xiàng),分別與處理變量進(jìn)行交乘。回歸結(jié)果報(bào)告在表7中,一次交互項(xiàng)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而二次交互項(xiàng)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結(jié)果表明隨著省屬高校比例的提升,高校擴(kuò)招首先推動(dòng)工資扭曲降低, 隨后對(duì)工資扭曲的作用由抑制轉(zhuǎn)為促進(jìn)。同時(shí)在異質(zhì)性檢驗(yàn)中,本文也發(fā)現(xiàn)中間規(guī)模的城市工資扭曲下降最多,從而為這一機(jī)制提供了輔助性證據(jù)。因此假說3也得到驗(yàn)證。
六、結(jié)論與展望
本文將高校擴(kuò)招政策視為準(zhǔn)自然實(shí)驗(yàn),通過創(chuàng)新性地構(gòu)建測(cè)度方法,利用雙重差分模型評(píng)估了勞動(dòng)力供給外生沖擊對(duì)工資扭曲的因果效應(yīng),緩解了以往研究中的內(nèi)生性問題。研究發(fā)現(xiàn):第一,高校擴(kuò)招政策顯著降低了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工資扭曲程度。在考慮了一系列干擾因素后,這一結(jié)論依然是穩(wěn)健的。第二,機(jī)制檢驗(yàn)表明,高校擴(kuò)招能夠通過“規(guī)模效應(yīng)”和“空間效應(yīng)”兩種機(jī)制影響工資扭曲。第三,高校擴(kuò)招對(duì)工資扭曲的影響存在異質(zhì)性。在城市層面,中間規(guī)模城市的工資扭曲下降最多,這與空間效應(yīng)的解釋相一致。而在企業(yè)層面,國(guó)有企業(yè)的工資扭曲下降幅度最大,其他類型企業(yè)的工資扭曲程度沒有顯著差異。
本文的核心政策含義在于高等教育擴(kuò)張不但能夠促進(jìn)人力資本積累,還會(huì)改變地方勞動(dòng)力供給,從而影響要素價(jià)格。由于空間效應(yīng)的存在,高等教育在何時(shí)、何地、何類行業(yè)擴(kuò)張就顯得尤為重要。基于上述結(jié)論,本文的政策建議如下:第一,在保證高等教育數(shù)量的基礎(chǔ)上,提升高等教育質(zhì)量,切實(shí)提升勞動(dòng)力技能水平,充分發(fā)揮“規(guī)模效應(yīng)”。第二,在人口流入城市中,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升級(jí),提高對(duì)高技能勞動(dòng)力的需求,降低“競(jìng)爭(zhēng)效應(yīng)”。堅(jiān)持人口流動(dòng)的市場(chǎng)化調(diào)節(jié)機(jī)制,盡可能地發(fā)揮“集聚效應(yīng)”。第三,優(yōu)化國(guó)有企業(yè)的資源配置效率。同時(shí)為民營(yíng)企業(yè)營(yíng)造良好營(yíng)商環(huán)境,降低兩類企業(yè)的工資扭曲程度。
參考文獻(xiàn):
[1]都陽, 曲玥. 勞動(dòng)報(bào)酬、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與勞動(dòng)力成本優(yōu)勢(shì): 對(duì)2000—2007年中國(guó)制造業(yè)企業(yè)的經(jīng)驗(yàn)研究[J]. 中國(guó)工業(yè)經(jīng)濟(jì), 2009(5): 25-35.
[2]王寧, 史晉川. 中國(guó)要素價(jià)格扭曲程度的測(cè)度[J]. 數(shù)量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研究, 2015(9): 149-160.
[3]鈔小靜, 沈坤榮. 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勞動(dòng)力質(zhì)量與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J]. 經(jīng)濟(jì)研究, 2014(6): 30-43.
[4]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國(guó)的奇跡: 發(fā)展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jì)改革[M]. 上海: 三聯(lián)出版社, 1994.
[5]陳林, 羅莉婭, 康妮. 行政壟斷與要素價(jià)格扭曲: 基于中國(guó)工業(yè)全行業(yè)數(shù)據(jù)與內(nèi)生性視角的實(shí)證檢驗(yàn)[J]. 中國(guó)工業(yè)經(jīng)濟(jì), 2016(1): 52-66.
[6]耿偉, 廖顯春. 要素市場(chǎng)扭曲與企業(yè)內(nèi)資源配置: 基于多產(chǎn)品企業(yè)核心產(chǎn)品出口比重的研究[J]. 財(cái)貿(mào)經(jīng)濟(jì), 2017(10): 146-160.
[7]盛仕斌, 徐海. 要素價(jià)格扭曲的就業(yè)效應(yīng)研究[J]. 經(jīng)濟(jì)研究, 1999(5): 3-5.
[8]戴魁早, 劉友金. 要素市場(chǎng)扭曲如何影響創(chuàng)新績(jī)效[J]. 世界經(jīng)濟(jì), 2016(11): 54-79.
[9]吳先明, 張楠, 趙奇?zhèn)? 工資扭曲、種群密度與企業(yè)成長(zhǎng): 基于企業(yè)生命周期的動(dòng)態(tài)分析[J]. 中國(guó)工業(yè)經(jīng)濟(jì), 2017(10): 137-155.
[10]蒲艷萍, 顧冉. 勞動(dòng)力工資扭曲如何影響企業(yè)創(chuàng)新[J]. 中國(guó)工業(yè)經(jīng)濟(jì), 2019(7): 137-154.
[11]張明志, 鐵瑛, 傅川. 工資扭曲對(duì)中國(guó)企業(yè)出口的影響: 全球價(jià)值鏈視角[J]. 經(jīng)濟(jì)學(xué)動(dòng)態(tài), 2017(6): 58-72.
[12]劉燦, 宋光輝. 高校擴(kuò)招過程中的規(guī)模經(jīng)濟(jì)和范圍經(jīng)濟(jì)[J]. 經(jīng)濟(jì)理論與經(jīng)濟(jì)管理, 2004(1): 44-48.
[13]登云, 齊恬雨. 論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人才培養(yǎng)[J]. 中國(guó)高教研究, 2016(4): 15-22.
[14]邢春冰, 李實(shí). 擴(kuò)招“大躍進(jìn)”、教育機(jī)會(huì)與大學(xué)畢業(yè)生就業(yè)[J]. 經(jīng)濟(jì)學(xué)(季刊), 2011(4): 1187-1208.
[15]周茂, 李雨濃, 姚星, 等. 人力資本擴(kuò)張與中國(guó)城市制造業(yè)出口升級(jí): 來自高校擴(kuò)招的證據(jù)[J]. 管理世界, 2019(5): 64-77.
[16]繆宇環(huán). 我國(guó)過度教育現(xiàn)狀及其影響因素探究[J]. 統(tǒng)計(jì)研究, 2013(7): 48-54.
[17]馬光榮, 紀(jì)洋, 徐建煒. 大學(xué)擴(kuò)招如何影響高等教育溢價(jià)?[J]. 管理世界, 2017(8): 52-63.
[18]吳曉剛. 1990—2000年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學(xué)校擴(kuò)招和教育不平等[J]. 社會(huì), 2009(5): 88-113.
[19]初帥. 高等教育發(fā)展與人口城鎮(zhèn)化: 來自中國(guó)高校擴(kuò)招的證據(jù)[J]. 中國(guó)人口科學(xué), 2016(4): 105-112.
[20]安孟, 張誠(chéng). 環(huán)境規(guī)制是否加劇了工資扭曲[J]. 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 2020(7): 118-128.
[21]MATTHEW M F, ANDREA M. Persistent distortionary policie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1): 387-393.
[22]邵敏, 包群. 外資進(jìn)入是否加劇中國(guó)國(guó)內(nèi)工資扭曲: 以國(guó)有工業(yè)企業(yè)為例[J]. 世界經(jīng)濟(jì), 2012(10): 3-24.
[23]安孟, 張誠(chéng). 外資進(jìn)入能改善中國(guó)的工資扭曲嗎: 基于中國(guó)省級(jí)動(dòng)態(tài)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J]. 經(jīng)濟(jì)與管理研究, 2019(8): 63-75.
[24]HARRIS J R,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1): 126-142.
[25]楊振兵, 張誠(chéng). 《勞動(dòng)合同法》改善了工資扭曲嗎: 來自中國(guó)工業(yè)部門的證據(jù)[J]. 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研究, 2015(5): 52-62.
[26]蒙大斌, 楊振兵. 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分割加劇了工資扭曲嗎: 來自中國(guó)省際工業(yè)部門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J]. 財(cái)經(jīng)論叢, 2016(9): 10-17.
[27]王鑫, 齊秀琳, 雷鳴. 工頭制、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分割與工資扭曲: 來自近代工業(yè)的證據(jù)[J]. 南開經(jīng)濟(jì)研究, 2018(5): 115-132.
[28]陳斌開, 陸銘. 邁向平衡的增長(zhǎng): 利率管制、多重失衡與改革戰(zhàn)略[J]. 世界經(jīng)濟(jì), 2016(5): 29-53.
[29]李洪亞, 史學(xué)貴, 張銀杰. 融資約束與中國(guó)企業(yè)規(guī)模分布研究: 基于中國(guó)制造業(yè)上市公司數(shù)據(jù)的分析[J]. 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科學(xué), 2014(2): 95-109.
[30]趙毅博. 中國(guó)高校擴(kuò)招對(duì)城鄉(xiāng)青年人口遷移的影響[J]. 人口學(xué)刊, 2019(4): 94-103.
[31]CHE Y, ZHANG L. Human cap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mpact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 the late 1990s[J]. Economic Journal, 2018, 128(614): 2282-2320.
[32]魯曉東, 連玉君. 中國(guó)工業(yè)企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估計(jì): 1999—2007[J]. 經(jīng)濟(jì)學(xué)(季刊), 2012(2): 541-558.
[33]NUNN N, NANCY Q. The potato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a historical experi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126(2): 593-650.
[34]DOBBELAERE S, KIYOTA K. Labor market imperfections, markups and productivity in multinationals and exporters[J]. Labour Economics, 2018, 53: 198-212.
[35]魏下海, 董志強(qiáng). 城市商業(yè)制度環(huán)境影響勞動(dòng)者工資扭曲嗎: 基于世界銀行和中國(guó)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的經(jīng)驗(yàn)研究[J]. 財(cái)經(jīng)研究, 2014(5): 4-18.
[36]李嵐清. 李嵐清教育訪談錄[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119-121.
[37]楊崇龍. 我國(guó)高校擴(kuò)招政策的提出和終止[J]. 云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07(2): 151-153.
[38]BRANDT L, BIESEBROECK J V,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339-351.
[39]聶輝華, 江艇, 楊汝岱. 中國(guó)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的使用現(xiàn)狀和潛在問題[J]. 世界經(jīng)濟(jì), 2012(5): 142-158.
[40]楊汝岱. 中國(guó)制造業(yè)企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研究[J]. 經(jīng)濟(jì)研究, 2015(2): 61-74.
責(zé)任編輯、校對(duì): 李再揚(yáng)
Doe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mprove Wage Distor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AI Siyuan, LU Ju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labor supply on wage distortion are often limited to draw reliable conclusions because of endogeneity. Regarding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s an exogenous shock on labor supp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ovel measur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employs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evaluate the causal effect on wage distor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wage distortion.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scale effect” and “spatial effect” are two important mechanisms that affect wage distortion. The “scale effect” is that colleges absorb potential surplus labor and reduce the wage distortion caused by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The “spatial effect”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labor mobility on wage distortion will change from restraining to promoting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city size. The heterogeneity test suggests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restraining effect on the wage distor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n other type of enterprises. At the urban level, wage distortion has been reduced most in middle-sized cities.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wage distortion; human capital; population mobility
收稿日期:2020-12-07。
作者簡(jiǎn)介:蔡思遠(yuǎn),男,通信作者,北京大學(xué)政府管理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電子郵箱:georgecsy@pku.edu.cn;
陸軍,男,北京大學(xué)政府管理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城市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
 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科學(xué)2021年4期
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科學(xué)2021年4期
- 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水平對(duì)城市創(chuàng)新效率的影響研究
- 環(huán)境污染、技術(shù)創(chuàng)新強(qiáng)度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jí)
- 環(huán)境信息披露如何影響企業(yè)創(chuàng)新
- 地區(qū)社會(huì)信任對(duì)企業(yè)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影響研究
- 成長(zhǎng)沖動(dòng)與風(fēng)險(xiǎn)對(duì)沖:經(jīng)濟(jì)政策不確定性如何影響企業(yè)海外并購(gòu)
- 制度環(huán)境、所有制差異與內(nèi)資獨(dú)資化績(jī)效評(píng)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