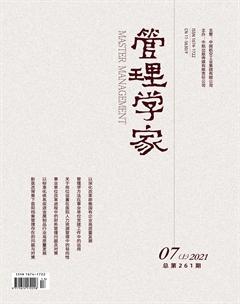心理契約視角下IT行業90后知識型員工的離職傾向研究
成勝楠
[摘 要] 新一批90后知識型員工具備知識與技能,對處在IT行業的企業發展至關重要。文章首先介紹了心理契約、離職傾向、工作滿意度等核心概念,然后提出了IT行業90后知識型員工的特征,進而分析了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心理契約對離職傾向的研究,構建出心理契約視角下IT行業90后知識型員工的離職傾向研究——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的理論模型,最后總結出這次研究的不足與未來展望。
[關鍵詞] 心理契約;IT行業;90后知識型員工;離職傾向
中圖分類號:F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2(2021)13-0048-0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8BGL139);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資助項目(17YJC630074)
如今,信息技術發展帶動著整個IT行業的快速發展,90后更是與互聯網發展密切相關。這批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90后逐漸進入職場,在企業中從事管理、技術研發、營銷等腦力勞動,被稱作知識型員工,他們逐漸成為IT行業發展的中流砥柱。但目前來看,90后知識型員工這個群體更換工作速度較快,離職率較高,這導致了整個IT行業的不穩定。
針對90后知識型員工離職率偏高的現象,管理學界展開激烈討論。國內外學者對員工離職傾向這個問題已經有了眾多的研究,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豐碩,但是具體針對IT行業90后知識型員工,尤其是國內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不夠完善,主要原因在于離職傾向的影響因素多而散,且這批90后知識型員工初入職場。
因此,筆者基于大量的國內外相關文獻,首先,闡述心理契約、工作滿意度和離職傾向的理論概念;其次,構建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模型,并采用回歸分析等方法檢驗模型,揭示影響IT行業90后知識型員工離職的因素;最后,提出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心理契約與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的萌芽最初產生于《經理人的職能》這一經典著作,該著作強調了在變革時代雇主與雇員溝通的重要性。而離職傾向是員工離開現在所在職位,去新的崗位工作的心理傾向強度(March、Simon,1958年)。心理契約違背了經典模型——雇員的 EVLN 行為分類模型中提到,如果員工受到心理契約違背感知,就會采取退出、呼吁、組織忠誠以及忽略行為[1-5]。針對第一種行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發現心理契約對員工離職傾向具有負面影響。
H1:心理契約與離職傾向的關系為負相關,且是顯著的。
(二)心理契約與工作滿意度
面對外部環境因素,員工從心理和生理兩個角度都感到滿意,這就是所謂的工作滿意度(Hoppock,1935年)。之后國內外學者紛紛證明了這一觀點,Porter(1998年)研究發現雇員與雇主的心理契約的差距與員工的滿意度呈負相關;周興(2008年)通過調查銀行柜員,發現柜員的心理契約與工作滿意度是正相關的[6]。
H2:心理契約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為正相關,且是顯著的。
(三)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
工作滿意度實際上反映的是員工個人的主觀感受(李利玲,2013年),會影響員工行為及績效,甚至員工會離職。雖然對于這方面,國內外學者進行大量實證研究,但仍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果。少數學者認為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之間并無顯著的相關,而大多數學者發現兩者之間呈負相關,如國外學者Hutchins和Tuttle(1979年)發現員工離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不滿意現在的工作[7-9]。
H3: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的關系為負相關,且是顯著的。
(四)工作滿意度的中介作用
內外部工作因素對員工心理感受產生不同作用,而這就說明了工作滿意度受到多方面影響。之前有學者已研究出工作滿意度在多個變量關系之間起到中介作用。例如,國外學者Turnkey 和 Feldman(2000年)發現工作滿意度在心理契約與離職傾向之間,工作滿意度起到部分中介效用;國內學者張勉和李樹茁(2001年)研究發現在人口變量與離職傾向之間,工作滿意度是一個中間變量[10-12]。
H4:在心理契約與離職傾向之間,工作滿意度具有中介效用。
(五) 實證研究模型
本研究將90后知識型員工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心理契約、工作滿意度以及離職傾向三者之間的關系。因此構建了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二、研究方法
(一)調研對象與樣本收集
本研究針對IT企業的 90 后知識型員工,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共發放問卷118 份,回收問卷 118 份,其中有效問卷 118 份,回收率為 100%,有效率為 100%。
(二)測量工具
心理契約量表參考Rousseau (1998,2000年)編制的心理契約調查問卷和 Millard (1998年)編制的心理契約測量問卷以及李原(2002年)設計的員工一企業關系調查問卷。工作滿意度量表借鑒明尼蘇達工作滿意度短式量表(MSQ)。關于離職傾向量表,本研究編制出相關的4個問題。這三個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點尺度記分。
(三)量表信效度
本文對心理契約量表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其KMO值為0.770,大于0.7,表示相關情況良好。心理契約量表數據顯著性概率為0.000,企業責任和員工責任兩個維度的 Cronbachα值分別為 0.778、0.773,說明這份心理契約量表是可以接受的量表。關于工作滿意度量表,結果顯示其KMO值達0.760。關于工作滿意度量表的 Cronbachα值為0.82,達到理想水平。關于離職傾向量表,結果顯示 KMO 檢驗值為0.779,大于0.7,說明樣本數合適。離職傾向量表的 Cronbach α值為0.804,達到理想水平。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相關分析
心理契約、企業責任、員工責任與離職傾向在0.01顯著水平上的負相關,其系數分別為-0.240、-0.292以及-0.173。心理契約、企業責任、員工責任與滿意度為 0.01顯著水平上的正相關,其系數分別為0.868、0.842及0.839。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為在0.05顯著水平上的負相關,其系數為-0.215。
(二)回歸分析
1.心理契約對離職傾向的回歸分析
離職傾向為因變量,心理契約企業責任和員工責任為自變量[13]。由回歸分析結果可知,F值為7.344。心理契約量表數據顯著性概率是0.001。且調整后的判定系數R2為0.098,那么心理契約的兩個維度對離職傾向有9.8%的解釋力。心理契約的企業責任對離職傾向有明顯的負向影響,而員工責任對離職傾向有正向影響。
2.心理契約對工作滿意度的回歸分析
工作滿意度為因變量,心理契約企業責任和員工責任為自變量。從回歸分析效果來看,F值為175.80。心理契約量表數據顯著性概率為0.000,小于0.001,非常顯著[14-16]。調整后的判定系數R2為0.749,可知心理契約的兩個維度對離職傾向有74.9%的解釋力。心理契約兩個因子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是正向的。
3. 工作滿意度對離職傾向的回歸分析
離職傾向為因變量,工作滿意度為自變量。從回歸分析效果來看,F值為5.60,工作滿意量表數據顯著性概率為0.02。因調整后的判定系數R2為0.038,可知工作滿意度對離職傾向有3.8%的解釋力。工作滿意度對離職傾向為負向影響。
4. 檢測中介作用
回歸模型1中,離職傾向與心理契約回歸系數為-1.142,其回歸關系顯著相關。回歸模型2中,工作滿意度與心理契約回歸系數為0.868,顯著相關。回歸模型3中,離職傾向與工作滿意度回歸系數為-0.215,顯著相關。回歸模型4中,離職傾向與工作滿意度回歸系數為-0.023;離職傾向與心理契約回歸系數為-0.220,這兩者關系都顯著相關。但心理契約對離職傾向回歸系數絕對值從回歸模型1中的1.142下降到回歸模型4中的0.220,這說明在心理契約和離職傾向的關系中,工作滿意度起部分中介作用。
四、實證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經過閱讀文獻、問卷設計與調查及數據分析等一系列過程,將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確定了心理契約、工作滿意度及離職傾向三者之間的關系。在本研究中,個人特征不會對心理契約及其各維度、工作滿意度和離職傾向產生顯著性影響,整體規律性不強,方向也并非一致[17-18]。對于研究假設的檢驗,假設回歸模型1、2、3中的驗證結果成立,假設回歸模型4中的驗證結果部分成立。
五、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第一,本研究所采用的問卷是借鑒國外學者開發的問卷,但不一定適合我國背景,這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我國背景下開發更適合的問卷。
第二,本研究搜集的問卷數量不足,針對個人特征對心理契約及其各維度、工作滿意度和離職傾向是否有顯著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之后的研究應該增加問卷的數量,以增加研究的可信度。
第三,本研究研究的變量僅僅為心理契約、工作滿意度、離職傾向三個變量,所以未來的研究,可以加入其他的變量,例如組織政治知覺、組織承諾等,一并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崔京京.90后新生代員工心理契約違背研究[J]. 管理觀察,2015(12):188-190.
[2]陳恬. 90后知識型員工心理契約對離職傾向的影響[D].重慶:西南大學,2019.
[3]陶小紅.90后知識型員工離職傾向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金華:浙江師范大學, 2018.
[4]馬菱,車麗萍.心理契約視角下新生代員工離職傾向[J].改革與開放,2015(20):62-63.
[5]蘭玉杰,張晨露. 新生代員工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關系研究[J].經濟管理, 2013 (09):81-88.
[6]馮麗娜. 知識型員工離職傾向影響因素分析[J]. 合作經濟與科技, 2011 (24):84-85.
[7]曹威麟, 陳文江. 心理契約研究述評[J].管理學報,2007(05):682-687,694.
[8]何霞. 心理契約違背國內外研究綜述[J]. 商業時代, 2009 (22):54-56.
[9]魏峰. 組織—管理者心理契約違背研究[D/OL]. 上海:復旦大學,2004.
[10]蘇中興, 劉松博.知識型員工心理契約的內容, 結構與違背研究[J].管理評論, 2007, 19(11):35-41.
[11]朱曉妹, 王重鳴.中國背景下知識型員工的心理契約結構研究[J].科學學研究, 2005, 23(01):118-122.
[12]鄭子林.知識型員工心理契約違背的影響及預防措施探析[J]. 管理世界, 2014 (04):1-4.
[13]曾斌.心理契約、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的關系實證研究[D/OL]杭州:浙江理工大學,2010.
[14]Hicks M, Monroy-Paz J. Into the Looking Glass: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2015;46(1):77-101.
[15]Bal P M, De Cooman R, Mol S T. Dynamics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with work engage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tenure[J].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3, 22(1): 107-122.
[16]McDonald D J, Makin P J.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rganis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temporary staff[J].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00, 21(2): 84-91.
[17]Rayton B A, Yalabik Z Y. Work engagement,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job satisfaction[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4, 25(17): 2382-2400.
[18]Qian X, Shi Y, Zhou H. Chinese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s: Effects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ies[C]//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pringer,Berlin, Heidelberg, 2015:1077-1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