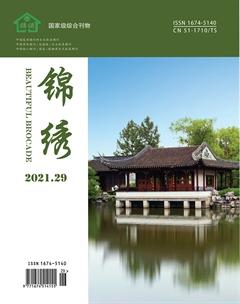鹽商修建揚州園林原因分析
王瀅瀅
摘要:鹽業事關民生大計,鹽商富甲一方。當生存需求得到滿足,隨之而來的是精神世界的享受。他們在住宅方面精益求精,關注園林的格局、構景、規模。是基于經濟基礎,追求雅奢的社會風氣,以及清朝統治者南巡的契機。揚州鹽商豐富了江南地區園林文化的內涵,影響不可等閑視之。
關鍵詞:鹽商;揚州園林;乾隆南巡
揚州素來有“園林城市”的美稱,清朝鹽商崛起是揚州園林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曰:“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輊。”[1]園林建筑的一磚一瓦見證當時揚州社會生活,熔鑄鹽商文化的烙印。揚州鹽商耗費巨資,形成了眾多私家園林爭奇斗艷的獨特景觀。這些園林行過時代的洪流,仍然熠熠生輝鐫刻著歷史的印記。目前探討鹽商與揚州關系文章,主要從飲食、戲曲、藏書等方面著手。關于園林的文章偏重描述園林的景色,而其修建的背景很少有人探究。究竟是怎樣的動因,推動鹽商斥巨資修建園林呢?筆者試圖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1鹽商經濟實力為建園提供堅實基礎
鹽業貿易促進大量白銀在揚州流通,激發市場活力,為其園林文化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鹽與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明朝萬歷年間實行綱鹽法,鹽商專買專賣制度逐步確立。鹽商對鹽的買賣具有壟斷特權,經營利潤十分可觀。古代揚州地區是重要的鹽產地,揚州地區鹽業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明清發展達到鼎盛時期。鹽場分布廣數量多,制鹽成本低利潤高。大運河航運便利溝通南北,使揚州地區成為淮南、淮北一代鹽業集散紐帶。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吸引各地商人紛至沓來。明清時期長途販運貿易成熟商品經濟發達,擴大了區域間商品信息交流。食鹽市場廣闊,遠銷各地,其中遠至湖南等地。揚州鹽商壟斷了食鹽貿易,迅速積累大量財富。
2文化追求風雅奢靡之氣園林增長如雨后春筍
鹽商將風雅和奢靡統一于園林追求,明清時期揚州成為園林極盛之地。古人講究重義輕利農本商末,謂之“士農工商”,以傳統四民社會價值觀念作為尺度,商人的社會地位可見一斑。揚州鹽商中徽商舉足輕重,而徽商素有“賈而好儒”的美譽。徽州汪道昆有云:“夫賈為厚利, 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 則弛儒而張賈; 既側身饗其利矣, 及為子孫計, 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 迭相為用。”[2]鹽商并沒有將經濟活動與文化活動割裂開來,將二者有機結合以求全面發展。加之“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足。”鹽商不愿囿于刻板印象,試圖扭轉世人對商人看法。一方面,追求“官商” 身份的加持,并借風雅之事以提高威望。有直接通過“捐官”獲得一官半職,“鯉魚躍龍門”一舉躋身官員行列。亦有重視教育,鼓勵家中后輩乃至族中弟子邁入仕途并提供經濟保障,為興辦書院進一臂之力。多方斡旋,解決商人子弟僑居外地科考不易的現實問題。鹽商子弟也不負眾望,在科考中取得驕人成績,揚州地區金榜題名者很大一部分是旅居客商子弟。同時追求風雅,與當時名聲赫赫,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文人群體頗有交情。園林中不乏文人墨客的作品,以及體現自已逸趣的楹聯。另一方面,鹽商參與經濟活動,住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財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鹽商購置房產,精雕玉琢爭奇斗艷,極盡其能。住宅景色賞心悅目曲徑通幽,花園石塊堆疊,門窗屋檐雕梁畫棟,雖不及鐘鳴鼎食之家底蘊深厚,卻也別有一番風味。竹影斑駁種類繁多,寓意吉祥。四時之景不同,根據季節特點在構景構造大相徑庭,置身其中心曠神怡。同時冬暖夏涼、避火防盜兼具實用功能。亦可作為宴請賓客之地,與商友盡顯主人財富與智慧。清朝揚州城內外,亭臺樓閣鱗次櫛比,鹽商攀比蔚然成風。
3清統治者江南巡游為官商合作提供契機
清朝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揚州,巡游背后的利益鏈條錯綜復雜。地方官府與鹽商各取所需,鹽業、鹽商、官員關系微妙。一方面,清朝鹽商壟斷特權來源于清朝統治者,出于經濟和政治利益的需要,長袖善舞的鹽商與當權者相處融洽。當權者登臨,作為揚州本地的富商大賈自當進“地主之誼”。是以當時,鹽商斥巨資修建帝王行宮、整頓街道、建造景點,甚至豢養規模可達百人的戲班。另一方面,鹽商協助本地官員將當權者行程安排的滴水不漏,其中好處不言而喻。乾隆年間有上諭稱:“朕此次南巡,所有兩淮眾商承辦差務,皆能踴躍急公,宜沛特恩,以示獎勵。”[3]今上的封賞和嘉獎,不僅為其在鹽務大開方便之門,使其在鹽業經營上如魚得水,也大大提高了其社會地位。其中領頭的鹽商,在一眾商人中的話語權更是大大增加。于官不用自己勞民傷財解決資金問題,南巡一應事宜安排的盡善盡美,有望得到當權者青睞從而加官進爵。于商借機結識達官顯貴,進一步穩固自己鹽業的壟斷地位,擴大自己鹽業話語權。
鹽商經濟基礎堅實、追求奢雅之風、偶遇皇帝南巡的東風,在多種歷史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揚州園林深深打上了鹽商文化的烙印。揚州鹽商在住宅上花費巨資,后人對其評價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揚州園林文化,為現代建筑和園藝提供借鑒。除此之外,園林的楹聯和其建筑包含的美學思想,亦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
注釋
[1](清)李斗: 《揚州畫舫錄》卷6《城北錄》,第 151 頁。
[2](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陽處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銘》,第1099頁。
[3]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1《巡幸一》,第1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