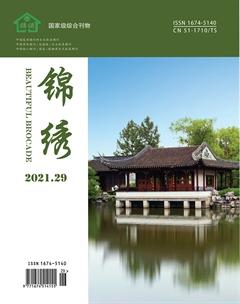讀薛永年《稱“中國畫”還是叫“水墨”》有感
李靜怡
摘要:“中國畫”與“水墨”二者相互交融生長,不論是好的中國畫還是“新水墨”,都要立足于優秀的民族核心價值觀,以高度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動民族藝術的創新發展,開拓豐富中國畫的表現力,將“新水墨”基于中國傳統的同時也要牢牢立足于全球化藝術時代之中。為民族繪畫藝術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時突破狹隘的民族文化視野而具有跨文化的穿越能力。從傳統中國繪畫中形成現代化的探索并為在此之間產生的優秀藝術保持強有力的生命力。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確立文化身份,建立文化自信的同時能夠以開放的心態參與人類文化的共建,推動世界文化的發展。
關鍵詞:新水墨;中國畫;發展;精神
讀薛永年教授發表在2019年《美術觀察》第五期中關于中國畫VS水墨專題中的文章,引發了我對目前“中國畫”和“水墨畫”的發展的思考,薛永年教授在文章中表達了他從美術史的角度看待對現中國“水墨熱”的現象的獨特見解。
在文章中他就“水墨畫”能否代替“中國畫”這一問題展開了辨析,說到中國畫的概念是近代的產物,因為受到西方繪畫傳入中國的影響,與“西洋畫”產生對立面才有了“中國畫”,這就使“中國畫”這個名稱中包含了獨特的民族性,強調了我們獨有的民族文化,民族價值觀和民族精神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稱謂。而“水墨畫”在中晚唐以來,成為中國繪畫歷史上的主流繪畫,它蘊含了中國獨有繪畫的藝術特色,傳承我國的文化脈絡,使這種獨特的繪畫藝術長久的矗立在我國的文化長河中不被其他外來畫種所替代,更加強調了中國畫是一種具有鮮明特色的畫種。近年來,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多以“水墨畫”命名的畫展中,是要以材料媒介的方法被西方所理解,更是一種有效的國際交流策略,但是并不等于把“中國畫”改為“水墨畫”。在時代不斷發展之中,中國畫的發展也在不斷地推陳出新,出現了“新水墨”,“新水墨”與中國畫的關系薛教授是這么表達的,他說“動態地觀察中國畫與新水墨的關系,可以發現二者在交融中此消彼長,堅持了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中國畫,在守正中延展,領域在緩慢的擴大。新水墨越來越擺脫西方的影響,在突破中回歸,部分融入了中國畫之后,仍然繼續新的探索。”可以在文章中總結出中國畫與“新水墨”是共同發展的,不是單純的替代與被替代的關系,而是保持各自的文化張力,推動當代民族藝術的發展。
我認同“新水墨”的出現可以說是我們在適應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拓寬了原本中國畫的概念,使原本不在中國畫范圍內的作品,以“新水墨”的形式不斷發展,但是當代中國“新水墨”該何去何從?我們是否應該從水墨文化生成的根源再談當代“新水墨”該如何發展?而“中國畫”究竟應該如何在數字文明的趨勢下展現出它新的一面?水墨藝術作為中國特有的一種藝術樣式構成了獨具特色的水墨文化,這個系統包括了材料媒介、符號語言、美學價值體系,是一種綜合而成的規范。五代梁荊浩在《筆法記》中提到:“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荊浩曾說過:“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采二子之長,成一家之體。” “吳道子筆勝于象,骨氣自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從這些評論中可見他對筆墨的重視和追求,但是他強調不要一味的重視筆墨,而是一同強調畫中的氣、韻。而對于筆墨的講究,則標志著水墨畫走向成熟。當然,要充分發揮出水墨畫的表現力自然離不開筆與墨,畫家只有通過筆與墨的自如運用,畫面之氣韻方得以展現,正如北宋韓拙《山水純全集》云:“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 北宋時期以歐陽修、蘇軾為代表的士大夫集團極力提倡“意”的觀念,豐富了文人畫的精神內涵,水墨畫成為文人畫家表“意”的有效媒介。文人士大夫加入繪畫行列在唐宋之際促成了水墨畫的形成。道家哲學追求天人合一,返璞歸真的美學思想和儒家的人格理想和節義思想構成了水墨文化的價值基礎。從古至今的水墨文化發展構成了水墨文化獨特的藝術規范,表現出中國畫獨有的精神境界和獨特追求。
近代中國“新水墨”就出現了一種矛盾,究竟什么才算好的新水墨藝術?當代水墨藝術可以大致分為三類,第一種是書寫型水墨,第二類是繪圖型水墨,第三種是思想觀念型水墨。第一種水墨是以傳統水墨的用筆方式,結合書法中的書寫章法,結合西方抽象概念的構成方式形成一種裝飾意味強烈的獨特語言。這種方式將水墨作為裝飾表現語言的一種形式,脫離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容易形成空洞的、概念化的藝術。第二種是將“水墨”作為國畫的一種工具材料來表現出一種新的繪畫形式。完全的脫離中國畫的表現形式,形成新的繪制方式。第三種,運用西方繪畫的方式,將水墨用于裝置、影像等等其他的綜合藝術形式,表現出西方藝術觀念。
雖然在今日新水墨藝術的邊界已經十分模糊,在東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下,為了突破中國傳統水墨畫的概念,體現“新水墨”而創造出不同材料形式的新水墨作品,但是這些從紙本水墨擴展至三維立體水墨特色的裝置藝術,有很大一部分缺失了中國水墨中的逍遙境界與超越精神,只是運用了水墨作為創作的材料元素。一味的追求打破傳統迎合市場使水墨畫喪失了千年傳承的水墨精神,石濤曾全面而又系統地闡述了學習者面對繪畫傳統應當持有的態度:“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為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于似則不廣。古君子惟借古以開今有也。”當代水墨是時代的產物元時代中,文化之間碰撞出的產物,脫離出中國畫的“新水墨”如何才能擁有長久的生命力,多種方式的“新水墨”應該如何發展才能在體現傳統東方精神的深度下,涵蓋古典又接納現代,是現代水墨發展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立足當下,我們想要新水墨表現出長久的生命力仍要拋開水墨形式表層的東西,追求內在的精神需要,而這些內在的精神需要的三個因素分別是“1、每個作為創造者的藝術家的心中都擁有呼喚著表現得東西(這就是個性因素)。2、每個作為時代的孩子的藝術家都不得不表現他那時代的精神(這是風格因素)——受命于他所屬的時代和特定的國家。3、每作為藝術的仆人的藝術家都必須協助藝術事業(這是純藝術性的因素,這在所有時代和所有國家里都是永恒不變的)。”想要創作出有足夠影響力的水墨藝術就要,探索時代精神,結合藝術家想要在畫中傳達出的心中理想境界的表達,表達一個優秀的民族在新的藝術探索中所做出的努力。
90年代以后,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大環境下,對于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視,是我們在現代化轉型中仍然處于高地的文化策略。在日漸開放的文化環境中,中國畫不僅在研究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更多在形式語言上的探索和實驗。中國畫,也不是簡單的以地域命名的畫種,它體現的民族文化也是我們在不斷創新中不能拋開的精神內涵。
處于包容并蓄的多
中國畫的發展,離不開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蘊的深厚內涵,是中國畫得以獨特個性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的深厚根基。優秀的傳統文化為我們提供文化自信,吳冠中先生說過“我有研究過莫奈的池塘睡蓮垂柳,我研究過塞尚的綠色叢林,我喜愛他們的作品,但他們的技法都不能用來表現我的垂柳與竹林。”“風景哪邊好?祖國好,故鄉好,感情深處好”藝術家的藝術傾向建立在對本土的情感依托上。我們傳統的中國畫迥異于西方文化,是因為中國畫獨立地意識形態,追求“意境”的審美。中國畫中的“氣韻生動”是我國古人總結中國畫中應有的審美追求,以整體的大局觀展現畫面中的景與物的生動和諧,超越客觀存在的意象之美。要保持中國畫的優秀品質,就要深入的了解傳統典籍和史論,對傳統美學深入研究,通過藝術家的獨立思考,揚棄取舍,結合當代的時代精神,開放包容,創造出具有時代特征的作品。
近代向西方學習的思潮不斷影響中國畫的發展,以徐悲鴻,蔣兆和為主的藝術家主張在中國畫中融入西方的繪畫觀念。中國畫的創新是適應時代的必然選擇,我認為中國畫在不斷地自我突破當中,必須以保留優秀基因為基礎,保留中國畫中體現優秀民族精神和內涵為基礎,不斷的創新與傳承。傳承容易,創新不易。
要在以民族精神為根基的基礎上,大膽創新,表達新時代的中國精氣神,跟上全球化浪潮發展的腳步,在對外開放的交流中,汲取西方優秀藝術之精華,融入中國畫的創作當中,博采眾長“師與古卻不泥與古”,形成中國畫創新獨特的藝術風格。康定斯基對于時代產生的好的藝術是這樣的觀點“藝術是那個時代的孩子。這樣的藝術只能創造一種已經被清晰地感覺到的藝術感。凡是沒有向未來發展的能力的藝術,只是一個時代的孩子而不能變為未來的母親,它只是貧瘠的藝術。它是曇花一現的。實際上,只要周圍不再有滋養它的氛圍,它會立即死亡。”
“中國畫”與“水墨”二者相互交融生長,不論是好的中國畫還是“新水墨”,都要立足于優秀的民族核心價值觀,以高度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動民族藝術的創新發展,開拓豐富中國畫的表現力,將“新水墨”基于中國傳統的同時也要牢牢立足于全球化藝術時代之中。為民族繪畫藝術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時突破狹隘的民族文化視野而具有跨文化的穿越能力。從傳統中國繪畫中形成現代化的探索并為在此之間產生的優秀藝術保持強有力的生命力。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確立文化身份,建立文化自信的同時能夠以開放的心態參與人類文化的共建,推動世界文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瓦里西·康定斯基著.呂澎譯.論藝術里的精神[M].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