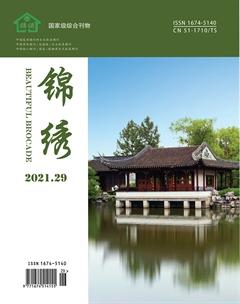周作人的日本觀與浮世繪
徐夢婷
摘要:周作人與日本以及日本文化有著深切復雜的聯系,他于1906年至1911年在日本留學的六年間里,接觸到了很多日本文化,這些文化對周作人的思想觀念、文學以及藝術方向的選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浮世繪便是其中之一。
關鍵詞:周作人;浮世繪;日本觀
一、周作人與浮世繪
浮世繪是江戶時代(1603年-1868年)在日本中流行的一種民間藝術——風俗畫。周作人在1917年3月發表《日本之浮世繪》一文,第一次向中國介紹日本的浮世繪,包括浮世繪的產生、發展以及著名的浮世繪畫師。在之后的三四十年代,依然可以在周作人的文章里看到他對浮世繪的介紹與評價。在這些文章里提到浮世繪時其中包含的感情、蘊含的意義也不同。本文以20世紀20年代為起點,探討周作人接下來的三十年里,不同時期對浮世繪不同的看法并分析其變化的原因。
二、周作人的思想變化
1.20世紀20年代——30年代
周作人第一次接觸到浮世繪是在一本叫做《此花》的雜志上,這本雜志主要內容是介紹浮世繪。談起中國繪畫,他認為“這大都是吉語的畫,如五子登科之類,或是戲文,其描畫風俗景色的絕少。這一點與浮世繪很不相同。我們可以說姑蘇板是十竹齋的通俗化,但壓根兒同是士大夫思想……。”[1]或者說“中國后來文人畫占了勢力,沒法子寫仕女了,近代任渭長的畫算有點特色,實在也是承了陳老蓮的大頭短身子的怪相的遺傳,只能講氣韻而沒有艷美,普通繡像的畫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畫只有差,因為他連氣韻也沒了。”[2] 就意圖和內容而言,浮世繪描繪了都市的風俗和男女的姿態,表現出江戶時代的世俗生活狀態。
日本近代唯美主義作家永井荷風對周作人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周作人十分欣賞永井荷風,在文章里多次提起永井先生并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斷引用永井荷風的話語,尤其是永井關于浮世繪的論述更是被周作人深深吸引。周作人曾引用了永井荷風對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隅田川兩岸一覽》這幅畫內容的描述:“開卷第一出現的光景乃是高輪的天亮。孤寂地將斗篷裏身的馬上旅人的后邊,跟著戴了同樣的笠的幾個行人,互相前后地走過站著斟茶女郎的茶店門口……第二圖里有戴頭巾穿禮服的武士,市民,工頭,帶著小孩的婦女,穿花衫的姑娘,挑擔的仆夫,都趁在一只渡船里,兩個舟子腰間掛著大煙管袋,立在船的頭尾用竹篙刺船,這就是佃之渡。”[3]永井荷風的這段描寫將文化初期的江戶風俗和氣氛栩栩如生地展現在紙上,就連中國社會里的存在的姑蘇版畫也難以相比,姑蘇版畫很少描繪習俗和風景,所以它的意圖與浮世繪非常不同。
中國士大夫自古就有一種濃厚的中華文化優越感。直到近代甲午戰爭的失敗,才迫使中國朝野開始睜眼關注日本,但是大部分人骨子里依然是中華尊大思想。浮世繪中素樸的風景、凡人的喜悲正和中國一些繪畫中的士大夫功名思想形成對比,批評中國存在的士大夫思想。
五四以來,周作人作為一個社會改造者積極參與社會生活,關心著國家的前途發展。但隨著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現實的極度失望,逐漸放棄了對社會改造的理想。在1928年以后民族主義思想開始沉寂,他基本不再寫文章發表對中日關系及中日社會文化的對比。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才從重新開始了對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研究。
2.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
當時的很多中國人認為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簡單移植,中國人去日本的目的,或是追尋在中國已經消失而在日本仍然存在的中國傳統文化。或是把日本看作世界文化的窗口。這實質上是對日本人民和文化的漠視,而且還沒有走出 “中國中心主義 ”的陰影。基于他在日本學習時的所聞所感,周作人深深意識到需要糾正當時中國人對日本文化的這種根深蒂固看法。
周作人于1936年在《談日本文化書之二》中提到:“假如要找出這民族的代表來問問他們的悲歡苦樂,則還該到小胡同大雜院去找,浮世繪工亦是其一。我的意思是,我們要研究,理解,或談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賢哲來……。”[4]之后,在1942年《日本之再認識》中:“在東亞民族間多是大同小異,從這里著眼看去,便自然不但容易理解,也覺得很有意義了。在十七八年前我曾說過,中國在他獨特的地位上特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就是這種思想......。”[5]從這些內容中可以看出周作人以日本浮世繪為例,號召中國學者重新認識日本的文化。
此后,1944年在《浮世繪》一文中提到:“畫面很是富麗,色澤也很艷美,可是這里邊常有一抹暗影,或者可以說是東洋色,讀中國的藝與文以至于道也總有此感,在這畫上自然也更明嘹。.......我們因為是外國人,感想未必完全與永井氏相同,但一樣有的是東洋人的悲哀,所以于當作風俗畫看之外,也常引起悵然之感......。”[6]在這里,浮世繪也傳達了一種冥冥中憂郁的悲哀,這是“東洋”所共有的,這是生活在一個專制時代一個凡人的的悲哀。簡而言之,浮世繪中所體現的“東洋人的悲哀”在周作人這里成為他以自己的人學思想關照東亞文明的審美感知結果。
三、結語
周作人對浮世繪的感情變化集中體現在他三四十年代所寫的文章里,浮世繪雖是具有美術意義,但周作人在探討浮世繪時對于它的美術意義的關注只占一小部分,對浮世繪的關注更多在于浮世繪里的世俗人情。前期通過中日兩國的繪畫內容與風格的對比,批判了當時中國國內盛行的士大夫思想。后期受國內形勢的影響,周作人將眼光放在了既有中國古典文化的神韻又有獨特新穎的日本文化上去,在藝術中尋找自己的感情寄托。浮世繪等日本藝術文化里包含的民俗文化讓周作人十分感興趣,同時為周作人的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參考文獻
[1]趙京華.尋找精神家園周作人的文化思想與審美追求.[J]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9.
[2]周作人.周作人文類編.日本管窺[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3]錢理群.周作人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1.
[4]周作人.苦竹雜記[C].石家莊: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周作人.日本與中國[A]談虎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2003.
[6]徐從輝.“東洋人的悲哀”:周作人與浮世繪[J].文學評論,2012
[7]劉婉明.從“竹內周作人”到“竹內魯迅”——周作人與北京留學時代的竹內好[J].文藝理論研究,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