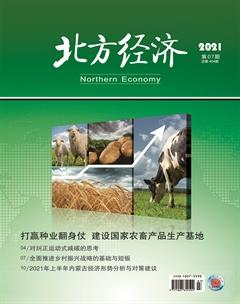對糾正運動式減碳的思考
文風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要求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盡快出臺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后破,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
當前,運動式“減碳”有兩種突出表現:一種是在資本市場上造概念、搶風口、蹭熱度、追熱點;另一種是在施政導向上不講科學、寧左勿右、層層加碼,超出目前的發展階段而采取不切實際的行動。任由運動式“減碳”現象發展下去,就會打亂中央統一部署,對我國碳達峰、碳中和進程產生負面影響。
所以,中央特別強調“先立后破”,就是要先把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配套政策確立起來,把減碳的基礎設施和運行機制建立起來,比如新型電網、新能源系統、新電價機制、碳排放權交易等,在保證經濟平穩運行的基礎上,才能開始去煤減碳。現階段保障能源安全、電力充足穩定供應依然重要。
因此,制定全局的、長遠的行動方案尤為關鍵。現在,黨中央國務院已經成立了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正在制定碳達峰、碳中和時間表、路線圖、1+N政策體系,將陸續發布指導意見。這是頂層設計,涉及到碳達峰、碳中和全國和各個地方、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政策措施。其中,“1+N政策”將很快發布,將從十個領域加速轉型創新。
運動式“減碳”反映出來的一些傾向,從頂層設計也就是“立”的層面,要統籌好以下關系。
“雙碳”與“雙循環”的關系
目前,我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節點上,一方面面臨履行減碳的國際責任,另一方面面臨大國競爭日趨白熱化的壓力,能否利用20年的時間打破美國對我國的圍堵,保障雙循環特別是國內大循環和供應鏈的暢通,實現在綜合經濟實力和話語體系上對美國的趕超至關重要,推進“雙碳行動”需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不易不顧現實、層層加碼,單一追求提前實現,2030、2060年是比較客觀的實現節點。目前,從生產端看,我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28噸/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比美國低;從消費端看,我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英法美都低;從人均累計排放看,1900年至今全球平均水平是209噸/人,我國才157噸/人,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國高達1218噸/人。這就是說,我國發展還需要相應的過程積累,應該考慮保留一定的空間。
“碳達峰”與“碳中和”的關系
碳達峰和碳中和是相互關聯的兩個階段,它們的辯證關系是“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緩彼難”。這就需要在頂層設計中根據各地實際客觀設計碳達峰的峰值和時間,有的地區能夠提前,有的地區能夠按時,有的地區可能需要推后;有的地區能夠低階位達峰,有的地區能夠中階位達峰,有的地區可能需要高階位達峰。
全國一盤棋與區域分工的關系
我們國家承諾,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一個整體性目標。具體到生產力空間布局、區域產業分工和產業鏈、供應鏈的層面有必要體現差異化的安排。內蒙古作為國家能源和戰略資源基地,擔負著保障全國能源和戰略資源供應安全的重要責任,能源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不可或缺。同樣,在核算和分配碳指標時,也需要統籌能源輸出地區和能源消納地區的關系,做出相應的安排。
減碳措施與技術進步的關系
造成運動式減碳的一個原因,就是左傾思想,沒有把減碳行動與技術進步同步,導致愿望與措施背離。因此,在頂層設計的過程中一定要把技術路線圖設計好,依次設計好施工路線圖,把政策支持的重點放在科技創新上面,使施工的步伐與技術進步的步伐保持在同步的水平上就是最快的,如果施工的步伐超過技術進步的步伐,會導致失敗。
能耗雙控與減碳指標的關系
能耗指標與碳排放量肯定不是一回事。但是大家普遍有種意識,就是一個地區、一個企業綜合能耗是多少噸標煤,按一個公式轉成碳就行了。這是一個誤區,能耗高不一定碳排放就一定高。比如,在同一個地點的兩個產量一樣但原料不同的水泥廠,傳統水泥廠能耗水平比電石渣水泥廠略低,但碳排放量高出1倍多。因為傳統廠原料分解產生了大量二氧化碳,而后者沒有。再比如,鐵合金廠是標準的高能耗企業,但它用水電站作自備電站,不用網電,碳排放就趨于零。可見,推進“雙碳行動”就要統籌能耗和碳排放指標的關系,把消納零碳能源與消納高碳能源區分開來,對消納零碳能源的企業和地區給予鼓勵。
生態保護與綠色發展的關系
大家的共識是,保護生態有利于增加植物和土壤的固碳能力。但僅如此還不夠,還應在保護的前提下更好開發利用生態系統的綜合價值,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內蒙古廣大的草原也是高質量的風場,建設國家低碳能源基地,發展風電、光伏發電等零碳能源大有可為,綜合利用草原上的風光資源是推進“雙碳行動”的重要抓手。如果在草原上不能上風電項目,在森林、農田就更不能上,沙漠又不適合上。我們國家的風力發電在哪里安身呢?這就需要認真研究一個較優方案,以保障我們國家高碳能源結構向低碳能源結構轉型。
多能互補與能源替代的關系
現在講碳中和,首先要考慮能源替代,就是用電、熱、氫能等替代煤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替代難度不同,需要按難易進行排出次序,依次推進。在民生領域,相對容易用電力、地熱、太陽能來替代;在交通領域,已經在推廣電動汽車,以后可能用氫能驅動船和飛機等;在農業領域,大部分也可以用電替代;在工業領域,冶金、化工、建材、礦山全部替代比較難,需要較長時期一步步推進。當前,提高新能源占比要克服電網穩定性問題需要一步步來。另外,如何發展氫能,也要破解技術門檻。
能源生產與能源消費的關系
我國大約10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中,發電端占比約47%,消費端占比53%,實現碳中和就需要在發電端用更多的非碳能源發電,在消費端用電和氫能等來替代,構建一個兩端共同發力的系統。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關鍵是不能“盲目”。我國是一個超大經濟體,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還沒結束,經濟社會發展還做不到與能源需求脫鉤,還離不開能源和原材料產業。重要的是要增強各產業之間發展的協調性,要推進能源原材料產業綠色高質量轉型。若非如此,將直接影響“雙碳”目標實現,直接影響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直接影響大氣環境質量改善。同時,也要防止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明顯上漲、經濟運行和居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政策引導與市場導向的關系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需要在能源結構、能源消費、人為固碳“三端發力”,所需資金之多,不可能靠財政補貼得以滿足,必須堅持市場導向原則,引導良性競爭,一步一步推進。財政資金應主要投入在技術研發、產業示范上,力爭加快我國技術和產業的迭代進步速度。就節能降碳現狀而言,我國政府約束大于市場機制,未來可能需要更多依靠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引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還需要政策目標的一致性、政策內容的科學性、政策之間的銜接性、政策力度的可及性、政策調控的有效性。許多政策部門,相互打架、缺乏協調,致使企業無所適從,市場機制難以發揮作用。中央提出讓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需要各部門、各地區在具體政策中加以更好體現。
體制改革與雙碳行動的關系
目前,制約“雙碳行動”不僅有技術因素、市場因素、政策因素,還有體制因素。特別是電力體制還需要進一步理順,使之有利于構建接納新能源上網的智能化新型電網,有利于推開構建削峰填谷的電價現貨交易機制,有利于形成高比例消納新能源的激勵機制,有利于推進多能互補、源網核儲一體化發展,等等。這些都是推進“雙碳行動”的基礎性工作,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作者系內蒙古北宸智庫首席專家)
責任編輯:張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