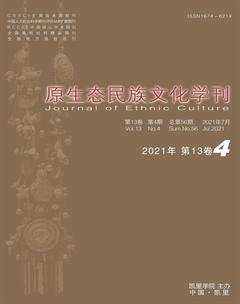來與往:共餐制與水族社會關系建構研究
余珍
摘 要:通過一個水族村寨共餐制的個案研究,探討社會網絡關系建構的秩序和內在動力。在當地,共餐制體現在陰食共享和陽食共享兩個方面,二者分別推動了人與鬼神的神性關系建構、人與人的俗性關系建構。通過陰食的共享,人與鬼神之間的責任和義務關系被確認和強化;通過陽食的共享,人們在來與往中鞏固了互惠的社會義務和共同的社會責任,并生產出新的社會關系網絡。神性和俗性的融合,使村寨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社會。
關鍵詞:水族共餐制;陰食共享;陽食共享;社會關系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1)04 - 0109 - 08
一、問題的提出
2016年7月至今,筆者持續對貴州省黔南州荔波縣玉屏街道辦的水利大寨做了長時段的田野調查。調查發現,“喊人吃飯”是當地社會生活的常態。進入他們的社會并取得他們信任的最佳方式是接受邀請,和他們一起愉快地用餐。拒絕用餐意味著拒絕人情往來,也意味著關系的疏離。當地有著豐富的鬼神體系。紛繁多樣的驅鬼儀式和日常祭祀共同促成了人與鬼神之間的飲食共享,成為引發人與鬼神交流的圣事部分。因此,在當地,共餐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與人之間的共餐;二是人與鬼神之間的共餐。這里,將之分別定義為陽食共享和陰食共享,二者共同構成了水利大寨的共餐制度,成為建構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
經典人類學理論從互惠的視角對社會的討論諸多。馬林諾夫斯基通過對“庫拉圈”的研究,探究出美拉尼西亞社會的互惠交換構成了社會的秩序基礎[1]。莫斯通過獻祭的研究,指出其性質與功能體現在獻祭中呈現的神圣與世俗的關系,是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映照[2]。《論饋贈》[3]是他探討社會關系互惠交換的又一經典[4]。根據莫斯的研究,交換中人和物背后的巫術般力量是社會運轉的生命力所在[5]。在中國的人類學研究中,閻云翔通過下呷村社會地位低的人向社會地位高的人送禮探討了反向的禮物流動,指出禮物的不對稱交換暗含了超越社會關系的權力因素[6]。有關人類學共餐制的互惠研究中,羅伯森·史密斯將閃米特人宗教儀式中的獻祭與“共食伙伴”聯系在一起,描述人與神之間的關系。在獻祭中,被殺死的動物被看作人與人、氏族與氏族神之間的團結機制,他們通過分享動物的肉而重新團結起來,獻祭成為對關系的更新[7]。神與人分享食物被視為一種對伙伴關系和共同的社會責任的象征和確認。同樣,食物的分享可以創造人與人的紐帶,將人們團結起來[8]。西敏司在他的研究中同樣關注共餐關系,他認為那些沒有坐在一起分享食物的人,既沒有宗教上的伙伴關系,也沒有社會義務的互惠關系[9]。
綜上,飲食不僅是滿足個體生理需求的手段,也是重要的社交媒介和通神手段,是理解當地社會關系網絡的文化現象。基于此,本文從共餐制的研究視角出發,分別從陰食共享的獻祭和建構社會關系的陽食共享討論共餐背后的神性和俗性何以構成了社會的整體性,以期理解當地社會秩序的生成基礎和社會關系建構的文化動力。
二、陰食共享與神性關系建構
水族是一個多神信仰的民族,有著豐富的鬼神體系,認為人的一切吉兇禍福均委身于鬼神。水族將鬼分為惡鬼、中性鬼和好鬼。惡鬼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需驅逐和規避的鬼。中性鬼介于兩者之間,因人們對之的態度而左右搖擺。當人們對之忽視時,中性鬼很有可能展現出惡鬼的一面,對人的身體和牲畜造成傷害。人們對之適時供奉和重視,中性鬼則不會帶來傷害。好鬼即神、祖先。神的種類較多,且有著較為明確的分工,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和意義。事實上,神與神之間的界限并非完全清晰,很多時候,不同的神肩負著共同的責任,承擔著相似的角色。當地對神的供養主要體現在日常生活和節日儀式之中。與之相對,水利大寨的惡鬼也多,解鬼儀式頻繁。當地人認為,冬季鬼無食可吃,作祟頻繁,是解鬼的最好時機,當地人稱之為“用好事”。根據鬼的不同,解鬼的場所也不同,有些鬼可在家中解,有些則必須要到屋外,甚至到野外。無論在哪里解,隨之均有犧牲以獻祭。敬神或者解鬼,與之相伴的重要一環便是人與鬼神要共享陰食。這里,筆者將從日常祭祀和解鬼儀式的三個事件呈現陰食共享與神圣世界的建構過程。
(一)禳災儀式:亂叫的雞
規則不僅僅對人行之有效,對動物,同樣如此。違背規則意味著要被修正并接受懲罰。村民吳玉春家的一只公雞總是在晚上七八點的時候打鳴。公雞叫錯時辰被視為厄運即將到來的征兆。避免厄運需求助鬼師或者水書先生“用好事”來“改掉”。1“改”的儀式分為兩步。首先,鬼師借助一定的儀式物品在主人家念經驅鬼。這之后主人把門鎖上,防止鬼再進入;接著,尋找有水源的野外去“改”,把違背時間秩序的公雞殺掉,供奉給“鬼”。目的是為了將鬼引誘至此徹底驅趕。1到野外解鬼,主人不能出現,以防再次被鬼盯上,難以將之徹底驅趕。協助野外解鬼的人是同家族的兩個男人,主要負責殺雞、找柴、升火、煮雞。儀式最后,要送鬼離開,送鬼之前眾人需陪同鬼吃祭品,目的是為了將之徹底驅趕。在野外解鬼,祭品不能帶回家,否則會招來鬼的再次索要,導致惡鬼纏身。儀式結束后,其他幾個男性村民應邀趕來共享祭品,直到祭品被吃光,儀式才算真正的結束。
儀式的目的是以犧牲獻祭換取和平。儀式中存在兩層關系:神職人員起到溝通鬼與現實世界的橋梁作用;前來幫忙與共食之人是現實生活關系的反應。與鬼共享陰食是驅趕鬼的重要一環,陰食與家的對立造就了前來共餐的人所負載的義務。通過解鬼儀式后的共餐,既避免了人與鬼神世界的沖突,又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在這場儀式中,主人并沒有缺場,他的存在暗含在兩層關系中:一是借助鬼師之手,主人對鬼的躲避和驅逐目的已然達成;二是主人與幫忙者和共享陰食者的關系在此場儀式中被強化,意味著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主人對這些人有還禮的義務。這種幫忙與還禮的互惠關系即為社會有序運行的動力所在。
(二)補償儀式:闖禍的狗
當地清明節要殺洋鴨祭祀祖先。清明前夕,村民吳迅家的洋鴨被鄰居家的兩只狗咬死了十幾只。損失折合成市價為1 500元左右,出于家族兄弟的考慮,僅讓鄰居補償700元。此前,鄰居去過陰,過陰婆讓回家找日子“做保財”,2鄰居因事耽誤沒來得及做,夫妻二人認定這次損失與此相關。幾天后,那兩只“闖禍”的狗成了“做保財”的“祭品”。
祭品要與眾人分享,來的人越多、吃的越干凈對主人家越好。做過保財后,夫妻倆到處喊人到家吃飯。受邀者攜帶大米作為禮物,進屋后放在堂屋的一角。接著,各自拿碗盛飯,找位置坐下。吃“保財飯”需盡量少說話,即使說也要說吉利話。對食物不能直呼其名,要用其他與“財”有關的詞代替。如鹽是銀子,肉是金子。飯飽后眾人要靜悄悄地離開,即使要和主人道別也不可說“飽”“撐”等字,而是要說“滿倉了”或者“荷包裝滿了,我去找錢來”等吉利話。出門后,人們用主人事先準備好的清水洗手洗嘴后方可離開,意為不帶走主人家的財運。出了主人家門,人們才可大聲說話。
表面來看,這場儀式過后的食物是與人共享的。靜悄悄、吉利話的規束賦予了共餐的神圣性,進餐者的行為也被“神圣化”。應邀而來的眾人擔負著陪同“保財神”吃完祭品的義務,它是關乎儀式成敗的重要一環,沒有人會忽視。因此,人與“保財神”之間的陰食共享,既預示著一切厄運的終結,事物的向前發展,也是眾人對主人家忠誠的證明。這種忠誠在于,一旦主人需要幫忙,他們便會到場且極力配合。這一規定存在且持續有效的前提在于人們總會期待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會得到主人家同樣的回應與配合。在這場儀式里,鬼師不需向主人表達忠誠,他需要忠于的是天上的神,這種忠誠建立在嚴格遵守不食狗肉的約束與禁忌上。他認為,因天上有犬,犬便是神,若要神助己,便不能食之。否則,在某個關鍵時刻可能得不到神的援助,這對鬼師是致命的,不可違背。
(三)祈福儀式:祭祀和敬神
祭祀和敬神是在每個家庭中不斷重復的行為。飲酒前用筷子沾杯中酒在桌子上點兩下是酒前祭祖;進餐前在娘娘座前擺上一碗米飯是飯前敬神。1一年中,春節祭祀最為隆重。講究的人家要從除夕夜一直敬到大年初二。現在儀式已簡化,多敬到大年初一便可。祭祀分屋內祭祖和屋外祭鬼。村民認為,非正常死亡的人會變成“鬼”。這類鬼多被歸類為中性鬼,對之適時供奉,鬼便不會生事。但是這類鬼不能進家,否則會招徠家庭的不幸。在門口擺放祭品,目的是將鬼攔在門外。因之,供奉鬼的真正動機是為了對之隔離,避免破壞現有秩序。屋內供奉的是祖先和娘娘。祖先供奉在堂屋的正中間,通常這里需要擺放祖先的牌位。娘娘座的供奉位置不同家庭間略有差異,但均位于廚房的一角。兩處供奉物品基本相似,多為雞、豬肉、水果、糯米飯等。無論是屋內祭祖還是屋外祭鬼,生者與死者皆要與之共享陰食。無論是節日祭祀還是日常祭祀,死者先食,生者后食的倫理秩序神圣不可違背。
此外,村民在春節期間要供奉與自己財運、生命相關的物品。有車的村民要“供車”,供品與供祖大致相同。至于供的是什么神說法不一,村民堅信只要認真供奉便能換取來年的平安出行。村民中也有供摩托車的,一開始只有兩三戶供奉,儀式物品也十分簡單,燒幾張紙,點一炷香即可。慢慢地供奉摩托的人多了起來,供品也逐年豐富。
對祖先的祭祀和對汽車、摩托車的供奉,其本質相同。通過儀式,人們將祭品作為禮物送給了神。此時,作為祭品的物品已不再屬于人,而是屬于神。在人神共享祭品時,二者成為“共食伙伴”,此時的食物是神分享給人的,共享食物意味著各自的責任被再度確認。通過共享食物,人與神之間的紐帶被創造,社會秩序得以保障。神依靠人的祭祀獲取能量,人們堅信,若得不到特有的營養品,神便不會為人類的利益而繼續效勞[10]。在這里,神依賴人,人也依賴神。
三、陽食共享與俗性關系建構
在水利大寨,“家族”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按照父系血緣關系延伸出來的三家六房。在民國時期,賦稅嚴重,大部分的村民逃離村寨,遷移到別處。直到新中國成立,一些村民又回到大寨。也有一些逃離他處的人在土改時分到土地,留在他鄉,沒有遷回。因此,水利大寨村民所認可的三家六房包含寨子內和寨子外的兩部分人。第二層含義為家族,等同于村寨。它包括村寨內四個不同的“三家六房”。第三層含義為家門。據族譜記載,吳姓祖先有四個兒子分別在荔波縣的水利大寨、三都縣的恒豐、廷牌和九阡2安家并各自繁育了后代。因為共同的血緣關系,家門內部不能通婚。需要幫忙,尤其是血親復仇時,便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在水利大寨,婚喪嫁娶辦酒,家族兄弟有幫忙的義務。共餐成為維系遠近兼顧的親屬網絡的重要途徑。這里將分別從個體之間、家族內部、村寨內部和跨越村寨的共餐進行分析,探求陽食共享與俗性世界的建構過程。
(一)個體之間的共餐
“吃”在水利大寨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白天人們忙于農事和生計,用餐的時間通常無法固定。到了晚上,人們才能抽身于繁忙的農事和瑣事而參加聚餐和接受邀請。這種共餐體驗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的共餐是“打平伙”,即“AA制”。“打平伙”是建構關系網絡的重要手段,也是社會生產生活協作關系的一種體現。“打平伙”遵循“平均主義”的原則,一般每人平攤20元,用餐地點可以在家中,也可選在野外。“打平伙”大致有三種形式:一是為接待共同的客人;二是出于分享野味或組織野外燒烤;三是以“打平伙”方式進行家族聚會。第二種形式是請客吃飯,當地的說法是“喊人吃飯”。“有人陪喝酒,人多吃飯香”是“喊人吃飯”最直接的表述。因此,“喊人吃飯”成為村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拒絕別人的共餐邀請,被視為“太小心”“太客氣”。這樣的“小心”和“客氣”會導致關系的逐漸疏遠。相反,“一喊就到”的人在村寨最受歡迎,接受邀請意味著“看得起人”“不嫌棄人”。因此,接受邀請是搭建社會關系網絡的重要途徑。
無論是“喊人吃飯”,還是“打平伙”,共餐期間村民的話題多圍繞日常生活瑣事展開。吃了什么、說了什么并不重要。因分享食物聚在一起的交談和陪伴才是共餐的意義所在。同時,回請式的酬謝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一環。接受一次晚餐的邀請,既是關系的確認也是關系的強化。通常意味著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客人有回請主人的義務。此外,農忙時的幫工、換工圈總是與共餐圈重合。作為共同的利益群體,共餐也表明了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你會心甘情愿地為這個圈子里的人效力[11]。違背這條規則會讓自己的名聲受損,變得不受歡迎,受到排斥,甚至在關鍵時刻得不到援助。
(二)家族內部的共餐
共餐有共同擁有、共同分享和共同享受的含義。在家族內部,不同家庭之間的聯系既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協作中,也體現在節日狂歡與對人生禮儀的參與。家族內部的共餐在節日期間最為頻繁。以春節和清明節為例,當地春節有“不干活,吃和玩”的傳統。大年初一早上,村民們便開始忙著挨家挨戶去“喊人吃飯”和應邀去別人家吃飯。與日常共餐不同的是,接受邀請與回請需在當天完成,且要遵從一定的秩序。通常,需先邀請和回請本家族的人,其次才輪到其他家族的人。“家家吃,家家請”是過年的常態。吃什么、吃了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要讓自己處于“轉”的狀態,確保每家每戶都能到,做到不偏不倚。
清明也是家族內部共餐的重要節點。過去,清明節多是三家六房一同掛青,現在逐漸出現了以家戶為單位的掛青。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有些人在外打短工,清明節當天無法趕回,無法與其他家庭的時間達成一致;二是家族過大,且血緣關系多出了三家,僅屬于六房的范疇。無論如何,晚上的共餐是清明節當天最重要的家族儀式。節日共餐人數的多寡與家族的子嗣是否興旺有直接的關系。因此,節日期間的家族共餐對內有強化認同和確認身份的作用,對外具有象征意義的區分與攀比。
家族內部的共餐還體現在重要的人生禮儀上。在水利大寨,因命數不同,有些孩子需要在特定的時間“認保爹”。“認保爹”的儀式叫“踩水碗”。這天,主人準備一碗清水、一雙筷子和一根紅線放在主管子嗣的娘娘座前。第一個不請自來且與孩子父母輩分相同的人便與這個孩子結緣,要把這個孩子認下。保爹將紅線綁在孩子的手上,儀式就算完成,兩家自此成為干親。接著便是殺雞、煮菜,請家族里的人來吃飯。通過共餐,保爹與孩子的關系正式確立,也意味著兩個家族的聯盟關系正式結成。保爹與這個家庭乃至這個家族建立了聯系,成為這個家族的成員。孩子也因此與保爹所在的家族建立了新的關系。因此,除血緣、姻緣外,“認保爹”成為第三種社會(擬親屬)關系再生產的一個重要機制,確保了社會可以在持續的更新中不斷地有序運轉。久而久之,即使出了三家六房的血緣關系,人們也總能因姻緣或者干親使關系變得再度緊密。村寨也因此而不斷地被建構成“整個寨子都是親戚”的特殊社會。
(三)村寨內部的共餐
超越三家六房的村寨共餐,多伴隨婚喪嫁娶的人生禮儀和關乎村寨整體利益的公共性事件而發生。在婚喪嫁娶的人生禮儀中,單個三家六房的力量不足以支撐一場儀式的完成,需要整個大家族通力協作。這種幫忙是義務性的,是互相的。幫忙的人在未來的某一天總能夠得到回報。破壞規則,后果是危險的,不去幫忙意味著別人不來幫你的忙,沒有人挑戰。幫忙后的共餐是儀式中的重要一環。
村寨內的共餐有時并不是出于酬謝,而在于關系修復,它通常伴隨著特殊事件而發生。寨子里一位婦女做了越軌的事,他的兒子得知后把對方打成重傷。對方家族伺機報復,村寨的男性村民聞訊后趕去幫忙,此事才算結束。事后,這家人為答謝村寨兄弟的幫忙,在村寨廣場殺豬酬謝。在當地,此類事件發生后,即便沖突已經解決,村寨的名聲也會因此招損,事主需殺牲畜“洗寨”以驅走可能為村寨帶來的厄運。同時,殺豬共餐表面看是酬謝,更深層次的含義在于賠罪以修補破裂的社會關系,回歸正常的生活秩序。越軌的行為違背了家族的行為規范,自然要受到懲罰。而共餐則起到調停的作用,通過共餐事主與村寨重新建立聯系,以確認他們與村寨依然存在一定的社會義務和親密的伙伴關系。村民進餐,共餐的達成,象征著敵意的冰釋,盡管有時這種冰釋是表面的,但它終歸能預示事件的結束。
(四)超越村寨的共餐
在水利大寨,姻親關系的形成和維系機制與節日密切相關。卯節和端節是水族最為重要的兩個節日。卯節在插秧之后的農歷五月,端節在稻谷成熟后的農歷九月。卯節和端節在時間安排上采取了按地域分期分批次的方式,且有“過卯不過端,過端不過卯”的習俗[12]159。差序的節日安排是走親訪友的重要時機,是一種集體性的行為[12]161。卯節分四個批次。水歌唱到:“第一卯是水利,第二卯是洞托,第三卯是水浦,第四卯是九阡。”目前,第一卯仍在水利過,洞托和水浦已不再單獨過卯,而是與第四批的九阡安排在了同一天。
有關水利過卯的傳說不一,當地人比較認可的說法是“因斗氣而過卯”。水利村原來有一塊“艾石”,供奉的是“艾神”。“艾神”負責保佑禾苗的豐產與村寨的興旺。水利村一個姑娘嫁到了水豐村,女婿便把這里的艾石偷走,艾節也隨之被偷到了水豐村。關于過卯的原因,村民普遍認為:“祖先生氣就開始吃卯給他們看,我們過第一卯正值插秧和青黃不接的時節,都說‘五六月人怕客,馬怕蚊,我們也硬著頭皮過。”
卯節當天的客人既有提前邀請的,也有臨時到訪的。客人主要有四類:一類是外家,包括妻子的家里人、母親的家里人及外甥。第二類是外家的本家及親戚。第三類是到本村寨其他家庭的客人。第四類是家人的朋友、同學、同事等[12]174。當天到訪的,可能有一些主人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過卯當天,主人要因此準備足夠多的食物,否則“對不起人”。同樣,客人的多寡與個人的聲望密切相關。那些“有能力”“有本事”“家族大”的人客人較多,過節當天甚是熱鬧。村民吳國利是當地著名的歌手,熟懂歷史,近年來與政府和文藝工作者接觸較多,交友甚廣。他的兒子們同學和朋友也多,每年來吃卯的客人自然多。2015年卯節招待了16桌(160人左右)客人,2016年卯節招待了17桌(170人左右)客人,2017年招待了16桌(160人左右)客人,2019年招待了18桌(180人左右)。鬼師吳志才有三個兒子,均已結婚,三個兒媳的外家加上妻子的外家及親屬,卯節來客較多。又因大兒子是村小的教導主任,朋友、同事到訪的也多。關于過卯,他的兒媳這樣表述:
我來這里十年了,從來沒趕卯過,連村口什么樣我都不知道。一直在洗菜、洗碗,每年都是十幾桌。那天哪家都忙,家家有客人。卯坡當天是什么樣我就不知道,看到別人手機拍的,我才知道,哇,原來村口這么熱鬧……過卯只過一天,第二天就沒有了,所有的客人都趕到這一天了。我姐姐也在大寨,我娘家的人還去我姐姐那里,要不然那天更忙。過卯那天,一早上人就來了,忙的也吃不下去了,客人來了要陪著喝酒,空肚子很容易醉酒。那天,全家醉酒,第二天全家大大小小只有睡覺,起不來了。
20世紀90年代以前,卯節為締結婚姻提供了重要的場所。它是青年人擺脫封建社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契機。這天,未婚男女可以自由選擇交往對象。有姑娘來寨子里吃卯,小伙子們就找上她們對歌。歌詞既有流傳下來的,也有現編的。通宵對歌成為節日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通婚的一個重要途徑。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外出打工人數不斷增多,節日中對歌不斷弱化,因對歌通婚的情況也逐漸減少。
同一個區域的差序節日安排發揮了社會整合的功能。輪流過節的來來往往使不同村寨、不同家庭的雙向流動得以實現,強化了原有的社會關系。不拘泥于親屬之間的走親訪友和共餐制也生產出了新的社會關系。從這個層面來講,輪流共餐不僅僅是出于互惠和酬謝,更是生存和繁衍的一種機制,蘊含著當地精致的文化安排和豐厚的觀念意義系統。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陰食與陽食的共享,本文探討了當地社會網絡關系建構的秩序和動力。陰食共享溝通了現世的人與未知的鬼神世界。在陰食共享中,被吃掉的祭品變得神圣,祭品不但被人類,也被某些看不見的祖先、鬼神和超自然的力量分享了。面對現世的挫折,人們求助于鬼神,或討好躲避或順從供祭,以求祈福禳災,確保生活的太平和家庭的興旺。獻祭與犧牲在此時便顯得尤為必要。鬼神依賴人獲取能量,伴隨著動物的犧牲和陰食的共享,人與鬼神成為“共食伙伴”,二者之間的紐帶被創造,社會責任被確認和強化。這種責任意味著某種不幸的終結,也預示著事物的向前發展。同時,共享陰食的體驗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這些坐下來共享陰食的人,宗教上的伙伴關系和社會義務上的互惠關系被重新建立或者再度強化。這暗含著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人們需要協助時,總會得到同樣的報答。
陽食共享使個體之間的協作、家族內部的認同、家族聯盟的形成、超越村寨的社會關系持續更新成為可能。加入一個圈子的最佳途徑就是接受共餐的邀請,與之成為伙伴關系,并愿意為這個圈子的群體利益做出努力。要想維系這種關系,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主客之間的身份必須得到轉換,這意味著作為客人要時刻準備著對主人回請式的酬答。同樣,家族內部的聲望與共餐的規模成正相關,家族共餐是認同與區分的過程。非本家族的人被排斥在共餐圈之外,強化了家族內部的自我認同。只是,家族并不是封閉的、區隔的,他們總是會尋求機會以壯大家族的影響力。這時,超越家族的共餐機制被創造出來,家族聯盟便產生了。共餐是見證家族聯盟形成的重要途徑。通過共餐,不同家族之間的聯系被正式確立,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共餐,這一聯盟關系被不斷地強化。在熟人社會,越軌行為的直接后果是社會關系的破裂。被孤立的后果是危險的,意味著在關鍵時刻得不到援助。通過共餐,預示著事件的結束,社會關系的修補,和正常生活秩序的回歸。差序的節日安排,輪流過節的來與往,使超越村寨的共餐成為可能。此時的共餐不僅僅是出于酬答、互惠而為之,更是一種重要的生存機制和繁衍機制,維持和強化了原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并再生產了社會關系,使社會關系網絡得以持續更新。
共餐制背后的倫理觀念是建構社會關系與社會秩序的基礎和文化動力所在。陰食和陽食共享推動了人與鬼神、人與人之間的來與往。在這里,神性和俗性得以融合,共同建構了有機的整體社會。
參考文獻:
[1]? 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張云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2]? 龍飛俊.讀莫斯《獻祭的性質與功能》[J].西北民族研究,2011(5):185 - 190.
[3]? 馬賽爾·莫斯.論饋贈: 傳統社會的交換形式及其功能[M].盧匯,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
[4]? 王銘銘.莫斯民族學的“社會論”[J].西北民族研究,2013(3):117 - 122.
[5]? 益西曲珍.人、物與社會——讀莫斯的《禮物》與《獻祭的性質與功能》[J].西北民族研究,2012(1):158 - 166.
[6]? 閻云翔.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M].李放春,劉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 張亞輝.駱駝與晨星——讀《閃米特人的宗教》[J].西北民族研究,2011(8):145 - 148.
[8]? Robertson Smith.The Religion of the Smeites[M].New - York:Meridian Library,1956.
[9]? 西敏司.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M].朱健剛,王超,譯.上海:商務印書館,2010:16.
[10]桑迪.神圣的饑餓:作為文化系統的食人俗[M].鄭元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35.
[11]瑪格麗特.維薩.食行為學:文明舉止的起源、發展與含義[M].劉曉媛,譯.北京:電子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76.
[12]王學文.規束與共享:一個水族村寨的生活文化考察[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責任編輯:劉興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