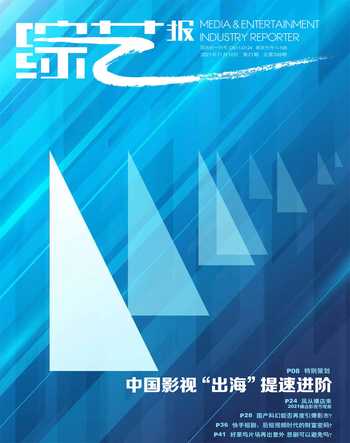《烏海》:沒有光,只剩下黑暗
偉青

電影《烏海》曾獲第三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jié)“金椰獎”單元推薦影片,入圍第68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獲得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等國內(nèi)外獎項。但影片上映7天,累計票房剛剛破千萬元,排片占比已不足5%。
觀看《烏海》并非一次輕松的體驗,壓迫感揮之不去。這是周子陽繼《老獸》之后自編自導(dǎo)的第二部作品,講述原本相愛的年輕夫妻楊華和苗唯,在生活的重壓和誤會中,一步步關(guān)系破碎,直至慘烈收場。
從這部現(xiàn)實題材作品中,我們能看到周子陽為豐富影片主旨所做的努力。例如,影片討論了交流困境下親密關(guān)系的崩塌,加入了對高利貸亂象的曝光,對原生家庭和貧富差距等現(xiàn)實問題的反思等。
與此同時,《烏海》也保留了《老獸》中的超現(xiàn)實表現(xiàn)手法,倒立的牧羊人、荒瘠沙漠上充滿后現(xiàn)代感的白色帳篷群、鄉(xiāng)村老人組成的樂隊與瑜伽隊,以及廢棄的恐龍樂園……這讓影片在荒誕感之外,還添了一絲冷峻的幽默氣息。尤其是那群暗夜中的恐龍雕像,在燈光的晃照之下,好似一群在現(xiàn)代都市中狼奔豕突的怪獸。楊華鉆進恐龍的肚子,看起來好像被恐龍吞掉一般,隱喻著人性被物欲吞噬。這場寓言意味極濃的視覺呈現(xiàn),帶給觀眾強烈的心理沖擊。
飾演楊華的黃軒無疑是專業(yè)且投入的,幾場單人戲份完成度很高,例如車內(nèi)隱忍的眼淚和自打耳光,在觀景臺上對昔日情濃的緬懷,放火燒帳篷后癲狂的大笑,以及撞落妻子后的痛哭迷茫等場景,都層次分明地表達出人物的困頓與掙扎,悲情與幻滅。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些表演在整部電影中卻顯得失衡,好像一場個人秀。
這源于其他角色的蒼白。在整部電影中,與黃軒演對手戲的楊子姍似乎一直處于游離狀態(tài),仿佛完全是為了配合前者的表演而存在,就連被主創(chuàng)津津樂道的夫妻吵架段落,也充滿了被安排的刻意與失真,讓人難以感受到演員間情緒和能量的碰撞。
其他配角也皆盡工具化,老丈人、丈母娘只剩下勢利的嘴臉,借高利貸的女大學(xué)生就一定是個愛慕虛榮者,苗唯在同學(xué)會上遇到的老同學(xué)偏偏就是十多年癡心不改……這一縷縷隱隱泛濫的狗血氣息,讓觀眾在影院如坐針氈。
然而,即便是分量極重的男主角,又帶給觀眾怎樣的體驗?zāi)兀亢萌R塢有一個著名的“救貓咪”理論,大意是要給主人公找到閃光點,讓觀眾與之產(chǎn)生某種情感聯(lián)結(jié),哪怕主人公是個反派。所以,觀眾同情與蝙蝠俠處處為敵的小丑,是因為他有不為人知的傷痛的過往;同情《低俗小說》中的無腦殺手,是因為他們身上懷有一份天真……“救貓咪”在《老獸》中也是成立的,男主角“老楊”在生活的一地雞毛之外,還有在洗浴中心的墻壁中救下的飛鳥和夢中的白馬,象征著他所憧憬的自由靈魂,更別說,他還有對老友的一腔熱忱。這些都讓這個人物在觀眾心中站住了腳,從而得到原諒和救贖。而《烏海》中,楊華被觀眾看到的,只有點燃在“沙漠月亮”帳篷上的烈火和在暗夜里吞噬他的史前怪獸,這個人物輕信、沖動、易怒、多疑、失智且瘋狂,當他將深愛的、懷著他骨肉的妻子撞下山崖時,觀眾還能去同情他什么呢?
這也是影片最致命的地方——一種令人窒息而絕望的基調(diào),沒有光透進來。這不免叫人想起李安那句流傳甚廣的關(guān)于電影的描述——“電影不是把大家?guī)У胶诎道铮前汛蠹規(guī)н^黑暗,在黑暗里檢驗一遍,再回到陽光底下,你會明白該如何面對生活。”《烏海》卻將大家?guī)У胶诎抵胁⒘粼诹四抢铮抢餂]有陽光,你仍然不明白該如何面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