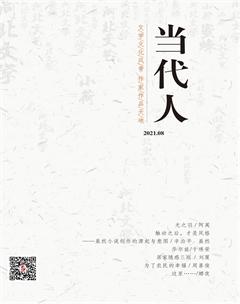開卷
2021-08-28 02:05:53
當代人 2021年8期
關鍵詞:小說
《光之羽》定稿前的名字是《光之翼》。翼,有實然的重量感,要它翩然長空,需要自控和他控的力來加持;羽,則是輕盈的,細柔的,有自恰的詩性上升。我們認為“羽”字更接近阿英這篇小說的氣息,便與他溝通,最終使用了“羽”。
這是兩句閑話,記錄在編刊手記里,這里拿來劇透一下“編輯部的故事”和編輯人的小心思。“煉題”“煉字”的主導是作者。編輯也需要有好手段,但最好的狀況是“備而不用”。所有的編輯都希望自己看上的稿子,從題目到故事、語言、結構都恰如其分的好,從而得到出版的最佳禮遇——原汁原味出版。
《光之羽》的語言較為可觀,不時蹦跶出一星兒冷金屬色的幽默,尤其善于使用動詞,“在句子縫隙里,置入一些節奏和韻律,讓其變得耐讀一些”。“我”、鄭潔、烏冬、小飯館老板娘,都是依靠動作的描畫而在讀者頭腦中勾連出獨特的面目。人物有面貌,故事便有了扎實的根基。一則原本平常的相親故事,場景、空間幾番輾轉騰挪,已經讓讀者和文本之間發生了扯不開的相互期待。溫暖,向光,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和體貼,令人流連。阿英說,他是一個“追光者”。有“信”之后再有“光”。
“小說坊”欄目,《華爾茲》《小海》《葬禮上的相遇》《種茉莉》幾篇,也都可圈可點。“對話錄”,由辛泊平和雖然談論小說的源起和意圖,是針對個體作家和個體作品的,安頓在《光之羽》與其他小說作品之間,也不期然有了“圓桌”研討的屬性。“碎閱讀”與“深閱讀”,文學期刊如果有一種小小的擺渡者功能,該是好的。我們致力于探索。
此外,本期發布“頌歌獻給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文學征文的獲獎名單。恭喜各位獲獎者,也感謝所有參與者和征文信息的傳布者。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