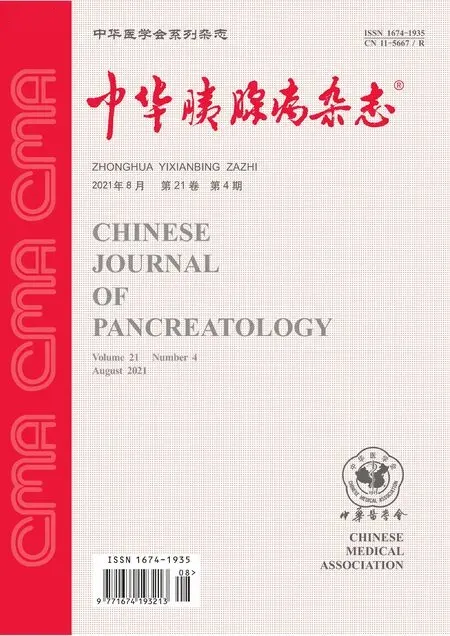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1在胰腺導管腺癌組織中的表達及臨床意義
李歡 李揚 杜娟 郭麗梅
1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病理科,北京 100191;2北京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病理學系,北京 100191
PDAC是全球第七大癌癥相關死亡原因[1],預計到2030年將成為癌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2]。PDAC手術切除率低,對放化療敏感度差,大多數靶向治療的臨床效果不滿意。因此,需要尋找潛在的分子標志物來幫助PDAC的早期診斷和靶向治療。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1(glypican1,GPC1)在前列腺癌[3]、肝癌[4]、食管癌[5]及膠質母細胞瘤[6]等腫瘤組織中異常表達,并與腫瘤的發生發展有關。研究報道GPC1陽性的循環外泌體可以區分PDAC和胰腺良性疾病患者,特異性和敏感性接近100%[7]。本研究檢測PDAC組織GPC1的表達,分析其與臨床病理特征及患者預后的相關性,探討GPC1對PDAC臨床診斷及治療的價值。
材料與方法
一、胰腺組織標本
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間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病理科存檔的125例PDAC組織石蠟標本和對應的癌旁正常胰腺組織標本。納入標準:(1)術前未接受新輔助化療、放療等其他抗腫瘤治療;(2)術中證實無遠處轉移,接受標準的胰腺癌根治術;(3)術后病理資料證實所有切緣為R0或R1切除(R0切除為肉眼和顯微鏡下均未看到腫瘤殘留;R1切除為肉眼未看到腫瘤殘留,但在顯微鏡下能看到腫瘤殘留);(4)患者臨床及隨訪資料完整。本研究經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醫學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并批準通過(IRB00006761-M2021030)。
二、GPC1蛋白表達檢測及分組
標本常規切片,厚度為4 μm,采用免疫組織化學Envision二步法檢測所有標本GPC1蛋白表達,嚴格按試劑盒說明書操作。兔多克隆GPC1抗體(ab73979)購于英國Abcam公司,工作濃度1∶200。以磷酸鹽緩沖液代替一抗作為陰性對照,以胞質顆粒狀染色和(或)胞膜染色判讀為GPC1蛋白陽性表達。由兩位病理醫師進行獨立評估,根據染色強度和陽性細胞百分比進行評分[5]:陰性或陽性細胞占比<15%為0分;染色呈淡黃色占比>50%,或染色呈黃色占比15%~50%為1分;染色呈黃色、陽性細胞占比>50%,或 染色呈棕黃色、占比15%~50%為2分;染色呈棕黃色、占比>50%為3分。0和1分為低表達組,2和3分為高表達組。
三、隨訪
通過患者術后就診記錄及電話方式進行隨訪。就診記錄包括門診復查記錄、急診就診記錄和再次入院記錄。隨訪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患者總生存期定義為手術日期至死亡時間或末次隨訪時間(月)。
四、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0.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生存曲線,生存期差異比較采用Log-rank檢驗。采用單因素及多因素Cox回歸模型分析評估影響患者生存期的危險因素,以風險比(hazard ratio,HR)及95%置信區間(95%CI)表示。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PDAC組織與正常胰腺組織GPC1蛋白表達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示腫瘤細胞的胞質內呈細顆粒狀陽性著色和(或)胞膜陽性表達,而癌旁正常胰腺組織均為陰性表達(圖1)。PDAC組織GPC1蛋白陽性表達率顯著高于癌旁正常胰腺組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93.407,P=0.000)。125例PDAC組織中38例(30.4%)GPC1蛋白表達評分為0分,19例(15.2%)為1分,23例(18.4%)為2分,45例(36.0%)為3分,高表達率為54.4%(68/125)。

注:GPC1為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1圖1 胰腺導管腺癌腫瘤細胞胞質(1A)、胞膜(1B)及侵犯神經的腫瘤細胞(1C)GPC1陽性表達(免疫組織化學 ×200 ×400)
二、GPC1蛋白表達與PDAC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
PDAC組織GPC1蛋白高表達與腫瘤部位和T分期均顯著相關,而與患者性別、年齡、有無糖尿病和胰腺炎病史、血CA19-9水平、切緣情況、腫瘤分化程度、淋巴結轉移、神經侵犯及脈管侵犯均無相關性(表1)。

表1 胰腺導管腺癌組織GPC1蛋白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例(%)]
三、GPC1蛋白表達與PDAC患者總生存期的關系
Kaplan-Meier法生存分析顯示,PDAC組織GPC1陽性表達與患者預后呈負相關,GPC1蛋白高表達組及低表達組的中位生存期分別為(11.00±0.82)個月(95%CI9.387~12.613)、(18.00±2.36)個月(95%CI13.382~22.618),高表達組顯著低于低表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圖2)。單因素Cox比例風險分析顯示,T分期和GPC1蛋白陽性表達是影響PDAC患者術后總生存期的危險因素(P<0.001,表2)。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分析顯示,T分期和GPC1蛋白表達水平是影響PDAC患者總生存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01,表2)。

表2 125例胰腺導管腺癌患者術后總生存期的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注:GPC1為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1
討 論
近年來,應用患者液體活檢材料,結合外泌體、循環腫瘤細胞和代謝小分子化合物檢測以尋找PDAC早期診斷標志物的研究取得了可喜進展[7-9]。血清中GPC1陽性的循環外泌體結合CA19-9檢測能夠發現82%的早期PDAC,并能夠在術后隨診和患者預后預測方面發揮作用,受到廣泛的關注[10]。本研究結果顯示,PDAC組織中GPC1蛋白表達升高且GPC1蛋白表達與腫瘤T分期呈正相關。PDAC的T分期標準依賴于腫瘤大小(T1~T3)和累及腹腔干、腸系膜上動脈和(或)肝總動脈(T4)的情況[11-12],提示GPC1可能參與PDAC的發生與進展,GPC1高表達的腫瘤生長更為活躍,侵襲能力更強。此外,GPC1蛋白高表達與患者的總生存期呈負相關,是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與Lu等[13]的研究結果一致。
GPC1由核心蛋白及糖鏈構成,具有胞內段和跨膜段結構域。GPC1的功能受到其糖鏈硫酸化程度以及核心蛋白錨著位點結構的影響[14]。本研究結果顯示GPC1在PDAC腫瘤細胞胞質和胞膜均呈陽性表達,此染色模式可能提示GPC1蛋白處于不同的結構、剪切狀態和功能階段。在PDAC發生和進展的過程中,GPC1可能保持了持續的蛋白合成與分泌,并在以近胞膜的區域發揮功能。
PDAC的原發位置(頭部與體尾部)與臨床預后之間的關系尚有爭議。Birnbaum等[15]研究比較了208例胰頭部和41例體尾部樣本的臨床病理學和基因表達數據,表明PDAC解剖學位置是一個獨立的預后因素。頭部原發PDAC患者的2年總生存率高于體尾部PDAC,并分析鑒定出334個差異表達基因。頭部組上調的基因提示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髓源性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活化和胰腺外分泌功能活躍;體尾部組的免疫原性特征表達顯著降低,并且上調基因與腫瘤細胞的鱗狀分化有關。另有研究報道,與胰頭PDAC相比,體尾部PDAC的K-ras和Smad4表現出更豐富的基因學改變[16-17],提示發生在胰頭鉤突部的PDAC與發生在胰體尾部的PDAC在驅動性分子事件、腫瘤免疫環境和癌細胞表型上可能存在本質差異。導管上皮可能在不同的微環境、不同的驅動突變下出現不同的分化和演進行為。本研究顯示GPC1表達與腫瘤部位相關,胰頭鉤突部GPC1高表達率為60.6%,體尾部為35.5%,推測這種表達差異可能由上述諸多原因導致。未來需要結合更多病例及詳細的分子檢測數據綜合分析加以明確。
本組伴有神經侵犯的72例PDAC中,41例GPC1高表達,占56.9%(41/72)。盡管統計學分析GPC1高表達與神經侵犯無相關性,但在上述41例PDAC中能夠觀察到多根神經纖維周圍腫瘤細胞的GPC1呈陽性表達。PDAC的腫瘤微環境具有促結締組織增生和高度神經支配的現象,神經周圍浸潤是PDAC的一個典型組織學特征。在這個過程中腫瘤細胞沿著固有的神經纖維生長和遷移,并與不良預后相關[18-19]。PDAC主要起源于胰腺外分泌部的導管上皮,其接受大量感覺和腎上腺素能神經支配。與均勻分布于整個胰腺的腎上腺素能神經支配不同,感覺神經支配在胰腺頭部的外分泌部最豐富,而胰頭是多數PDAC的原發部位。在轉基因小鼠PDAC模型中,使用化學方法去除感覺神經后發現,感覺神經缺失可減少癌前病變——胰腺導管上皮內瘤變的發生,并抑制癌前病變向PDAC的進展[18-19]。有大量研究發現,GPC1作為一種細胞表面的糖蛋白,能夠與多種生長因子和細胞因子結合,這種相互作用對血管生成和腫瘤細胞的增殖、侵襲和轉移能力產生持續影響[15,20]。在PDAC中,GPC1與神經生長因子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需要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GPC1蛋白在PDAC腫瘤細胞中異常高表達,GPC1蛋白高表達與腫瘤T分期及患者總生存期呈顯著相關性,是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