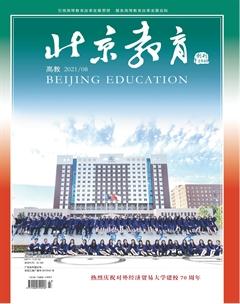先師三記

張靜如(1933年—2016年),北京人。我國著名學者、中共歷史學家、李大釗研究專家。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高校黨建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全國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副會長、北京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研究”項目首席專家。
張靜如先生是黨史大家,在他逝世以后,許多人都很懷念他。我是他的學生,這種感情自然要更深一層。回想從第一次拜見先生,到最后一次告別先生,我的腦海中就會閃過許多珍貴的歷史鏡頭。這不是用一兩篇文字可以表達清楚的。因此,我只能根據自己的體會,選取三個角度,裁剪三個片段,然后按照我的方式連綴起來,名之曰“先師三記”,來寄托我的哀思和對先生的崇敬之情。
張門求學記
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是在2001年,經過一波三折,直到2004年第三次報考,才通過考試,被張先生收入門下。對于這一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我是倍加珍惜的。先生言語不多,但在文章上卻總有獨到的見解。大到論文的主旨,小到注釋的規范,我得到的是一套完整的學術訓練。現在我也當導師,開始指導自己的研究生。我總是把先生教給我的東西,作為經典的教學案例講給我的研究生,讓他們從中得到智慧和啟迪。
我希望他們像先生一樣,做一個合格的“資料員”。1953年,張先生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資料員”。那時候,他在資料室內放了一張床,常常睡到那里,以便看到更多的書。他甚至把《新青年》月刊一卷至九卷、四期季刊、五本不定期期刊中的論文、小說、詩歌、譯文、通訊、廣告,都一字不落地全部看完。為了寫《李大釗同志革命思想的發展》(1957年)這本書,他不滿足于劉弄潮在《李大釗著述目錄試編》中提及的100多篇,也不滿足于蔡尚思在《李大釗著述的分類編目》中提及的200多篇,而是到北京市委檔案室借來李樂光(李大釗同鄉)生前所存李大釗著作的抄件300多篇,全部抄下并用能夠找到的原件校對。這比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選集》中收錄的133篇要多得多。先生之所以被譽為“國內外李大釗研究的第一人”,我想與他有“資料員”的這個經歷是分不開的。
大師印象記
石仲泉先生曾贊譽張先生為學問大家,原因有四:一是學問的開創性與創新性,不僅開辟學科建設的新領域,而且還提出諸多具有創新性的學術觀點;二是學問的厚重性與深刻性,能做到史料扎實,分析精到,成一家之言;三是學問的廣博性和多領域性,能將多門學問融會貫通并在多個領域有所建樹;四是學問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其著述之豐,加之培養研究生、國內外訪問學者之眾,在黨史界可以說無以出其右者[1]。仲泉先生所說自然不虛,但除此之外,我想先生那種“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率真”和“自省”,也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效法的大師氣象。
先生是李大釗研究的開創者。他在24歲時就出版了《李大釗同志革命思想的發展》一書,這既是國內學者研究李大釗革命思想的首創之作,也是事實上存在的“李大釗學”的奠基之作。但先生卻并不以此自滿,他認為“這本小冊子基本上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精神”,之所以說“基本上堅持”,是因為書中“確有不夠實事求是之處,如有些結論就說得過了頭,有些話說得絕對了些,不甚符合實際”。
如果說這還有些“大而化之”的話,那么下面的這個自我批評則更見這位黨史大家的“真功夫”。例如:在《關于研究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幾點意見》一文中明確指出,自己在1980年發表的《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之史的考察》一文,由于沒有看到1925年黨的十月擴大會議的材料,因而對李大釗的《土地與農民》一文就作出了不甚恰當的評價,認為其“提出了耕地農有的正確主張。實際上,耕地農有是在十月擴大會議上提出來的,而李大釗的文章則是依據中央決議精神寫的。這種沒有弄清情況就妄下結論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在這篇文章的“評文紀事”中,他進一步寫道:“文中在舉例中,對我以往文章中的錯誤,做了更正,我以為有錯就應該承認、糾正,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2]
正因為以研究李大釗起家,所以先生始終都在關注和反思自己的這個“老本行”。例如:在《李大釗和北京師大》一文的“評文紀事”中,他就對22年前的這篇舊作寫出如下評語:“我在文章中把1921年10月李大釗在女高師的講演與12月1日發表在《晨報》上的《美國圖書館員的訓練》弄混了。……功夫不到家,必然出錯。科學研究只差一步也不行,這是絕對真理。”[3]當看到自己的學生朱志敏教授寫出一部高質量的《李大釗傳》時,他欣然為之作序。也正是在這篇序言中,他用自我批評式的話語表達了對李大釗研究的期望:“我50年代寫關于李大釗的書時,沒有這樣的水平。有人說在學術研究上一代不如一代,我認為一代更比一代強。社會在發展,學術研究在進步,這就是我們希望之所在。”[4]
先生是黨史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開創者,其代表性著作是《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對此,黨史界有很高贊譽,認為它是中共歷史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最有價值的成果”[5]“這種結構性、層次性分析對根除中共黨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條化、原理化思維模式是一種理性的救治”[6]。但先生同樣并不以此自滿,“我以為這本書的主要毛病,是沒有能提出一個完整的中介理論體系。”正因為認識到書中的缺憾,所以先生始終都在關注和反思這個“中介理論體系”的建構問題。此后歷經十年思考和反復論證,他終于得出一個較為成熟的結論,并將它概括為如下五個方面:一是以近現代社會史為基礎,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為主線;二是以社會進化為基礎,以社會變革為動力;三是以群體社會作用為基礎,以個人社會作用為契機;四是以社會心理為基礎,以社會意識形態為導向;五是以歷史辯證法為核心,以中國傳統治史方法和現代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精華為輔助。[7]
一般說來,史學批評是史學理論產生的基礎。它為史學理論提供了豐富的原料與素材,成為史學抽象的根據。先生構建的“中介理論體系”,不僅具有推動黨史研究的方法論意義,而且還具有指導黨史批評的獨特價值。
關于自己的學術研究,先生曾有一個總體評價。他說:“在有關中共歷史研究方面,我提出的新的并在學界產生較大影響的主張有四點:一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應該屬于歷史學科;二是以現當代中國社會史為基礎,深化中共歷史研究;三是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歷史;四是倡導研究中共歷史學理論和方法。在我的研究中,毛病是在每個新開創的研究領域中沒有深入下去。”針對文中的“功過是非”,在《張靜如文集》“評文紀事”中,他均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從“信、達、雅”的角度作出了精彩評論。
第一,就真實性而言,先生總體上肯定其文章,“思想解放,比較實事求是”[8]。但他也嚴肅指出一些文章中的不實之處。例如:在《〈汪精衛評傳〉序》的“評文紀事”中指出:“文中說在本書出版前還沒有一本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汪精衛傳,這話說得不準確,說明我孤陋寡聞。”“看來,不要輕易說‘以前沒有過‘填補了空白‘歷史上第一次之類的話,說了,常常會被打屁股。”[9]
第二,就思想性而言,先生總體上肯定其文章,“有開創性,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和新的觀點”[10]。但他也不放過對一些“陳舊”之作的反思。例如: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毛澤東思想》的“評文紀事”中說:“沒有什么新的見解,只是把以往的觀點集中一下。”[11]
第三,就藝術性而言,先生總體上肯定自己“寫文章、講話深入,通俗易懂”。但他也對一些文章的敘事文風提出批評。例如:他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的“評文紀事”中說:“文中的缺點,十分明顯。不僅論斷絕對化、簡單化,如對胡適的分析之類,而且敘述方法上也很呆板。”在《李大釗和陳獨秀》的“評文紀事”中說:“有些話不通暢,從內容上說是很膚淺的。”[12]
先生認為,“有的學者很在乎自己的對錯,其實也沒有什么,對了當然好,不對改了就是。這類事,我覺得不必隱諱。”[13]正因為能不隱不諱,知錯即改,所以在自我評價中才會說出“大實話”。這也就是“為什么他不怕自揭其短,卻比別人更受敬重的原因”[14]。
千秋功業記
“八十三載人生路,黨史學科擎天柱。務實求真開新經,情滿杏壇英才出。”[15]這既是先生學術人生的真實寫照,也是北京師范大學“勵耘”“樂育”精神的生動體現。
先生的最大功業,就是率先構建黨史學科大廈。黨史學屬于史學門下的歷史學科還是法學門下的政治學科,曾一度成為困擾該學科發展的最大難題。因為自1958年以后,黨史被確定為高校的政治理論課之一,人們便漸漸忘記了它作為歷史學科的性質。在中國學術界,先生最早關注這一問題。他認為,高校歷來都有依據不同時期對學生進行理論和思想教育的需要,選擇一定的學科充任政治理論課,被選入的學科,并不因此而改變它們的本來性質。但由于人們長期忽視了這一點,將黨史認定為政治理論學科,容易引導人們不是按照史學而是按照政治學的方法來研究黨史學,這樣既不利于黨史學按照其自身的規律發展,也不利于發揮自己的學科特長為高校的理論和思想教育服務。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之后,先生于1987年發表《黨史學科建設斷想》,首次明確指出“黨史學是歷史學”“黨史是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的縱向學科,是近現代歷史時限之內的一部專史,其性質自然應該屬于歷史學科”[16]。
黨史學科發展落后,與學科性質不明有密切關系。因此,在闡明黨史學科性質之后,先生便呼吁學界加大對黨史學理論問題的研究力度。1989年,先生還與訪問學者唐曼珍教授合作編寫《中共黨史學史》,對黨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各個時期黨史研究概況,以及黨史重要文獻資料的編纂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探討,并從理論上提出黨史學史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意義,從而為黨史學科的發展和完善作出重要貢獻。此外,他還強調:“任何人文社會科學都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但每個學科又有自己的獨立理論,歷史學科也應如此。”“用唯物史觀指導黨史研究,需要建立起一個中介理論體系。否則,無法應用。”[17]先生說他寫《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一書就是打算要解決這個問題。
在黨史學科建設中,先生不僅強調“固本”,強化基礎理論研究,而且主張“開新”,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王炳林教授曾對其學術貢獻作八個方面概括:一是以五四運動為基礎的中共歷史事件研究;二是以李大釗為中心的中共歷史人物研究;三是中共歷史學科建設研究;四是中共歷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五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史研究;六是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研究;七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八是高校思想政治課教學與改革研究。
在以上八大研究領域中,先生均保持國內領先地位。除此之外,先生還積極推動黨史學科為現實服務,在北師大黨史學位點開設新的研究方向。一是設立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現代化研究方向。自1991年設立這一方向以來,先生帶領他的同仁和學生先后發表了《“五四”與中國社會現代化》《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現代化》《再論社會現代化》等一系列論著,從現代化角度觀察共產黨歷史,突破傳統的研究模式,從而引領了黨史研究的新潮流。二是設立高校黨建研究方向。2004年,先生倡導成立北師大高校黨建研究中心,并在全國黨史學位點中率先設立了這一研究方向,并得到學術界的初步認可。
先生還有一項重要功業,就是教書育人。在63年的職業生涯中,他踐行“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格言,譜寫“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篇章。先生一生桃李滿天下,培養的博士、碩士和訪問學者近150人,還有更多的編外弟子。先生喜歡年輕人,總是積極創造條件獎掖后學,幫助他們進步。從1986年開始,他就發起組織全國黨史學位點年會,構筑青年人相互學習、交流思想的學術平臺。每次會議,他都慷慨解囊,對學生論文演講比賽的優勝者予以嘉獎。現今,這項活動已成為我國黨史學界一件盛事,30多年從未間斷。先生一生儉樸生活,但他卻把節省下的工資收入10多萬元貢獻出來,于2002年設立“張靜如中共黨史黨建優秀論文獎勵基金”,用以獎勵全國范圍內黨史黨建研究的優秀論文成果。這是目前我國黨史學界唯一的學術論文獎勵基金,對于全國黨史專業中青年學術隊伍建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2016年8月29日,先生在北京與世長辭。在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際,我想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對其精神風范作一次深入總結。我以為,我們一定要學習先生鍥而不舍的執著精神。從一個動蕩年代的知識青年,成長為一代學術名家,沒有這種執著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我們也一定要學習先生富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他總是能夠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這是多么難得的一種可貴品質。我們還一定要學習先生自信達觀的生活態度。他從不因處境的一時困難而終日憂心忡忡,也絕不為追求富貴而往來奔走、到處鉆營。當然,更為重要的,還是要繼承先生的遺志,光大先生的事業。他雖已筑起黨史學科這座大廈,但的確還有一些“添磚加瓦”的事,需要我們這些后學者來完成。
參考文獻:
[1]賀張靜如先生從教60周年[J].北京黨史,2013(2):29-34.
[2][3][8][10][12]張靜如. 張靜如文集:第1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299,350,序言,序言,76.
[4]朱志敏.李大釗傳[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序言.
[5]郭德宏.中共歷史研究不斷創新的一個典范—評《張靜如文集》[J].中共黨史研究,2007(4):121-122.
[6]一部凝聚理論思維的創新之作─評張靜如著《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J].北京黨史研究,1996(1):50-56.
[7][13]張靜如.張靜如文集:第3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778,715.
[9]張靜如.張靜如文集:第2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473.
[11]張靜如.張靜如文集:第4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1216.
[14]李向前.人有多真,學有多深—張靜如《暮年憶往》讀后[J].中共黨史研究,2013(3):121-125.
[15]周良書.張靜如先生的學術人生[J].唐山學院學報,2016,29(5):1-5.
[16]張靜如.黨史學科建設斷想[J].黨史研究,1987(6):18-23.
[17]周良書.“黨史學是歷史學”—訪張靜如先生[J].北京黨史,2016(5):58-62.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責任編輯:苑聰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