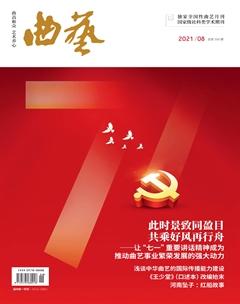鄉(xiāng)音裊裊 余韻悠長
蔣慧明

“方言就是一個(gè)地方最本土的聲音,也最能體現(xiàn)一個(gè)地方最本土的魅力和特色。”這是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長篇小說《繁花》的作者金宇澄在一篇訪談文章中的話。小說中隨處可見的滬語詞匯,連綴起了一幅幅極具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場景,獨(dú)特的方言敘事令這部長篇小說大放異彩。而據(jù)此改編的蘇州彈詞版《繁花》,則可能是較話劇、電影改編外更能貼近原作精髓的一種舞臺呈現(xiàn)樣式,只因,方言的魅力恰恰也是蘇州彈詞的特色之一。
眾所周知,曲藝的曲種之所以多達(dá)數(shù)百種,其中很重要的一個(gè)原因便是各地方言的差異,而“依字行腔”的基本規(guī)律正是根據(jù)不同方言的字音譜唱旋律,也就有了不同曲種各具特色的唱腔音樂。可見,方言在曲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演出乃至傳播方面皆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方言對地域文化的保護(hù)與傳承
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方言同時(shí)也是地域文化的載體,是體現(xiàn)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種標(biāo)志。我們所熟知的唐代詩人的七絕《回鄉(xiāng)偶書·其一》:“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就寫出了人事更迭、鄉(xiāng)音如故的感慨,在這里,“鄉(xiāng)音就是方言”。①
作為當(dāng)?shù)厝藗內(nèi)粘鞑バ畔ⅰ⒔涣魉枷氲墓ぞ撸窖跃哂袧庥舻泥l(xiāng)土氣息,將地方的文化精神、風(fēng)土民情與社會(huì)習(xí)俗融于一爐。正如西方人類學(xué)家的論點(diǎn):“語言也不脫離文化而存在,就是說不脫離社會(huì)流傳下來的,決定我們生活面貌的風(fēng)俗和信仰的總體。”②“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禮記·王制》)有道是“十里鄉(xiāng)俗不同”,不同的方言,體現(xiàn)了不同地域人民的生活日常與社會(huì)生產(chǎn),自然也體現(xiàn)了人們的審美觀念與生活情趣。早在司馬遷撰寫“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的不朽名著《史記》時(shí),便大量運(yùn)用了關(guān)中方言來描寫人物的性格、風(fēng)度與日常生活習(xí)俗,使全書頓生錦上添花、通俗引人之妙,關(guān)中方言中所蘊(yùn)涵的“古色古香之風(fēng)和凝重典雅之貌”③彰顯無遺。
方言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諸多學(xué)者早有論述,尤其當(dāng)下,隨著社會(huì)城市化進(jìn)程的加快,普通話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廣,方言的生存空間卻變得越來越狹小,因此,方言作為一種獨(dú)特的文化記憶又重回公眾的視野,保護(hù)和傳承地方方言的呼聲亦日漸成為共識。留住方言,就是留住了文化的多樣性和民俗風(fēng)情多樣化的根。
除了日常生活交際和溝通,方言在大量文藝作品中的運(yùn)用最顯而易見,也最能直觀地體現(xiàn)“一方水土育一方人”的文化烙印,因而,當(dāng)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在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融合中逐漸消隱時(shí),保護(hù)和傳承方言理應(yīng)成為我們每一個(gè)中國人的責(zé)任。
二、方言在曲藝作品中的重要作用
沒有了方言,方言曲藝亦即地方曲種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和地域文化的豐富性一樣,地方曲種的多樣性也離不開各地方言的運(yùn)用。
例如在南戲發(fā)源地的浙江瑞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曲種便是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的瑞安鼓詞,有著極其深厚的群眾基礎(chǔ),不僅是瑞安當(dāng)?shù)匕傩障猜剺芬姷囊环N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更是在外的瑞安游子寄托情思的最佳載體。瑞安鼓詞的魅力和特色,方言的運(yùn)用是重要因素之一。瑞安方言屬于甌語體系,其最為突出的特點(diǎn)便是保留了古漢語的聲調(diào)體系,至今仍有著古音中的全部入聲字,甌語因此被稱作華夏古漢語的“活化石”。④而主要使用瑞安方言中的瑞安話進(jìn)行說唱的瑞安鼓詞,輕盈流暢,溫情活潑,有著濃濃的鄉(xiāng)情、鄉(xiāng)音和鄉(xiāng)韻,其中所涵含的文化底蘊(yùn)更是值得我們倍加珍惜。
再如蘭州鼓子詞的傳統(tǒng)曲目之一《罵雞》,盡管同類題材的曲藝作品在許多地方都有存在,但又都因各地方言和民間習(xí)俗的不同而各有千秋,尤其是在曲調(diào)的地域性、唱詞的內(nèi)容、表達(dá)的方式和語氣等方面,體現(xiàn)出各具鮮明的地方特色。由對蘭州鼓子詞《罵雞》的考察及對同類題材曲藝作品的橫向比較,學(xué)者發(fā)現(xiàn):其故事內(nèi)容是“隨著歷史上東部人口的遷徙而傳入的舶來品。這個(gè)題材在移植過程中一旦與蘭州地方方言相遇,并且經(jīng)過了聰慧的蘭州鼓子藝人的傳承與改造,就使得《罵雞》成為了蘭州方言的承載物之一。”⑤如果從曲藝學(xué)的角度再進(jìn)一步地深入研究,從這個(gè)作品中方言的運(yùn)用,亦能管窺蘭州鼓子詞與來自北京的滿族八角鼓之間的承續(xù)關(guān)系,以及某個(gè)地方曲種在流布過程中所發(fā)生的諸多變異等現(xiàn)象。
三、方言在當(dāng)下曲藝創(chuàng)演實(shí)踐中的困境
文化和語言是共生的,保護(hù)方言,既是傳承地域文化,也是維護(hù)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努力。不得不說,在方言使用普遍式微的大背景下,特別是年輕群體對原生方言的認(rèn)同感和情感因素大大減弱的情況下,方言竟也成為了地方曲種向外傳播的主要受限原因。普通話的大力推廣,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溝通越來越便捷且毫無障礙,與此同時(shí),各地方言的逐漸“隱沒”,也讓地方曲種的生存境遇變得越來越艱難。
“好聽是好聽,就是聽不懂!”在許多場合,但凡有地方曲藝節(jié)目的演出,常能在觀眾席中聽到這樣的評價(jià)。于是,我們經(jīng)常會(huì)注意到,許多參加全國性比賽的曲藝節(jié)目,或者是在晉京演出的舞臺上,一些地方曲藝節(jié)目會(huì)有意棄用鄉(xiāng)音,而改用普通話來說唱,首要的目的顯而易見是為了爭取更多的觀眾。這樣的改動(dòng)自然也產(chǎn)生了許多爭議,贊之者主要是從“聽懂了”的角度考慮,認(rèn)為可以藉此擴(kuò)大傳播范圍,讓該曲種“走向全國”;而反對者則認(rèn)為:如此改動(dòng)令曲種獨(dú)特的地方韻味頓失,實(shí)不足取。
寫到這里,不妨可以用福建的南平南詞這樣一個(gè)地方曲種在說唱語言運(yùn)用上的變化來舉例說明。南平南詞的語言流變經(jīng)歷了土官話、土官話改普通話和改回土官話這樣的3個(gè)階段⑥,由于特殊的方言環(huán)境,南平南詞這個(gè)福建的曲種一度成為少有的以普通話演繹的地方曲種。隨著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的深入,普通話的南平南詞亦成為了爭議的焦點(diǎn)。在從業(yè)者的努力下,如今,繼《鐵膝海瑞》(2012)、《應(yīng)老漢修橋》(2015)、《印度來的準(zhǔn)親家》《國系九零后》(2019)等用土官話進(jìn)行說唱表演的南詞節(jié)目的相繼獲獎(jiǎng),“從一個(gè)側(cè)面體現(xiàn)出社會(huì)對語言回歸的期待和好評”。⑦
方言不僅是一種地方性的語言、鄉(xiāng)土性的語言,更是一種母語文化。母語,在現(xiàn)代人文中的角色和定位是相當(dāng)重要也是無可替代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設(shè)立有“國際母語日”,其主旨就在于“為了幫助人們了解世界各民族母語文化的現(xiàn)狀,推動(dòng)語言及文化的多元發(fā)展。在理解、寬容與對話的基礎(chǔ)上幫助人們進(jìn)一步加深對語言傳統(tǒng)及文化傳統(tǒng)的認(rèn)識”⑧。那么,就曲藝來說,方言承載著地方曲種的特性,地方曲種的藝術(shù)魅力則有利于方言的傳播,從這個(gè)意義上而言,“如何讓下一代記住方言、傳承方言,這可以說是地方曲藝的歷史重任。”⑨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當(dāng)下曲藝作品中的方言運(yùn)用,一方面保證了曲種的本體特征;另一方面,其在文化傳播和影響力上的群眾性、普及性、娛樂性對方言的保護(hù)和傳承有著不可輕視的重要作用。
注釋:
①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4頁。
② 周振鶴、游汝杰: 《方言與中國文化(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頁。
③ 蔣寶德、李鑫生主編:《中國地域文化》,山東美術(shù)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215頁。
④ 沈克成、何克識編著:《瑞安方言曲藝韻書》,寧波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1-2頁。
⑤ 雷巖嶺、張彥麗:《蘭州鼓子<罵雞>中的蘭州方言和民俗現(xiàn)象分析》,《甘肅高師學(xué)報(bào)》,第20卷第6期(2015),第22頁。
⑥ 張慧:《鄉(xiāng)音鄉(xiāng)情——芻議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xiàng)目“南平南詞”說唱語言的前世今生》,《戲劇之家》,2020年第24期,第32-33頁。
⑦ 同上,第33頁。
⑧ 參見百度百科詞條“國際母語日”https://baike.baidu. com/item/%E5%9B%BD%E9%99%85%E6%AF%8D%E8%AF%AD%E6%97%A5/1835253?fr=aladdi
⑨同⑦,第33頁。
(作者: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曲藝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曲藝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北京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
(責(zé)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