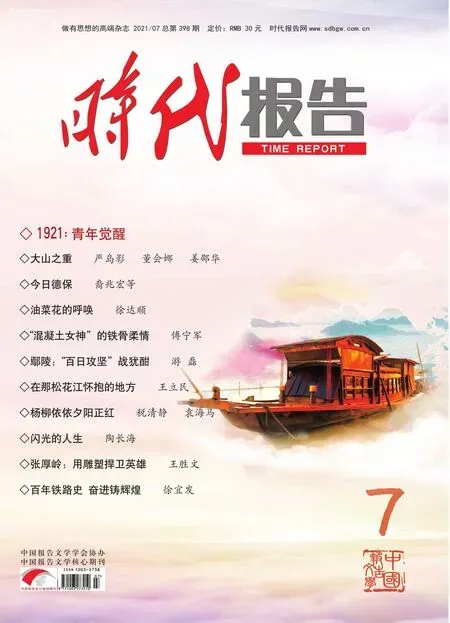張厚嶺:用雕塑捍衛英雄
王勝文



“向英雄潑污水與惡言,豈止是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簡直連一點人性良知都沒有。”一段時間以來,為英雄而歌的文藝創作傳統似乎在弱化。一些居心叵測的人,詆毀英雄、貶損英雄、抹黑英雄的言論屢屢成為輿論焦點,反復挑戰人們的心理底線。在這種亂象之下,駐洛“鐵軍師”這支英雄部隊的軍士長,曾以陶瓷作品“盛世中華”榮獲上海世博會特別獎的作者張厚嶺,用他雕塑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體形象的藝術作品,捍衛著我們的英雄。
1994年12月,張厚嶺來到素有“鐵軍”之稱的英雄部隊服兵役。在部隊里,除了日常訓練,他還學習雕塑。學習之初,張厚嶺碰到了一系列難題,有時泥塑制好了,卻出現斷胳膊掉腿現象,胳膊腿全了,又出現裂紋變形的狀況。為解決這一系列難題,張厚嶺利用假期四處拜師求藝,先后到福建德化陶瓷雕塑廠、廣州雕塑公園、上海多倫路雕塑街、四川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參觀學習,行程6萬多公里,造訪老師20多位,但所遇老師大都含糊其辭,不愿將自己的手藝外傳。經濟拮據時,他幾次都想賣掉洛陽谷水古鎮的住宅。妻子哭著勸他:“你學手藝俺不反對,但你總得給咱孩子留個窩呀!”張厚嶺把自己心愛的幾件藏品變賣后,才渡過難關。后來,他在濟南軍區政治部雕塑家仇世森的傳幫帶下,摸到了門道,求得了技藝。最終,他的作品受到眾多名家的充分肯定,他還被全師官兵親切地稱為“軍人泥人張”。
為英雄塑像,這是張厚嶺走上雕塑藝術之路的一個強烈愿望。2008年7月11日下午2時50分,在汶川抗震救災前線“鐵軍師”的營地都江堰,張厚嶺揚起他的雕刻刀,完成了抗震救災英雄戰士武文斌烈士的雕像。“像,太像了,他就是我的兒子文斌呀!”看到雕像,武文斌的父親武中林眼中飽含淚水。
武文斌是“鐵軍師”炮兵團指揮連一位最不要命的兵,他用26歲短暫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壯歌。時任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簽署命令,授予武文斌“抗震救災英雄戰士”的光榮稱號。
歷史寫下了武文斌和連隊戰友32天創造的業績:他們走遍都江堰市玉堂鎮12個村7816戶人家,轉移群眾3638人,幫助群眾搭建1000余間帳篷和簡易房,組裝木床1818張,卸載救災物資54車。19名醫學專家聯名寫下了武文斌的死亡診斷:腦血管畸形張裂猝死,誘因為勞累過度。
“以前,我和武文斌不是很熟悉,他光榮犧牲后,從搭建靈堂到送他最后一程,我一直在努力尋找他的影子,希望能雕刻一座雕像來紀念他!”張厚嶺的這一想法得到了部隊首長的贊同。
要雕塑,首先就是選土,看似簡單的工序,張厚嶺卻跑遍了都江堰。“這里的土有些硬,不太符合雕塑的標準,但最終我還是決定用這里的土來完成雕塑,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他與巴蜀大地融為一體,讓他的精神永存!”最后,張厚嶺放棄了選擇外地土的想法,從都江堰玉堂鎮鳳歧村取來了泥土。
由于土質較差,張厚嶺就用木棒反復捶打。用了整整一天時間,才將泥土調好。“白天要參加抗震救災,我只能在晚上抽出時間來進行雕刻!”張厚嶺說。
經過10天的反復修改、打磨,武文斌塑像于11日下午雕刻成功。“好像啊,文斌又和我們在一起啦!”部隊官兵發出由衷地贊嘆和感慨。武文斌的父親武中林,被邀請到部隊駐地,他走進張厚嶺那間臨時工作室,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兒子”,滿含熱淚地向張厚嶺道謝。“雕塑的過程,就像是跟英雄在對話。”張厚嶺眼前不斷浮現出悼念英雄的場景:一夜之間,花圈挽幛堆得如山似海,十里八村前來吊唁的人群,擠滿了連隊。拄著拐杖的白發老人來了,蹣跚學步的孩子來了,在地震中被救生還的人來了……
在雪白的床單上,戰友們咬破手指,蘸著鮮血,為武文斌請功。數以千計的群眾,同樣用血書為英雄請功。
不久,武文斌的雕像運抵成都并制成4尊銅像,一尊送給武文斌父母,一尊放在武文斌生前所在連隊,一尊運回“鐵軍師”師史館作紀念,一尊送給都江堰博物館。
張厚嶺對英雄的理解升華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時代的坐標,是精神的燈塔,上了戰場,就是為人民擋子彈的人。抹黑、詆毀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英雄,就是在摧毀其精神航標。英雄題材文藝作品,不僅是民族精神的“營養品”,也是文藝百花園中的“壓艙石”。“要秉承精品意識,塑造英雄形象,用雕塑捍衛我們的英雄。”張厚嶺說。他不斷深入軍營生活實踐,了解和熟悉各種英雄人物。
2010年11月15日,張厚嶺正在師政治部圖書館里看書,不經意間,目光被一本雜志封面吸引過去。自己的戰友、維和英雄謝保軍的大幅圖片映入眼簾,頭戴藍色貝雷帽,肩上佩戴著藍色的聯合國徽章,是那么帥氣。幾個月前,他還不知疲憊地奔波在蘇丹維和戰場上,累得直至腦出血倒下……英雄魂歸故里當天,蘭考縣近十萬民眾列隊相迎。人群里,英雄母親的哭喊撕心裂肺:“我的兒呀,你咋舍得離開媽呀!”
當聯合國駐蘇丹特派團司令摩西·歐比莊嚴宣布授予謝保軍“維和特別貢獻獎”榮譽勛章后,在場的434名中國維和官兵不禁淚飛如雨。
“一個名字,一旦寫入詩行,便可以成為永恒;一個人,一旦雕成塑像,即可以成為不朽!”張厚嶺萌生了為戰友謝保軍塑像的想法。
“給他雕兩個塑像,一個留在部隊,一個留給他父母,好陪伴兩個‘家!”張厚嶺的熱血在燃燒,說干就干。工作室內,張厚嶺手握泥塊,輕輕朝泥胎上捏去。塑一頂藍色的貝雷帽,雕一枚藍色的聯合國徽章……
崇敬、感動在心頭翻涌。在泥土里塑出精神,是雕塑者與英雄的心靈對話,也是雕塑者對自我精神價值的一次重塑。
16年軍旅生涯,先后8次立功受獎,張厚嶺的軍旅人生同樣寫滿榮耀。當坦克駕駛員時,年年是優秀車手;苦學雕塑藝術,反映抗震救災的群雕《眾志成城》獲得軍內外大獎,以及“全軍優秀人才獎”。2010年,張厚嶺還被濟南軍區評為“自學成才先進個人”。
上級的表彰,心靈上的崇敬,化為藝術的靈感,升華為情感的共鳴。塑英雄的軍服時,張厚嶺流淚了。謝保軍從小喜歡軍人,他身穿軍裝離開大家,他可以一生不脫掉它……而這一切,又何嘗不是張厚嶺內心的寫照。
“并不是每個人的離去都能化為明亮的星辰,只有那些生命里充滿了熱血與擔當、犧牲與奉獻的人,才格外耀眼。”放下刻刀時,張厚嶺對英雄充滿了無限敬仰。
電話鈴響了,謝保軍生前所在團的政委王高峰問張厚嶺:“過兩天英雄的父母要來部隊,我們想在團史館給他塑一個像,不知你是否有時間?”
“這一切,多么像天意的安排!”張厚嶺一抹臉上的淚水,笑了:“我早已給英雄塑了兩個像,一個留在英雄的團隊,一個送給英雄的父母!一是為青年官兵樹立起這個時代不可缺少的精神坐標,二是好讓老人想念兒子的時候能夠看到他。”
張厚嶺所在的部隊,是一支有著光榮歷史的英雄部隊——紅二師四團。
1935年5月,紅四團以一天行進240里的急行速度,搶在敵人炸橋前奔向瀘定橋。為了搶時間,他們把生米塞進肚里充饑,塞得滿嘴都是血。22人的突擊隊,冒著東岸敵人的火力封鎖,在鐵索上,邊鋪門板、邊匍匐射擊,激戰兩個小時,硬是重創川軍一個團,奪取了瀘定橋,占領了瀘定城。每想起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張厚嶺都激動不已。
2005年,長征勝利70周年。為了再現紅四團22位勇士在鐵索上的戰斗情景,張厚嶺決定創作一尊《飛奪瀘定橋》的泥塑作品。張厚嶺找來了當年紅軍飛奪瀘定橋的圖片、書籍,認真構思,反復琢磨。為了保證泥塑作品不變形、不開裂,張厚嶺打破以往的制作常規,采用純天然血色黏土,將市面上很少用的榆樹皮切成絲線,加入泥塑這一煩瑣的傳統工藝。經過半年的辛苦創作,最終成功制成,并獻給了紅四團團史館。如今,這尊作品依然指引著后輩不忘初心,走向未來。
2015年9月3日,北京長安街上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閱兵式。中國人民解放軍受閱官兵接受了國家軍委主席習近平的檢閱,接受了黨和人民的檢閱。當守在電視機前的張厚嶺看到十支英模方隊中的“劉老莊連英模方隊”,以排山倒海的氣勢,正步通過天安門廣場時,他激動不已,心中埋藏已久的創作種子一下子被激活。劉老莊連當年浴血奮戰劉老莊的場面,仿佛就在眼前:戰壕里,熱血流淌,一具具身著灰色軍裝的忠骸,仍保持著生前搏斗的勃勃雄姿,有的狠狠地咬著敵人的半邊耳朵,有的緊緊揪著敵人的一綹頭發,有的弓著雙腿,握著捅彎了的刺刀……
張厚嶺決定為他所在的老部隊雕塑一件《浴血劉老莊》的作品。為了更好地展現82位勇士殉國時的英姿,他到駐地的一個小山坡上找到了與當時作戰地形地貌相似的泥土和景物。作品既還原了真實的歷史,又實現了藝術的升華,成為全連官兵發揚抗戰精神,傳承紅色基因的力量源泉。
張厚嶺雕刻藝術的視野不斷地在廣闊的空間延伸,不斷地為捍衛我們的鋼鐵長城增光添彩。
一天,張厚嶺接到一項特殊的任務,老部隊根據上級的指示,要他作為全軍雕塑藝術家代表赴俄羅斯參加比賽。
張厚嶺當即決定用中國的國粹陶瓷,以雕塑的寫實手法塑造出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的形象,以此來見證中俄友誼。
出國比賽前的日子,張厚嶺基本上沒有休息過。雕塑稿經歷4次反復修改,還需要克服燒制的種種困難,在出發前夜,雕塑終于成功出窯。在參賽的18個國家、128支隊伍中,張厚嶺的一尊肖像雕塑,在“友誼屋”帳篷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2016年7月31日,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從張厚嶺手中接過了這件見證中俄友誼的陶瓷文化作品,如獲至寶,并給予高度的評價。
張厚嶺滿載“最佳文化展示國獎”榮譽而歸。當戰友來為他慶功時,他深情地說:“一個人沒有祖國什么也不是,要不是我們偉大的祖國,強大的軍隊,就沒有這次獲得榮譽的機會。”他表示,“地球在轉,時代在變,但英雄不死,正氣永存,仰慕英雄、尊敬英雄、熱愛英雄的信念和意志永遠不會變。”
如今,張厚嶺又找到100多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單,將著手為他們一一雕塑,以此激勵一代又一代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責任編輯/董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