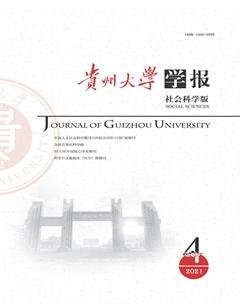經濟圈空間經濟關聯與增長:基于泛成渝地區的經驗分析
陳健 包瀅暉 伍國勇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shb.2021.04.07
摘?要:面對重大機遇的“十四五”時期,構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新格局,對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采用構建鄰接矩陣、地理矩陣與經濟地理矩陣的研究方法,利用空間杜賓模型對2008—2019年泛成渝地區經濟圈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研究發現,該區域在資本、技術以及教育方面的投入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勞動力的空間溢出效應系數為負;貴陽與成都、重慶的關聯系數大于西安與成都重慶的關聯系數,它的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超過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強化增長極城市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從政策、資源稟賦、生態發展的角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推動泛成渝地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關鍵詞:泛成渝;經濟關聯;空間溢出效應;增長極
中圖分類號:F29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099(2021)04-0064-09
一、引言及綜述
2020年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時強調,要推動泛成渝地區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其建設目的在于推動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增強中心城市與城市群之間的經濟和人口承載力,發展中心城市,帶動泛成渝地區輻射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強化增長極城市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即增長極能夠推動主要產業部門高效地聯合一組產業,通過乘數效應帶動該地區經濟增長。區域經濟發展依賴于條件較好的產業和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使該地區成為增長極,縮小區域經濟差距。從西部大開發和西部陸海新通道對區域經濟聯動效果來看,增長極在擴散效應的作用下,致使城市內部經濟結構升級、轉型,同時也使內部產業向周邊地區擴散,對周邊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西部大開發是為了完善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其范圍包括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全區域發展視角來看,泛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需要西部大開發,在西部地區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增長極。如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城市群,依靠經濟圈帶動其區域發展。因此,西部地區也需要建設一個引領發展的經濟圈,而泛成渝雙城經濟圈便起到引領作用。發揮成都、重慶和陜西綜合優勢作用,使重點產業、教育、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取得新成效。2019年10月13日,西部12省區市以及海南省和廣東湛江市,在重慶市進行協議簽約,合作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西部陸海新通道以重慶為發展中心,廣西、貴州為節點,充分發揮鐵路、公路、海運在西南地區經濟發展中的輻射作用,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健康發展。因此,對泛成渝雙城經濟圈區域發展的分析,離不開對貴州與陜西經濟發展的討論。
國內外學者對空間經濟關聯與增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城市空間經濟關聯效應
曹煒威[1]對泛成渝地區空間網絡結構進行研究,提出城市群形成以成都和重慶為核心,驅動其周邊城市網絡化協同發展。Harms[2]發現大量的區域規劃政策都是圍繞增長極城市進行的,導致增長極城市對周邊地區的積聚效應更加明顯。孫久文[3]通過對雄安新區基礎建設以及空間結構的研究,提出經濟圈發展對周邊地區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李慧燕[4]運用耦合協調度對京津冀13個城市的新型城市空間協調發展水平研究,發現經濟圈可以優化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作用良好,空間協調發展程度較好。
(二)城市群經濟增長及其影響因素
王業強[5]對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差異主要來源于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方面。賈冀南、楊麗倩[6]研究中原地區經濟增長時發現,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人才積聚。王振坡、朱丹、王麗艷[7]對成渝城市群城市規模的研究,提出影響城市群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大城市聚集效應逐漸增強,城市群內城鎮化水平差距較大、產業結構相似。何雄浪、葉連廣[8]對長江經濟區要素稟賦差異分析,發現要素稟賦對城市群經濟發展存在顯著影響。孫久文[9]提出如果城市要素過度積聚引起區域間勞動力的失衡,會影響城市群經濟增長效率。
(三)增長極空間溢出效應
張可云[10]對雄安新區經濟發展與空間效應的研究,提出增長極城市的引力作用,會擴大該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金田林、王振東[11]研究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空間溢出效應,提出中心城市規模過大會優化區域空間功能,帶動周邊地區經濟增長。姚鵬、呂佳倫[12]使用增長極溢出效應理論對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提出優先發展區域增長極城市,帶動周邊區域經濟發展。李想、劉春霞、李月臣[13]對成渝雙城經濟圈旅游經濟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發現成渝兩市對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很強。
基于以上研究發現,相關學者對區域經濟關聯與增長和空間溢出效應展開了較為豐富的研究,運用大量的理論和實證分析研究城市群城市空間關聯關系、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城市經濟增長極等內容,但缺乏對泛成渝地區城市群的研究,成渝雙城經濟圈應如何更加有效促進周邊城市經濟增長?將是一個熱點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有必要對“城市群空間經濟關聯與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針對泛成渝地區經濟圈空間形態進行分析,運用引力模型對泛成渝地區經濟圈經濟聯系強度進行測度,構建泛成渝地區經濟增長空間計量模型,對經濟增長因素進行分解探究,進而分析成都、重慶對周邊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有利于泛成渝地區形成更加良好的經濟發展關聯機制,為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相應理論依據和現實路徑。
二、泛成渝地區經濟圈各市經濟關聯和增長機制
Francois Perroux[14]認為:“區域經濟增長應該最先出現在那些具有創新的行業,而這些行業常常聚集經濟區的某些空間點上,進而形成該地區的增長極。”從泛成渝區域空間關系來看,成渝雙城增長極即為該地區經濟增長的龍頭區域,通過對周邊城市的輻射作用,帶動區域經濟增長。對成渝雙城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關聯及經濟增長方面,分析成渝雙城增長極的極化和擴散作用,有利于周邊地區經濟發展。根據增長極理論,成渝雙城憑借“虹吸效應”,大量吸收該區周邊的勞動力、資本等,使得該地區經濟水平嚴重失衡,極化效應大于“涓滴效應”。隨著中心城市經濟實力的提升,涓滴效應慢慢大于極化效應,最終使得該中心城市的經濟水平與其周邊地區趨于平衡。使用中心外圍理論研究泛成渝地區經濟增長與周邊地區產業關聯。成渝雙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足,將會吸收周邊的生產要素,同時產生大量創新成果,這些創新成果會不斷地向外周邊區域擴散,產業在空間上積聚發展,使泛成渝地區的產業更加協調。這種由集聚效應產生的競爭優勢會在該城市群中脫穎而出,形成該地區的增長極。
成渝兩市的經濟體量與其周邊城市之間的差距較大,致使泛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發展不協調,周邊地區發展動力不足。中心城市產業體系不健全,能級不高,周邊地區協調發展機制不完善。泛成渝地區沒有高新技術產業支撐,經濟發展主要依賴資源密集型產業,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同于京津冀、長三角等地區的發展模式,成渝“雙城”受地理因素影響,致使經濟發展與周邊地區不協調,在這種情形下,成渝兩市容易發生激烈競爭,形成“雙龍吸水”的局面,容易產生“鄭寧—克魯格效應”。那么,如何協調該地區整體協調發展,是泛成渝地區未來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問題。
不同地區增長極的“極化與涓滴效應”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雖然有所差別,但是從宏觀層面上看,該集聚優勢可以為該城市的發展帶來巨大效益,最終形成該地區的增長極。從長三角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該地區憑借其雄厚的資本吸引大量的人才以及眾多大企業家在該地區落地,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入該地區,為該地區帶來強勁的發展動力。而泛成渝地區整體實力趕不上長三角地區,在發展方面受外部極化效應大于該地區的涓滴效應的影響,其經濟發展空間被壓縮。從泛成渝地區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方面來看,基礎設施可以促進產業形成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貴州、陜西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于其工業發展水平,相關配套設施跟不上,工業缺乏支撐力度,阻礙其工業發展。研究泛成渝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打造西部地區增長極,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因此,從理論上來看增長極對泛成渝地區經濟關聯與增長具有深遠影響。
三、模型構建
(一)空間引力模型構建
依據程惠芳、阮翔[15]等人的研究方法,將“經濟規模、人均國民收入與中國的地理距離等變量納入引力模型”,并通過構建空間引力模型,對泛成渝城市群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度進行測度。
Rij表示城市i與城市j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度,Pi、Pj表示城市i與城市j的人口規模,Gi、Gj為城市i與城市j的GDP,dij表示城市i與城市j之間的矢量距離。
(二)經濟增長模型
根據索羅經濟增長核算模型,資本、勞動力會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低估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資本、勞動力和技術作為基本生產投入要素,可以作為經濟增長的解釋變量,GDP作為被解釋變量,選擇C-D(柯布—道格拉斯)經濟增長模型,對泛成渝地區經濟圈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經濟增長進行測度。對空間計量模型中的,面板誤差模型(SEM)、面板自回歸模型(SAR)以及空間杜賓模型(SDM)進行篩選,建立空間回歸模型,以此檢驗各個城市群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度以及經濟發展中相關要素投入對該經濟體產生的影響。
其基本模型如下:
Lny=αLnA+βLnK+γLnN+ε
其中,α、β、γ為待估參數,ε為誤差項,Lny、LnA、LnK、LnN分別為該區生產總值、技術、資本以及勞動力的對數形式。以SEM、SAR、SDM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如下:
空間自回歸模型:
Lnyit=ρW′tyt+β1LnAit+ β2LnKit+β3LnNit+ηi+μt+λit(1)
空間誤差模型:
Lnyit=β1LnAit+β2LnKit+β3LnNit+ρWiεi+ηi+μt+λit(2)
空間杜賓模型:
Lnyit=ρW′tLnyt+β1LnAit+β2LnKit+β3LnNit+τ1d′tLnAt+τ2d′tLnKt+τ3d′tLnNt+ηi+μt+λit(3)
其中,y為人均GDP,i為城市,t為時間,A、K、N分別為技術、資本以及勞動,ρ、β1、β2、β3、τ1、τ2、τ3分別為該模型的估計系數,ηi為個體趨勢,μt為時間趨勢,λit~(0,σ2In)為對以上空間模型運用最大似然估計。
(三)權重矩陣構建
依據安虎森[16]的研究方法,本文構建常用空間權重矩陣地理權重矩陣(W1)、經濟距離矩陣(W2)和經濟地理矩陣(W3),對成渝城市群進行空間計量分析。
其中,d表示城市i與城市j之間的距離,yi、yj分別表示城市i與城市j的GDP。
(四)變量描述
本文選取2008至2019年泛成渝地區各地級市數據,數據主要通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獲得,為消除通貨膨脹對GDP的影響,本文以2008年的GDP作為基期,計算各年份GDP平減指數。選擇以固定資產投資作為資本,科技投入作為技術要素,以年平均就業量作為勞動力。各變量描述性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面板數據容易出現自相關、異方差等問題,為使數據更加平穩,本文對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然后對相應數據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見表2),組內自相關(Wooldridge)檢驗值為1.111,組間同期相關(Pesaran)檢驗值為5.66,組間異方差(Wald)檢驗值為40 065.75,Pesaran和Wald檢驗均在1%水平下顯著,Wooldridge檢測值不顯著,說明數據存在組間同期截面相關和組間異方差問題,本文數據為短面板數據,可以忽略組間自相關的影響,為了不降低模型的回歸結果,只需要重點分析組間同期相關即可,使用“組間同期相關”穩健標準誤對模型進行回歸處理。
四、實證分析
通過對中心城市聯系強度進行測算發現,該區域呈現為重慶>成都>西安>貴陽的強度排序。在與中心城市聯系系數方面,重慶—成都為91.6,重慶—貴陽為62.9,重慶—西安為10.4,成都—貴陽為382,成都—西安為30.1;說明在經濟關聯方面,泛成渝三個區域關聯較強,成都、重慶對該地區輻射較強。
基于Morans I指數對泛成渝地區進行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泛成渝地區在空間上存在較強的關聯。不同城市之間呈現出較高聚類的回歸結果。在GDP、資源、技術以及勞動力流動方面尤為顯著。考慮到四川、重慶、陜西和貴州所屬區域屬于西部欠發達地區,計量結果顯示該地區空間關聯層面呈現出較強的相關性,但是這種相關性也只符合俱樂部收斂的特性,因為時間、空間、政策等因素導致不同省份的經濟表現有所不同。
從表3的檢驗結果來看,泛成渝地區城市群之間存在著較強的空間關聯。莫蘭指數為正數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即泛成渝地區經濟圈GDP之間存在正相關。從莫蘭散點圖分布上來看城市群之間的經濟聯系主要呈現出低高型,且分布相對集中,呈現為積聚態勢。該地區主要以成都和重慶兩座城市為中心,表現為“雙峰增長極”的區域分布格局。從整個地區來看,該區域城市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在第一象限內相關城市較少,而大部分城市發展處于低高型或者是低低型,相對原點集中。因此,有必要加強該地區城市之間的聯系,增強貴陽、西安等省會城市經濟實力,實現多核增長極帶動的方式發展地區經濟。
通過研究空間面板計量模型之間的內在邏輯性,并給出了使用空間面板模型具體形式的過程。基于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泛成渝雙城經濟圈數據進行檢驗。莫蘭指數檢驗結果顯示,泛成渝地區城市群之間存在較強的經濟積聚和空間相關的特征,因此,選擇空間面板回歸模型估計效果相對更優。但為選擇相對合適的計量模型還需進一步對相應數據進行檢驗。三種權重矩陣下的空間誤差以及空間滯后LM檢驗結果見表4。檢驗結果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該城市群之間存在較強的空間相關性。地理權重(W1)除了在LM-lag和R-LM下不顯著外,其余檢驗均在1%水平下顯著。經濟距離權重(W2)和經濟地理距離權重(W3)全部在1%水平下顯著。根據LM檢驗結果來看,選擇建立空間杜賓模型較優。
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采用固定效應估計效果要優于隨機效應,基于Hausman檢驗結果,本文將采用面板空間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表5中列出了普通面板以及不同權重矩陣下空間面板的回歸結果。結果發現經濟距離下的可決系數(R2)為0.636 2,模型回歸系數相較于其他模型更加顯著,因此,本文選取經濟距離下杜賓模型進行泛成渝地區經濟增長極與經濟相關性分析。
表5中第(3)列結果顯示,泛成渝地區的技術、教育支出、勞動力以及資本都對該地區經濟增長起到正向促進作用,技術、資本、勞動力均通過5%顯著性水平的檢驗,教育在1%水平下顯著。其中,科技每提高1%會使得GDP平均增加0.143%,資本每提高1%會使得GDP平均增加0.072 5%,勞動力每增加1%會使得GDP平均增加0.095 5%。
不同要素對GDP增長的邊際貢獻率相差較大。相對于資本和勞動力,技術以及教育對GDP的增長促進效應更顯著。控制變量ppi、ind和ser對GDP增長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從泛成渝地區的空間溢出效應來看,技術、教育以及資本的溢出系數為正,均對泛成渝地區產生正向空間溢出效應,而勞動力的系數為負數,且在5%水平下顯著。主要原因在于該地區經濟差距較大,尤其是受到成都和重慶雙核增長極的影響,憑借其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就業機會以及社會福利保障等優勢,會對該區域產生較強的虹吸效應,大幅度吸收周邊地區的生產要素,致使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技術因其自身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以及市場關聯性,其溢出效應一般對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強的促進作用。不同城市之間生產要素的投入與流動,會使得該地區不同城市的經濟發展出現較大差異。
對泛成渝地區經濟圈經濟增長溢出效應進行偏微分分解,以測度其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及總效應。從表6中可以發現技術、教育、資本的總效應為正,直接效應在5%水平下顯著大于間接效應。發現技術、資本以及教育的投入增加會對本區域以及其他城市經濟發展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但是,勞動力對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沒有表現出積極態勢。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虹吸效應”,造成勞動力生產要素分布過于集中,對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產生抑制作用。第一、第二以及第三產業的直接效應均通過了0.1%的顯著水平,對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很高的積極態勢。三大產業的直接效應均大于間接效應,且第二、第三產業的溢出效應系數明顯大于第一產業,說明三大產業雖然對該城市群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但是產業發展主要依靠第二和第三產業引領,尤其是第二產業發展高過第三產業,說明西部地區未來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潛力。
從三大產業發展方面來看,泛成渝地區第二產業發展具有較強的優勢。一方面,國家相繼出臺各項支持西部發展政策,這對吸引外資入駐西部建廠與吸引勞動力匯聚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另一方面,政策的扶持、產業的積聚,勢必帶來第二產業的快速發展,空間溢出效應將會更加顯著。由于第二產業對基礎設施的要求比較高以及產業自身的積聚效應,勢必會造成產業發展不均衡。因此,諸如陜西和貴州這種限于地理條件以及經濟資源實力等條件較為欠缺的地區,要重點考慮第三產業的發展。生產要素的不完全流動,制約著泛成渝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空間溢出效應的釋放。鑒于“行政區經濟”效應的存在,需要從國家層面出臺相應的規劃,打破限制經濟資源流動的壁壘,促進區間生產要素流動,提高生產要素的邊際貢獻率,對促進泛成渝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泛成渝地區經濟發展為背景,使用該區域2008至2019年33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對泛成渝地區城市群之間的經濟增長與空間溢出效應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第一,結果發現泛成渝地區經濟圈之間存在很強的空間關聯,經濟發展以及產業之間具有很強的空間溢出效應。第二,城市群內部各城市對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呈現積極溢出效應。從目前來看,第二產業的發展優勢較強,說明該地區的發展空間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較大。這對十四五規劃中提出將東部沿海的相關產業轉移至西部地區,發展西部經濟有也一定影響。第二產業回歸系數大于第三產業回歸系數,說明回歸結果與該項政策吻合。從泛成渝地區經濟圈內部來看,該地區城市發展不平衡,尤其是陜西省,受地理位置的影響,致使其與成都和重慶之間的經濟關聯很弱,相比之下,貴州省與成都、重慶的關聯度相對較高。
根據增長極理論,區域經濟發展增長極的前提,首先打破“行政區經濟”。如果只在一個行政區內建立增長極,勢必造成區域經濟發展割據,資源浪費、地方政府爭奪資源,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最終造成工業項目遍地開花,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而且,破壞區域經濟的空間聯系,將進一步弱化市場對經濟活動的調節作用。第一,需要實現“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過度,可以考慮建立“泛成渝地區聯合公署”,其行政級別高于地方政府,協調各地方利益主體,在促進地方發展的同時,逐步開放本行政區的市場,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第二,改變以往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主導地位,弱化地方政府在市場中的權威,發揮市場活力,使生產要素可以在不同行政區之間自由流通。上級政府應當出面打破這種局面,以避免讓市場的壓力沖破這種局面,造成過高的成本,以成本最小化來處理這種局面,符合經濟效益。第三,同級政府之間進行開放合作必須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做到“大家參與,大家分享”,在制定區域規劃時,要求不同地區政府都要參與制定,經濟發展成果符合各參與方的利益要求。
市場方面,在十四五規劃的章程中,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要素稟賦的差異,推動成渝周邊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業布局。增長極分為自然增長極和人工增長極,發達地區憑借其自然資源優勢,擁有的是自然增長極,欠發達地區則需要政府的公共投資,對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投資,創造增長點。因此,泛成渝地區經濟發展需要加強交通、信息、水利等方面建設,提升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保障能力。使用積極的政策吸引外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重點發展裝備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發揮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成渝雙城加快發展高科技產業,增強高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另外,發展第三產業經濟,提高服務業比重,優化服務業結構,促進服務業全面快速發展。大力發展區域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在產業一體化分工過程中,堅持資源互補,以優勢產業為基礎,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貴州與陜西兩地處在雙增長極的輻射范圍內,在基礎設施、人才交流、生態環境以及產業發展等方面需要在時間與空間方面合理推進,實現區域經濟與產業之間的優勢互補。
參考文獻:
[1]曹煒威,楊斐,官雨嫻,等.成渝經濟圈城市群的經濟聯系網絡結構[J].技術經濟,2016(7):52-57.
[2]HARMS E.Megalopolitan Megalomania: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s Southeastern Region and the Speculative Growth Machine[J].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2019(1):53-67.
[3]孫久文. 雄安新區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定位[J].甘肅社會科學,2019(2):59-64.
[4]李慧燕.“三生”空間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研究[J].生態經濟,2021(5):92-98.
[5]王業強.中國區域經濟增長格局演變與國家增長極體系建設[J].當代經濟科學,2014(1):39-45+125.
[6]賈冀南,楊麗倩.人才集聚視角下的中原經濟區增長極培育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6(4):68-73.
[7]王振坡,朱丹,王麗艷.成渝城市群城市規模分布及演進特征研究[J].西北人口,2019(1):8-14.
[8]何雄浪,葉連廣.長江經濟帶城市群經濟關聯、空間溢出與經濟增長[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20(1):16-28.
[9]孫久文,蘇璽鑒.我國城市規模結構的空間特征分析:“一市獨大”的空間特征、效率損失及化解思路[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5):1-13.
[10]張可云,孫鵬.雄安新區城市發展、空間作用演化與冀中南地區協同[J].河北學刊,2020(6):139-146.
[11]金田林,王振東.城市規模分布、空間功能分工與區域經濟增長[J].現代經濟探討,2021(5):17-27.
[12]姚鵬,呂佳倫.陸海統籌戰略的理論體系構建與空間優化路徑分析[J].江淮論壇,2021(2):75-85.
[13]李想,劉春霞,李月臣.泛成渝地區經濟圈旅游經濟空間溢出效應[J].資源開發與市場.2021(5):1-13.
[14]Francois Perroux. Les Poles de Developpement et la Politique de LEst[J]. Politique étrangère, 1957, Vol.22(3):233-270.
[15]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J].世界經濟,2004(11):23-30.
[16]安虎森,吳浩波.利用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研究空間相關性問題:來自地級及地級以上城市樣本數據[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5(5):107-115.
(責任編輯:楊?洋)
收稿日期:2021-05-24
作者簡介:
陳 健,男,安徽碭山人,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應用與經濟學院。研究方向:區域經濟研究。
包瀅暉,女,貴州貴陽人,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研究方向:文化產業管理。
伍國勇,男,貴州織金人,貴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農村經濟、生態經濟。
Spatial Economic Correlation and Growth of the Economic Circle: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an-Chongqing-Chengdu Area
CHEN Jian 1,BAO Yinghui 2,WU Guoyong 3
(1.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Guizhou,China,550025; 2.Beijing Film Academy,Beijing,China,100088;3.School of Economics (West Center),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China,550025)
Abstract:In the face of major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hiev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This paper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nstructing adjacency matrix,geographic matrix and economic geographic matrix,and uses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economic circle of Pan-Chengdu-Chongqing area from 2008 to 2019.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vestment in capital,technology,and education in this region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an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coefficient of labor is negativ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Guiyang and Chengdu,Chongqing is greater than the that between Xian and Chengdu,Chongqing,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ts secondary industry to GDP exceeds tha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growth pole cit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areas,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resource endowment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this area.
Key words:Pan-Chengdu-Chongqing area; economic relation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growth p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