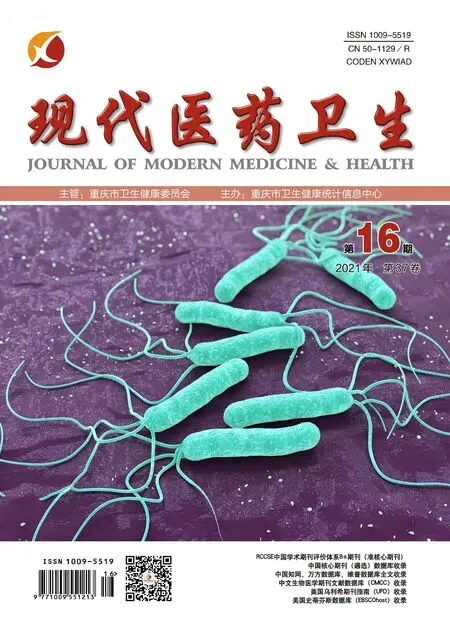成人無癥狀導管相關血栓形成后無抗凝治療對其預后影響研究*
張 偉,傅麒寧,李 追,趙 渝,向 志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管外科,重慶 400016)
導管相關性血栓形成(CRT)是中心靜脈導管(CVC)等置入后一種常見并發癥。文獻報道CRT的發病率為1%~56%[1],巨大發病率差異主要在是否使用影像學檢查手段發現無癥狀CRT。事實上,大多數CRT無置管側疼痛、腫脹等臨床癥狀,亦未出現導管閉塞、導管功能喪失等情況[2]。目前,對CRT的研究多數在危險因素上,在治療方面的研究有限。相關指南[美國胸科協會抗栓治療指南(ACCP)10版與國際血 栓形成與止血學會(ISTH)等]均建議對CRT予以抗凝治療,但無論是劑量還是療程,均是基于對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DVT)治療經驗的推導[3-4]。《輸液導管相關靜脈血栓形成防治中國專家共識(2020版)》提出對于CRT主要進行觀察隨訪,不需要抗凝治療,但該建議僅為專家意見,缺乏臨床研究佐證[5]。在一項前瞻性研究報道中,兒童無癥狀CRT的急性或遠期并發癥發生率很低,因此對于兒童無癥狀CRT可能不需要抗凝治療[6]。國內一項基于輸液港的研究也發現,抗凝治療并未給無癥狀CRT帶來確切收益,但該研究并未報道輸液港移除后的長期預后情況[7]。本研究主要觀察不進行抗凝治療的無癥狀CRT成年患者的預后轉歸情況,以及急性并發癥發生情況,由此評價該種處理方式對于成人無癥狀CRT的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7年9月至2019年1月在本院住院期間請血管外科會診時的輸液導管相關無癥狀CRT患者。輸液導管包括CVC、經外周置入中心靜脈導管(PICC)、完全植入式靜脈輸液港(TIVAP)。納入標準:患者經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檢查存在CRT;排除標準:(1)置管側或同側肢體、頸部、胸部和(或)面部有疼痛、腫脹、紅腫等臨床癥狀,或有導管閉塞或功能障礙;(2)合并其他部位血栓形成[DVT、肺栓塞(PE)等];(3)合并其他疾病需要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療(心房顫動、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等);(4)患者拒絕接受后期預定的超聲檢查。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已通過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
1.2方法
1.2.1導管的管理 根據ACCP 9版[4]的建議:對于與CVC相關的血栓,如果導管功能正常且治療仍然需要,可繼續保留導管。本研究中,采用保留導管至患者不再需要導管,或者導管功能障礙、并發導管相關血流感染(CRBSI)等情況予以拔除導管。對于在隨訪期間無癥狀CRT發展為癥狀性CRT的患者,則由血管外科醫生、靜脈治療團隊和患者所在科室主治醫生聯合討論,共同決定是否拔除或保留導管。
1.2.2觀察指標 診斷CRT時,記錄超聲測量下血栓體積、D二聚體水平并收集患者一般資料(年齡、性別、科室、導管種類、直徑、置入部位等);導管留置期間觀察患者是否出現上肢深靜脈血栓、PE等癥狀;導管拔出時記錄超聲測量下血栓體積、D-二聚體水平、導管留置時間及導管拔出原因;導管拔出后隨訪3個月,統計主要血栓不良事件發生情況,包括中心靜脈狹窄、患肢深靜脈血栓形成后綜合征(PTS)。

2 結 果
2.1患者基本情況 符合標準共357例患者[男81例(22.69%),女276例(77.31%)],平均年齡(52.23±14.26)歲;科室分布:內分泌乳腺外科231例(64.71%),腫瘤血液科35例(9.80%),神經內科/神經外科10例(2.80%),胃腸外科34例(9.52%),重癥醫學科15例(4.20%),呼吸內科/胸外科17例(4.8%),其他科室15例(4.20%);其中CVC置管54例(15.12%),PICC置管89例(24.92%),其余214例(59.94%)為TIVAP。
2.2導管留置時間及拔出原因 357例患者于確診后均未予以抗凝治療。43例CRT患者在會診后24 h內拔出。其中37.21%(16/43)患者已經結束治療,62.79%(27/43)患者擔心無癥狀CRT加重,要求拔出導管。
剩余314例患者在導管留置期間出現2例左側DVT,1例PE,需抗凝治療,故停止隨訪。剩下的311例患者中位保留導管時間為54(24,101)d,其中最長的留置導管即TIVAP保留267 d。91.32%(284/311)患者直至治療結束時導管功能仍正常。導管拔出的原因:0.96%(3/311)患者導管失去功能,0.64%(2/311)患者導管發生意外脫出,2.25%(7/311)患者死亡,但均與靜脈血栓栓塞無關。因可疑CRBSI拔管5例(1.61%),經血液和(或)導管尖端培養確診4例(金黃色葡萄球菌3例,白色念珠菌1例)。3.22%(10/311)患者在治療過程中自行要求拔出導管。
2.3CRT患者血栓緩解情況 除外導管意外脫出及患者死亡9例;其余302例患者中,拔除導管前血栓消退情況:完全消退者(超聲無法檢測出血栓)占35.43%(107/302),血栓體積縮小至診斷時50%以下占30.79%(93/302),血栓體積縮小至診斷時50%~100%占25.83%(78/302),血栓體積增大占7.95%(24/302),但體積增大的患者中未出現置管側或同側肢體、頸部、胸部和(或)面部疼痛、腫脹、紅腫等臨床癥狀。
2.4各組患者確診CRT時與拔出導管時血栓體積及D-二聚體水平比較 CVC、PICC、TIVAP三組患者拔出導管前D-二聚體水平、血栓體積均較首次診斷為CRT時下降,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各組患者確診CRT時與拔出導管時血栓體積及D-二聚體水平比較[M(Q1,Q3)]
2.5隨訪情況 導管拔出后應隨訪347例(除外導管留置期間死亡7例,發生DVT、PE 3例),其中有13例患者拒絕返院或未接電話而失訪;32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均與靜脈血栓栓塞無關;7例患者在隨訪中自訴有置管側肢體不適感,但經過超聲未發現置管側肢體殘留血栓。其余患者未出現同側肢體的沉重、疼痛、瘙癢、身體受限或感覺異常。
3 討 論
CRT發生原因與輸液導管作為異物留置在血管腔內密切相關,尤其是無癥狀CRT在導管置入后非常常見。但由于相關研究的缺乏,對于無癥狀血栓應如何處理尚缺乏規范意見[2,8]。
對于無癥狀CRT進一步蔓延、引起PE、血栓對導管功能本身的影響和未來發生PTS的擔憂,是支持無癥狀CRT患者采用抗凝治療的理由[9-10]。但是,考慮到很多置管的患者是惡性腫瘤化療患者,不同程度地存在化療相關的血小板減少、腫瘤破裂出血、術后出血等風險,因此對于無癥狀CRT是否需要抗凝治療,不僅涉及治療的必要性,也關乎治療的安全性[11]。
本研究中,35.43%的無癥狀CRT患者在未使用抗凝藥物情況下血栓也可完全消退,僅有7.95%患者的血栓體積出現增大。同時即便對于本研究中歸類于“血栓增大”的患者,仍未發展為癥狀性CRT。分析患者診斷時和導管拔出時血栓體積及D-二聚水平,發現患者導管拔出前的血栓體積和D-二聚體水平均較診斷CRT時降低,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隨訪過程中也僅有1例患者出現無癥狀PE,無一例患者在導管移除過程中出現癥狀性PE。BODDI等[12]研究結果顯示,使用低分子肝素的標準抗凝治療只能溶解50%的CRT。SON 等[13]研究即使使用尿激酶溶解CRT,完全溶解率也僅有50%。國內既往研究針對輸液港相關的無癥狀CRT,也提示抗凝治療并未給無癥狀CRT帶來更優的治療效果[7]。因此,說明對于無癥狀CRT患者,無抗凝治療對患者預后無不良影響,血栓在導管留置的情況下仍有自發溶解、縮小的傾向。
事實上,隨著對靜脈血栓認識的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和指南均建議對靜脈血栓的治療要結合位置、體重進行更精準的分類治療[14-15]。例如2016年的ACCP 10版提出,對于小腿遠端無嚴重癥狀的急性孤立DVT,單純影像學隨訪優于抗凝治療;對于肢體近端無DVT且靜脈血栓栓塞癥復發風險較低的孤立亞段PE,臨床監測優于抗凝治療[15]。《輸液導管相關靜脈血栓形成防治中國專家共識(2020版)》中將CRT根據臨床癥狀劃分為深靜脈血栓、血栓性淺靜脈炎、無癥狀血栓和血栓性導管失去功能,并據此提出了分類處理的建議,且建議對無癥狀血栓只進行觀察隨訪[5]。本研究支持該種處理策略在臨床上是安全有效的,同時本研究也發現,僅有0.96%無癥狀CRT患者的導管在留置過程中出現了導管失去功能,側面支持了無癥狀CRT與血栓性導管失去功能為各自獨立的2種臨床分類類型。
既往認為CRT可能為細菌等病原體提供了附著的位點,從而增加了CRBSI的風險。在本研究中,5例(1.61%)患者出現疑似CRBSI,最終4例診斷明確,整體而言,CRBSI的發病率并不高。對比既往關于CRBSI研究報道的發病率在0.54%~4.60%[15-16],可見CRT并不增加CRBSI發生風險。
本研究選擇導管移除后3個月作為隨訪終點,是因既往指南建議對CRT的抗凝治療應維持至導管移除后3個月[3,17]。本研究顯示,在拔除導管后短期內未見明顯異常,其長期影響尚不清楚。其他研究也表明PTS在CRT發生后似乎不常見[18]。基于此,作者認為無癥狀CRT可能是導管置入后的生理現象,而不是需要治療的病理狀態,采用單純觀察隨訪手段是安全可行的。這一觀念的推廣,有助于降低臨床工作人員對CRT的過度反應心態,避免過度診斷和過度醫療。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其回顧性和橫斷性研究性質,未設置對照組,隨訪時間相對較短,未對凝血功能進行探討。為了更好地理解CRT的管理,以及體現常規超聲監視的真正價值,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因此,對無癥狀CRT患者可能無須進行抗凝治療,但無癥狀CRT發生機制仍需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