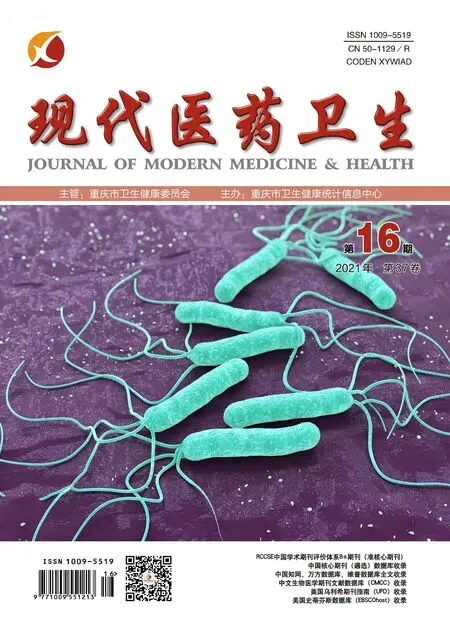移動醫療系統在院前急救重癥患者中的應用研究
衡正軍,方 向,肖春玲
(1.淮安市急救中心,江蘇 淮安 223001;2.淮安市第二人民醫院,江蘇 淮安 223002)
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移動醫療已經進入人們的生活并且可能和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1]。隨著移動通信的不斷發展,移動醫療也逐漸走進了人們的視線,經過近10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移動醫療在醫院內尤其是三級醫院中的應用已經日益普及和成熟,尤其是在2020年年初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移動醫療更是大放異彩。而作者認為,移動通信設備與可在移動狀態下提供醫療支持的設備如自動心肺復蘇(CPR)機等,可統稱為移動醫療系統。移動醫療系統在院前的應用較院內明顯滯后,淮安市急救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自2017年開始應用Zoll X型除顫監護儀,為配合醫院三大中心建設,2018年4月新增移動通信傳輸功能,可以實時向接診醫院急診科、胸痛中心、卒中中心等傳輸患者基本生命體征、心電監護、指脈氧、呼氣末二氧化碳波形圖、12導聯心電圖等信息,做到院前院內無縫銜接。2018年年初本中心開始投入使用新型Zoll自動CPR機100,取代威爾(Weil)CPR機,故本研究以2018年4月作為時間節點,將該節點前后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分析探討移動醫療系統在院前急救中的應用意義及尚存在的不足之處。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1.1.1CPR病例 選取2016年6月至2020年6月本中心(不含急救分站,下同)救治的277例心跳呼吸驟停(CA)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2016年6至2018年4月的151例CA患者作為對照組,2018年5月至2020年6月的126例CA患者作為觀察組。CA診斷標準:院前接診時患者呼吸停止,頸動脈搏動不能觸及,瞳孔散大固定,對光反射消失,口唇蒼白或發紺。排除接診時已出現尸僵、尸斑或顱腦、胸部毀損型損傷現場死亡者,以及家屬放棄搶救已簽署拒絕CPR文件的患者。影響CPR成功率的因素包括患者年齡、有無基礎性疾病、CA時心律類型、是否有目擊者給予CPR、急救反應時間、現場CPR質量、除顫開始時間等[2]。兩組CA患者CPR成功率影響因素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CA患者CPR成功率影響因素比較
1.1.2急性冠脈綜合征(ACS)病例 選取標準、時間及分組同上,總病例數為385例,對照組為178例,觀察組為207例。對照組中男113例,女65例;年齡39~92歲,平均(59.64±9.81)歲;體重指數(27.56±5.25)kg/m2;主訴胸痛53例,胸悶等心前區不適125例;基礎疾病:高血壓104例,糖尿病56例,高血脂63例;吸煙88例,飲酒72例。觀察組中男132例,女75例;年齡37~86歲,平均(59.36±9.14)歲;體重指數(27.72±5.48)kg/m2;主訴胸痛68例,胸悶等心前區不適139例;基礎疾病:高血壓128例,糖尿病69例,高脂血癥80例;吸煙85例,飲酒81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主訴類型、體重指數、基礎疾病、吸煙飲酒史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1.3腦血管意外(CVA)病例 選取標準、時間及分組同上,總病例數為441例,對照組為239例,觀察組為202例。對照組中男155例,女84例;年齡32~89歲,平均(65.94±9.87)歲;體重指數(27.54±5.24)kg/m2;出血性卒中41例,缺血性卒中198例;合并疾病:高血壓178例,糖尿病103例,高血脂82例;吸煙94例,飲酒87例。觀察組中男126例,女76例;年齡35~96歲,平均(67.37±10.05)歲;體重指數(27.82±5.38)kg/m2;出血性卒中27例,缺血性卒中175例;基礎疾病:高血壓108例,糖尿病83例,高血脂75例;吸煙86例,飲酒71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重指數、卒中類型、基礎疾病、吸煙飲酒史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處置方法及觀察指標
1.2.1CPR病例 對照組接診后均立即施行現場CPR,開放氣道(球囊面罩、口咽管),必要時實施心電監護、氣管插管、電除顫、建立靜脈通路、復蘇藥物應用等。觀察組接診時攜帶Zoll X型除顫監護儀、Zoll自動CRP機100、球囊面罩、全套插管設備、復蘇藥物等,并予以心電監護同步傳輸、插管、建立靜脈通路、電除顫,現場放置CPR機。對比兩組CPR成功率。
1.2.2ACS病例 對照組常規給予吸氧、心電監護(心率、血壓、呼吸、脈搏),密切觀察生命體征變化,口服藥物[硝苯地平(心痛定)、阿司匹林、硝酸甘油片等],開放靜脈通路及靜脈使用硝酸甘油、抗心律失常等藥物,必要時行CPR術。觀察組除常規吸氧、監護外,利用Zoll X型除顫監護儀,第一時間行12導聯心電圖檢查,并傳輸至最近有胸痛中心的醫院急診,利用微信、對講機或手機與胸痛中心聯系,并在其指導下,給予心肌梗死患者“一包藥”(阿司匹林腸溶片300 mg、替格瑞洛180 mg、阿托伐他汀片40 mg),以及開放靜脈通路及應用血管活性藥物。觀察兩組院前處置率、院前癥狀緩解率,以及惡性心血管事件(心源性休克、心律失常、心搏驟停等)發生情況。
1.2.3CVA病例 對照組到達現場后立即檢查患者生命體征、意識狀態及伴隨癥狀,予保持氣道通暢、吸氧、監護、血壓監測、測血糖等,開放靜脈通道及應用甘露醇、甘油果糖、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藥物。觀察組中意識清楚的患者予吸氧、監護、對癥處理,與院內卒中中心聯系,利用辛辛那提院前卒中量表評估,考慮為缺血性卒中的提前做好靜脈溶栓準備;意識不清的患者做好氣道管理、吸氧、吸痰、插管,監護并傳輸生命體征數據,規劃并傳送至最近有卒中中心的醫院,開放靜脈通道及應用藥物治療。觀察兩組院前處置率、院前癥狀緩解率,以及惡性腦血管事件(抽搐、腦疝、心律失常、呼吸心搏驟停等)。

2 結 果
2.1兩組CA患者CPR成功率比較 對照組予以心電監護143例,插管14例,建立靜脈通路15例,電除顫14例,2例上車后實施威爾(Weil)CPR機按壓,實施時間分別為52、65 s;觀察組心電監護同步傳輸122例,插管37例,建立靜脈通路33例,電除顫9例,現場放置CPR機19例,于人工按壓5~8 min后實施,操作時間24~42 s。觀察組CA患者CPR成功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CA患者CPR成功率比較
2.2兩組ACS患者救治情況比較 觀察組ACS患者院前處置率、院前癥狀緩解率均高于對照組,惡性心血管事件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ACS患者救治情況比較[n(%)]
2.3兩組CVA患者救治情況比較 觀察組CVA患者院前處置率、院前癥狀緩解率均高于對照組,惡性腦血管事件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CVA患者救治情況比較[n(%)]
3 討 論
院前急救存在環境復雜、病種多樣,緊急性、隨機性強等特點,而院前急救人員臨床經驗不足、專業性不強等,往往制約著院前急救的水平提高。遠程醫療的發展,使醫術高明、經驗豐富的院內醫生能夠指導院前醫療活動,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不斷革新進步,尤其是5G技術的成熟和應用,傳統的互聯網帶寬限制的影響逐漸消除,“one to many”遠程醫療模式的出現,一個醫生或團隊可以同時進行多個醫療活動[3],既可以解決院前急救水平的不足,又可以緩解院內醫生工作時間過長,解決臨床醫生相對不足等問題。但在診療過程中仍可能出現網絡不暢、傳送圖片或視頻不清晰、監測設備失靈等問題,導致無法診斷或誤診[4],準確而有效地收集患者的信息是移動醫療的靈魂,如果沒有準確的患者信息,那么其他都是徒勞無功的[5]。這也提出較多的現實問題:醫療數據的可靠性誰來保證?一旦出現醫療事故,誰來承擔責任?這些問題導致院內指導院前時存在顧慮和擔憂,這也是制約移動醫療系統在院前應用進一步發展的一個因素。
心腦血管疾病具有發病率高、致殘率高、死亡率高、復發率高的特點[6]。有研究指出,心血管疾病死亡已占居民疾病死亡構成的40%以上[7]。2016年全球范圍內因腦血管死亡的人數超過550萬人[8]。因此針對心腦血管疾病的救治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自本中心開展“三大中心建設”以來,淮安市各大醫院急診科通過“智能監護儀、微信群、視頻指導”等方式與本中心展開密切合作。通過兩年多的實踐,效果顯著,具體表現在院前急救重癥患者尤其是ACS、CVA患者的遠程指導率、處置率大幅提高,惡性事件的發生率大大降低,到達急診室后的確診時間大大縮短,患者的救治成功率及預后都明顯改善。即時傳輸的醫療監護系統加上急救人員隨身攜帶的執法記錄儀,一方面可以加強院前院內的銜接,提高患者的救治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重現急救人員在現場的診療搶救過程,不僅能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也為院前急救的質量把控提供了可量化的依據。這也要求院前醫護人員規范搶救流程,不斷提高自己的急救技能水平。
CPR成功率與多種因素有關,而高質量的CPR至關重要。自動CPR機與手動CPR的優劣爭論一直不斷,國外有研究表明:未提示CPR機相對手動CPR能夠提供更好的生存率及神經系統預后[9],也并未提示CPR機和手動CPR相比在4 h生存率和30 d生存率方面有顯著差異[10],但理論上CPR機能夠提供持續高質量的CPR。國內部分急救中心如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采取主要在現場持續復蘇的方法,這需要醫生、醫助(護士)、駕駛員均要有扎實的基礎生命支持(BLS)的基本功,同時要能密切配合,及時開展高級生命支持(ACLS),重要的還要有充沛的體能及患者家屬的充分理解。而大部分急救中心仍采取的是現場CPR一段時間后“邊救邊送”的模式,難免會在轉運過程中如上下樓、上下車等出現較長時間中斷按壓;CPR機幾乎不受轉運因素的影響,各項按壓指標與靜止狀態沒有明顯差異[11]。在放置CPR機后,還可以釋放醫護人員進行氣管插管、開通靜脈通路等操作,提高現場ACLS處置率。老式威爾(Weil)CPR機采用的是氣動模式,使用時需氧氣瓶等氣源支持,存在安裝費時、使用場景受限等缺點,在本中心開展情況不理想。新式的Zoll自動CPR機100采用可充電電池,安裝時間較前明顯縮短,可現場安裝使用,但仍存在機器笨重搬運難、患者固定不牢固等缺點,目前只是初步開展應用。另外,作者不建議在CPR初始的4~6 min內放置CPR機,美國心臟協會建議高質量CPR中斷按壓時間小于10 s,實際操作中還達不到這一要求。
可視化的移動通信設備與加裝了射頻識別(RFID)芯片的診療設備的組合,讓傳統診療設備擁有了“智慧眼+智慧心”。但因資金等因素的影響,院前急救還存在移動醫療設備不足的問題,目前很多還僅限于基本生命體征及心電圖等資料的傳送,理想中的5G急救車可將多功能生理監測儀、超聲機、車載X光、CT機、高清視頻會診等多種設備集于一身[12],真正做到院前與院內實時無縫連接,實現“上車即入院”的愿景。
綜上所述,移動醫療系統在院前急救中的使用,可以明顯提高CA患者CPR救治成功率,提高ACS及CVA患者院前處置率及患者的生存率,降低院前惡性事件的發生率,改善患者的預后,值得在院前急救中進一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