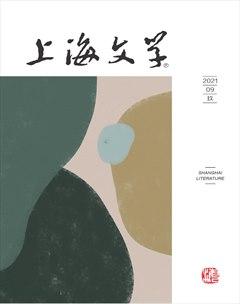樂觀的悲觀主義
吳昊
美國潘通公司作為世界范圍內(nèi)的色彩權(quán)威,每年都會公布一個年度流行色彩,所有制造業(yè)都會將其奉為圭臬推出大量的產(chǎn)品。這里面當然有消費主義的導向作用,但是色彩對于人情緒、心理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細心去觀察這幾年的流行色趨勢,不難探看出“灰度”元素成為了一個關(guān)鍵詞,它造就了煊赫一時的莫蘭迪——那種節(jié)制的消極味道的色調(diào)。
《圓周定律》給我的初步印象就是這樣,由于作者本身就是個知識產(chǎn)權(quán)律師,這種代入感是很真切的,你甚至會在結(jié)尾想起“農(nóng)夫與蛇”這樣的經(jīng)典主題。這是一部典型的談?wù)撊诵缘男≌f,一個初涉人世的菜鳥律師不幸遭遇“民科”老油條的欺騙,本想著交心沒想到被反咬一口的俗套設(shè)計。然而“農(nóng)夫與蛇”的本質(zhì)是對人性的徹底的不信任,《圓周定律》只是看著像而已,但作者卻“滿懷深情”。三三的文字便是這般,初看像韓非,近看才識得那是荀卿。
三三自言是一個有“好奇心”的人,我們不妨把小說中“我”與任天時的通信看做一種自我對答,執(zhí)筆人是作者,信的彼端也是她自己。“我”在生活中很冷淡,對于同僚的日常調(diào)侃提不起興趣,就連和男友之間的互動也談不上親密,然而在寫給素未蒙面的被告任天時的信中,“我”的打開程度是空前的,可以談?wù)劻钊瞬粣偟谋狈綒夂颍只蛳蚰吧朔e極地介紹自己的履歷,甚至對于“民科”狂熱的執(zhí)念也表示由衷的感佩。這種激烈的表達,在冷靜克制的全文中顯得尤其突兀。再看任天時的回信,那就是理想主義到了極致,那種極具表演人格的形象躍然紙上。這是一種戲謔的耦合,一面是自己也無法描述自己的新人律師,另一面是妻離子散不被理解的“民科”,他們居然在官司之外成了精神信友。
法律是一種尺度,是衡量文明社會中人類最低行為標注的底線。它自身的強制性或者他律性,實質(zhì)上是在鞭策人類激發(fā)自我的自律性。所以說任天時對“我”的背叛,其實不正確,他并沒有背棄自己的“理想”,他成功地用自己的努力換來了好奇的探尋,換來了一個忠實的粉絲,換來了和解的賠償,改善了自己的窘境。我也不覺得小說中的“我”被辜負了,那是本雅明式的爬到沉船頂端試圖發(fā)出的“求救信號”,這種試圖將自己從孤絕中拯救出來的嘗試雖然失敗,但并不會止息。書信的一來一回及其最后的毀滅,我看到的是依賴他律的“我”最終看到“茫然、虛幻的面孔”,然后結(jié)成自律的“我”并未落淚。
這或許印證了三三在創(chuàng)作上的某種意圖,像馬爾克斯一般冷眼旁觀,早已洞穿一切本質(zhì)的道理與結(jié)局,展現(xiàn)一種極端而又節(jié)制的哀傷。在前面我也提到了,《圓周定律》給人的第一觀感可能有些簡單,設(shè)計感或許有些強烈,“民科”任天時最后的行為,或許早已經(jīng)被“我”洞見,然而“我”還是會試圖將局做下去,這讓人會不由得質(zhì)疑“我”的動機,與周遭眾人的接觸真的會如此艱難,為何一個陌生且有知識代差的“民科”反而可以卸下防備。三三所需要加強的合理性,其實是需要把握自身對于社會體認的自信,或許再加上一點點的不自信和不徹底,這個故事會顯得更加圓融。
對生活的深情并不需要那種高亢的調(diào)子,也不盡是罪與罰的變奏。宣泄的途徑不同,色彩也可以加上灰度。三三“悲觀”的自我表述更接近于海底的休眠火山,雖然最終會被海水覆蓋,然后遮掩不住對于生活的熱誠,與對他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