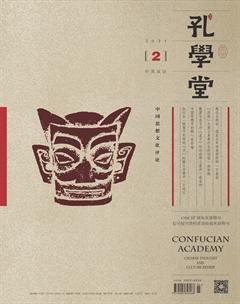“物勒工名”與傳統工匠精神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手工業的發展和“工商食官”制度的衰落,使“物勒工名”作為一種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新的手工業管理制度應運而生。“物勒工名”在秦漢時期臻于成熟,它不僅有比較完善的法律和工官制度,而且有嚴格而完整的監督管理體系。漢代以后,“物勒工名”作為官營手工業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盡管在不同朝代的具體實施情況略有不同,但一直綿延不斷。直至清末,隨著官營手工業的衰落,這項制度才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物勒工名”不僅是傳統手工業生產質量的保證,而且是傳統工匠精神形成與傳承的制度保障。
關鍵詞:生產分工 ?物勒工名 ?手工業 ?監管制度 ?傳統工匠精神
作者梅其君,貴州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貴州 ?貴陽 ?550025)。
所謂“物勒工名”就是在手工業產品上鐫刻或用烙印、模印、戳印、漆書、朱書等方式標記上“工”的姓名,這里的“工”不僅指工匠,還包括監工、工匠所屬機構等。“物勒工名”是中國古代官營手工業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這項制度始于春秋戰國時期,而終于清朝。在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中,這項制度對中國傳統手工業生產和技術進步起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也保障了傳統工匠精神的傳承。
一、“物勒工名”的濫觴 [見英文版第66頁,下同]
“物勒工名”是從器物上鑄刻“銘文”演化而來。商代的青銅器上就已經出現了銘文,銘文主要是對祭祀內容、土地制度變化、戰爭、禮儀制度、官職名、計時法、邦國關系、音律以及一些大事件進行記載。商代青銅器銘文很短,出土文物中超過十字者也不過百件。到了周代,青銅器銘文內容日益豐富,包括徽記、祭辭、冊命、訓誥、記事、追孝、約劑、律令、媵辭、樂律、符令、節令、詔令、工名等。其中,“工名”就是工匠、監工等的姓名。不僅青銅器上有銘文,陶器、漆器等各種器物上也有銘文,“物勒工名”也反映在這些器物的制作上。
從文獻記載推斷,“物勒工名”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禮記》和《呂氏春秋》對“物勒工名”都有記載。《禮記·月令》記載:“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鄭玄注:“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禮記》是孔子及其弟子闡發禮儀的經典,這說明“物勒工名”可能萌芽于春秋時期。稍后的《呂氏春秋·孟冬》也有類似的記載:“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這段文字與《禮記·月令》的描述基本相同,只是少了一個“命”字,“毋或”寫作“無或”,“功有”寫作“工有”。《呂氏春秋》成書于戰國晚期,這說明至少在戰國時期,“物勒工名”制度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
從考古發現看,“物勒工名”最早出現在春秋時期的齊國。春秋中晚期齊國青銅酒器國差上刻有“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攻師鑄西墉寶”的字銘,這是目前發現最早記錄了工師(攻師)的銘文。春秋晚期齊國的陶器也出現了“工名”,但總體上看,春秋時期的題銘主要還是“銘功紀德”,“物勒工名”只是個別現象,齊國制陶業的“物勒工名”也是在戰國時期才比較普遍。齊國陶器上所勒“工名”主要是監造者,也有記陶工名的。官營制陶業常見的勒名格式是“某某立事歲+司職地點+器名”或“地名+立事者人名+立事及屆數+陶工名”;私營制陶業常見的勒名格式為“邑里+姓名”。“立事”即“蒞事”,指器物的督造者。在簡省格式中,“立事歲”字樣又常常省略。
“物勒工名”在戰國時期已不局限于某國和某一行業。楚國的漆器制造業較為發達,其管理制度完善,“物勒工名”也比較典型。楚國漆器上的銘文主要內容包括制造機構、主管官吏和制器工匠,常見的勒名格式主要有“產地名+制造機構+制器工匠”“時間+督造者+監制者+制器工匠”等。如長沙三眼塘楚墓出土的一件漆卮上所刻銘文為:“甘九年,大(太)后□吿(造),吏臣向,右工幣(師)象,工六人臺。”涵蓋了該漆器的制造時間、主造者、監造者和制造者。三晉冶鑄業發達,“物勒工名”制度在韓、趙、魏三國的兵器鑄造業上體現得很充分。三晉兵器勒名格式因年代和國別而有所不同,基本格式由三級組成:“督造者+主持鑄造者+制造者”。督造者稱為“令”“相邦”“守相”“司寇”“邦司寇”等,為掌政者;主持鑄造者稱“工師”“冶尹”或“左右校”;制造者稱“冶”,即工匠。詳細的勒名還包括時間、地名和庫名。秦國自商鞅變法后開始實行“物勒工名”制度。早期的勒名只反映了督造官吏的信息,如上海博物館商鞅方升上的銘文:“十八年,齊?(率)卿大夫(合文)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愛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重泉。”到了秦昭襄王時期,勒名內容已擴展至工師以及工匠的姓名,如出土的一私官鼎上所刻銘文:“卅六年,工幣(師)瘨。工疑,一斗半正,十三斤八兩十四銖。”到了戰國末年,秦國的勒名內容更加詳細,如出土的“少府”戈上所刻銘文:“五年,相邦呂不韋造。少府工室阾丞冉、工九。武庫。”“相邦”即丞相;“少府”為秦國官名;“工室”即“考工室”,隸屬“少府”;“阾丞”即掌管“少府”的“令丞”。勒名格式的變化反映了秦國手工業管理制度日趨完善,主管機構上至中央丞相,下至少府、工室,層層相扣,各司其職,為產品生產質量提供了保障。
“物勒工名”的出現與春秋戰國時期手工業的發展密不可分。春秋戰國時期的手工業發展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階段。一方面,原有的技術進一步發展,技術更成熟,工藝更復雜。例如,青銅制造技術由早期的合范或一面平鑄法的單一鑄造方式,發展到混鑄法、分鑄法、失蠟法以及各種熔鑄、合鑄、接鑄、嵌鑄工藝的綜合運用。另一方面,隨著新技術的發明,手工業部門進一步增加。例如,隨著冶鐵技術的發明和進步,冶鐵和鑄造鐵器的手工業部門出現了,并且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越來越重要。《考工記》記載:“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筑、冶、鳧、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鐘、筐、?;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這段描述表明,春秋戰國時期的手工生產日益多樣化,生產技術日益專門化,分工越來越細,完成一件手工產品往往需要多個工種的配合。這就需要一種監管制度來保證產品的質量,當發現質量問題時,能有效地追究責任,“物勒工名”應運而生。
“物勒工名”的出現還與“工商食官”制度的衰落密切相關。“工商食官”是商周時期國家對工商業進行管理的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百工”以家族的形式為王公貴族服務,職業世襲,而國家則利用家族內部血緣關系對從事手工業的勞動者進行管理。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國家權力下移,宗法制度遭到破壞,血緣凝聚力減弱,統治者無力維持龐大的“食官”體系。原來依附官營體制而生存的工匠生存困難,不斷反抗。例如,《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記載生存困難的工匠卷入周王室的權力爭斗:“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這說明,“工商食官”制度已難以維系,依靠血緣關系對手工業進行管理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發展需要一種新的手工業管理制度。“物勒工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二、“物勒工名”的發展 [68]
“物勒工名”制度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首先,從實施范圍看,“物勒工名”在當時手工業生產的各個部門中普遍推行。除了上文提到的秦國的度量衡器、禮器和兵器制造實施“物勒工名”制度外,其他行業,如陶器、漆器、銅器、鐵器乃至秦始皇兵馬俑的制作都實行了“物勒工名”。
其次,從勒名格式看,“物勒工名”的內容更加明確。例如,兵器制造必須刻有鑄造時間、主管部門、督造官名、工師名、工匠名等,如果工匠身份為刑徒,還要刻其所受刑罰名稱。《工律》甚至還有勒名方式的規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書之。”意思是兵器不能刻記的,也要用丹砂或漆來書寫。
再次,從法律和配套制度看,“物勒工名”制度更加完善,不僅“物勒工名”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與之配套的管理制度也有明確規定。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墓文物中有很多法律類的竹簡,例如《效律》《秦律雜抄》《工律》《工人程》以及《均工》等,都清晰記載了秦朝嚴格管理手工業生產的制度。《效律》記載:“公器不久刻者,官嗇夫資一盾。”意思是未按要求勒名的工匠要受到相應處罰。《效律》還詳細規定了一些核驗制度,《秦律雜抄》對工匠不認真檢查材料有處罰規定,《工人程》《均工》對官營手工業生產定額有規定,以“物勒工名”為核心的一整套手工業管理制度,從物資保管、生產監督到產品檢驗,在秦王朝已經基本上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
漢承秦制,漢初主要沿用秦朝的“物勒工名”制度。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后,“物勒工名”制度在秦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西漢昭帝到東漢章帝時期,“物勒工名”制度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東漢中后期,中央集權弱化,國家放松了對手工業的控制和工官機構的管理,“物勒工名”制度開始松懈。
“物勒工名”在漢代的手工業特別是官營手工業生產的各個部門中普遍推行,勒名器物的種類、數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考古發現看,銅器、漆器、鐵器、陶器、兵器、金銀器、度量衡器、磚瓦、錢范、石刻、書寫工具等都有勒名。其他手工產品也可能勒名,但由于保存困難,尚有待考證。
漢代的勒名格式因生產機構、器物種類、制造年代的不同而有較大差異。官營手工業勒名一般比較詳細,而私營手工業器物勒名比較簡單,一般僅刻工匠名或作坊姓氏,也有刻籍貫、紀年和吉祥語的,具有廣告推銷的性質。不同種類的器物勒名不一樣,有的器物勒名比較詳細,如宮廷所用的漆器、青銅器;有的器物勒名比較簡單,如日常所用的陶器、鐵器。不同時期的器物勒名格式也不一樣。繁榮時期官營手工業典型的勒名格式是“紀年+器物名稱和規格+工官名+諸工匠名+諸監造官吏名”,具體勒名內容的順序可以變換,如“器物名稱和規格”可以放在“紀年”之前,也可以放在“工官名”之后,還可以放在最后;“諸工匠名”也可以放在“諸監造官吏名”的后面。漢代器物勒名內容比以前更豐富,“監造官吏名”包括各級官吏負責人,“工匠名”包括每道工序的負責人。如貴州清鎮出土的一件漆耳杯上刻有銘文:“元始三年,廣漢郡工官造乘輿髹羽畫木黃耳杯。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髹工立、上工階、銅耳黃涂工常、畫工方、羽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護工卒史惲,守長音,丞馮,掾林,守令史譚主。”該漆耳杯為西漢平帝時廣漢郡工官為皇帝制造的,這段銘文不僅刻有各級監督、主管負責人姓名,而且刻有每道工序負責人姓名,責權更加明確,也反映了漆器制造的工藝流程與具體分工。又如,山西洪洞縣出土的一件銅鼎上刻有銘文:“安邑宮銅鼎一,容三斗,重十七斤八兩。四年三月甲子,銅官守垂調,令史德,佐奉常,工樂造。第卅一。”這段銘文除了有器物的名稱、容量、重量、制造時間、工官名、諸監造官吏名、工匠名外,還有器物編號,并且反映了該鼎的鑄造機構為漢代中央在地方郡縣設置的銅官。銅官是漢代中央政府根據手工業門類的不同而設置的專業性工官。類似銅官的這種專業性工官在漢代最為常見,它與綜合性工官一起構成漢代的工官系統。這套工官系統對官府手工業的管理有兩種:一是由為皇室管理私財和生活事務的機構“少府”所屬的考工、供工、右工、尚方、內者等機構直接對手工業進行管理;二是地方工官所屬的令(長)、丞、掾、史(令史)、佐等各級管理人員以及郡守派遣到工官進行督察和監視的護工卒史等官吏對手工業進行管理。器物勒名的詳細內容就反映了這種管理體系的嚴格和完善。
可見,“物勒工名”制度在秦漢時期已經比較成熟,它不僅有比較完善的法律和工官制度,而且有嚴格而完整的監督管理體系。“物勒工名”在官營手工業生產中普遍推行,使勒名器物的種類、數量都達到了歷史高峰,并逐漸向民間延伸。
三、“物勒工名”的沿襲 [69]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政權更迭頻繁、長期封建割據和戰爭連綿不斷,官營手工業發展的側重點與和平年代不同,兵器、農具、城建器具等在官營手工業中最為發達。除了兵器、度量衡器等政府重點把控的器物依然嚴格勒名外,其他器物勒名一般都比較隨意。兵器的勒名格式與秦漢時期大同小異,如四川郫縣出土的蜀國弩機上刻有銘文:“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興業,劉純業,史陳深,工楊安作十石機,重三斤十二兩。”其勒名格式是“制造時間+主管機構及官吏名+工匠名+器物規格”。又如南京石門坎出土的曹魏弩機上刻有銘文:“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監作吏晁泉牙匠馬□,師陳耳臂匠江□聶□。”其勒名格式是“制造時間+主管機構+監督官吏名+具體工匠名”。其他器物也有勒名,如銅鏡、磚瓦。北朝時期的筒瓦與板瓦上刻劃或戳印的文字,多是匠人名氏,這是“物勒工名”傳統的延續。
隋唐五代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物勒工名”較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恢復和發展。以唐代為例,國力強盛的唐朝政府設立了多種不同層次的機構,直接經營、管理著門類眾多的手工業生產,形成了十分龐大的官府手工業系統。“物勒工名”則是官府手工業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尤其是在兵器生產上。《唐六典》規定:“凡營軍器,皆鐫題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閱其虛實。”《新唐書》也記載:“軍器則勒歲月與工姓名。”因行業、器物的不同,隋唐的器物勒名內容有繁有簡。與“物勒工名”相配套的處罰措施,唐代法律也有明確規定。《唐律疏議》記載:“輒違樣式,有不如法者,笞四十。……親監當造作,若有不如法,減工匠三等,笞十。”工匠必須嚴格按照工程質量標準生產或施工,如果工作不達標,就會受到相應的處罰,上級監管人員也要跟著受罰。
宋朝的官營手工業依然實行“物勒工名”制度,如作為中央官營手工業機構之一的少府監對工匠的考課:“庀其工徒,察其程課,作止勞逸及寒暑早晚之節,視將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官營建筑工程明確要求,工匠完工后必須題寫自己的姓名和施工年月,景德三年(1006)詔:“自今明行條約,凡有興作,皆須用功盡料。仍令隨處志其修葺年月、使臣工匠姓名,委省司覆驗。他時頹毀,較歲月未久者,劾罪以聞。”至于官府所掌控的兵器生產,其勒名及管理則更加嚴格:“所造諸色軍器,各行鐫記元造合干人、甲頭姓名”,“刀紉、鐵甲鐫鑿,弓弩箭之類用朱漆寫記”。民間手工業生產也有勒名,如私刻或坊刻宋版書,版心下方往往標注刻工姓名;又如銅鏡,宋代鑄鏡中心湖州生產的銅鏡上常常有諸如“湖州石家法煉青銅照子”“湖州李家煉銅照子”之類的字銘。民間手工業生產的勒名是為了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提供質量擔保,也起到宣傳產品的作用。
元代的官營手工業盡管規模龐大,管理機構也十分復雜,但關于“物勒工名”的史料記載闕如。不過,從出土文物看,“物勒工名”制度依然可以窺見。例如,故宮收藏的三彩龍蓮紋香爐上刻有“至大元年汾陽琉璃待詔任塘城造”的字銘;山西平遙縣東泉鎮百福寺的琉璃寶頂上刻有銘文:“介休縣張元村琉璃待詔張琳男仲祥,延佑三年六月造”;元大都考古發掘出土的排水溝渠石板上刻有“致和元年五月×日石匠劉三”的字樣。可見,“物勒工名”制度在元代依然在延續。
明清是我國古代手工業發展的高峰時期,但官營手工業的經營范圍與前代相比已經縮小。為了保證工程質量,官營手工業依舊采用了“物勒工名”的制度。明代的城磚制作是這一時期“物勒工名”的典型,如荊州城洪武年的城磚上勒名:“荊州府潛江縣提調官縣叢張銘、司吏蔡銘;監工人王興禮、張興,作匠陳文,小甲譚友德,人夫談茂原,洪武十三年×月×日。”明代中葉以后,官營手工業開始走下坡路,而民間手工業則發展迅速。民間手工業生產也有勒名,但這種勒名主要是顯示品牌,江南地區的一些工匠漸漸擁有自己的品牌和社會名望。清代官營手工業繼續衰落,其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進一步縮小,而民間手工業則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鴉片戰爭后,官營手工業陷入重重困境,最終被民間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生產所取代。隨著官營手工業的衰落,“物勒工名”制度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四、“物勒工名”對傳統工匠精神的影響 [72]
作為一項制度,“物勒工名”不僅是傳統手工業生產質量的保證,而且在傳統工匠精神的形成與傳承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傳統工匠精神的核心是“精益求精”“敬業專一”。《詩經·衛風·淇奧》中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詩句,“切磋琢磨”就是指工匠們把骨頭、象牙、玉石、石頭等加工制成器物的動作和方法。《爾雅·釋器》解釋為:“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朱熹進一步解釋:“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描述了制作骨角牙器、玉器、石器的工匠的工作狀態與精神面貌,這種工作狀態與精神面貌也是其他高質量手工產品得以產生的最佳描述與概括,因而成為工匠精神的核心內容。“敬”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動,《禮記·少儀》載:“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祭祀活動中“敬”后來逐漸演化成一種美德,《左傳·文公十八年》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兇德。”“敬業”一詞出自《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敬業”原指對待學業的態度,后擴展到對待職業的態度。朱熹注:“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敬業專一”就是以敬畏、專心致志的態度對待自己的職業。對古代工匠而言,“敬業專一”雖然是社會歷史環境中不得已的選擇,但也是成就其精湛技藝的必要條件。“精益求精”“敬業專一”的工匠精神實質上是一種職業操守,它的形成與傳承都與“物勒工名”制度密切相關。
首先,“物勒工名”促進傳統工匠精神的形成。精神的形成無非是作為精神主體的人的內在心理、認知、情感與其外在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傳統工匠精神也不例外。“古代‘工匠精神本質上來說是由兩種路徑共同促成的:一是由官府、行會、作坊等社會環境和傳承方式所形成的‘外化路徑;二是工匠這一職業群體對上古‘圣人創物之道的內省心理而造就的‘內化路徑。”“外化”路徑和“內化”路徑對工匠精神的形成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外化”路徑中的關鍵因素就是“物勒工名”這一制度。“物勒工名”對工匠而言是一種外在的約束和壓力。在這種約束和壓力的作用下,工匠們必須對自己的產品質量負責,因而不得不認真勞作、精益求精。久而久之,這種外在的約束和壓力就形成一種文化氛圍,并逐漸轉化成一種自覺的意識與行為。如果沒有這種外在的約束和壓力,沒有一種有效的監管制度,工匠也許會出于誠信或自我實現的動機而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精益求精,但更多的是會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產品質量無法保證,偽劣產品泛濫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物勒工名”是傳統工匠精神傳承的制度保障。如前所述,在“工商食官”制度下,工匠以家族的形式為王室和貴族服務,國家并沒有破壞這些工匠家族內部的血緣結構,而是利用了這種血緣關系對他們進行管理,因此,生產活動的組織、產品質量的保證和工匠精神的傳承都是靠家族血緣關系來維系的。“工商食官”制度瓦解后,以家族為單位的生產組織與服務方式被打破,工匠的流動性增強,家族血緣關系對工匠的約束削弱,傳統工匠精神的傳承需要有制度上的保障,這個制度主要是從秦漢一直延續到明清的“物勒工名”。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看,傳統工匠精神的傳承是一種持續的社會化心理活動行為,也是一種工匠文化的傳承。文化的核心是制度,傳統工匠文化的核心是“物勒工名”制度。正是這一制度的延續,使得傳統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雖歷經朝代的更替和社會的變遷卻仍得以傳承。一旦“物勒工名”制度消失,建立在該基礎上的傳統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也難以為繼。當代工匠精神之所以衰微,原因很多,但最根本原因還是建立在“物勒工名”制度基礎上的傳統工匠文化已不復存在,而新的工匠文化又沒有形成。
最后,“物勒工名”從官方向民間衍生,從“被動勒名”向“主動勒名”發展,這說明這種制度所蘊含的價值取向和倫理規范得到了普遍認可。從“被動勒名”向“主動勒名”的發展過程也是工匠“個體認知結構在接納、過濾與整合外部工匠文化刺激而形成新的認知結構的同化過程”,這說明在認知層面,工匠精神的職業道德心理構成有了堅實的基礎。這種職業道德認知會促進職業道德情感的發展,并通過職業道德意志的調控,引導產生職業道德行為,表現為工匠在工作中排除干擾、克服困難、抵制誘惑而執著于產品質量的精益求精的行為。民間品牌的樹立實際上是工匠精神不斷踐行的結果。
盡管工匠精神是近年來學界的熱門話題,但學界對中國傳統工匠精神的研究仍然不夠,尤其是對傳統工匠精神的形成機制缺乏合理的解釋,以至于有人認為,在輕視工匠活動的文化氛圍和工匠社會地位低下的中國古代并不存在所謂的工匠精神。梳理“物勒工名”制度的演化,能夠為中國傳統工匠精神的形成及傳承提供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盡管當今已不可能照搬古代“物勒工名”的做法,但“物勒工名”制度之于工匠精神的意義,仍然能夠為我們培育工匠精神所進行必要的制度建設提供一些借鑒。
(責任編輯:陳 ? 真 ? 責任校對:羅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