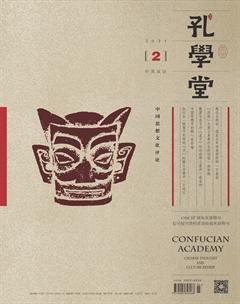此心光明,則諸惡潛消
摘要:陽明學說以“心即理”“致良知”為核心論題,強調知行合一,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格。但是,它也必須面對從心所生發出來的惡以及去惡的問題。陽明所言之惡,不能歸咎于外在的“習”或“物”的浸染干擾,而是源于人心私意私欲的遮蔽。是心之所發之意偏離良知,即私意遮隔本心,呈現為“軀殼起念”或“分別善惡”。其根源則在于將知行二分,導致心之發用背離良知本體。就其本質而言,惡作為一種狀態,并不具有本體論意義,僅具有現象學意義。惡由意念所起,在知行合一的框架中,陽明主張致良知即去惡,通過立志克己以“誠其意”,以使人無蔽于私意私欲。縱觀陽明的全部生命歷程,存在著由強調“意之所在”的存理去欲到重視“明覺感應”良知心體本身的彰顯的去惡路徑的轉變,但“有”“無”之間即體即用的關系是一以貫之的。去惡之依據不在外物,而在于人心本身。此心光明,則諸惡自然復返,是陽明對善之價值的肯認與堅持。
關鍵詞:惡 ?意之所在 ?明覺感應 ?致良知 ?王陽明
作者王進文,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湖南 ?長沙 ?410083)。
儒家哲學并不以邏輯思辨為勝場,而是將價值重心放在實踐上,通過實踐來彰顯其價值。陽明學說強調知行合一,充分彰顯了儒家哲學的實踐性格。縱觀陽明之生命歷程,“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50歲之后,“始揭致良知之教”,以“心即理”“致良知”為核心論題,展開了一個全新且豐富的義理體系。“蓋良知之在人心,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陽明一方面繼承孟子“良知良能”之說,肯定良知是真實存在而非假定的,使心學范疇更為精確與清晰。另一方面,在延續宋代“心即理”的理論和經學主張的基礎上,他進一步闡明“人心與物同體”,人和萬物之心體相同,天地萬物有其昭昭之天理,心之靈明原本也是心體光明,存在著成圣為圣的本質,此即龍場所悟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陽明主張心即理,心體本身純善無惡,是成圣的根據,與此同時,他也必須面對從心所生發出來的惡的問題。四句教中“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即表明善惡出現在“意”的環節之上。心通過“意”發動,便不免有“不善”出現的可能。陽明有關惡的理論在為晚明以降儒者對相關議題的反省提供豐富理論資源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歧義與爭議。為何在心即理、至善是心之本體的前提下,與善對立的惡往往被視作無實體性或無根源的存在?惡的內容究竟為何?其來源又是什么?當人呈現出怎樣的意念或行為時,可稱之為惡?惡與善有著怎樣的內在關聯?前述種種都是我們在探討陽明思想中的惡時不能回避的問題。
一、惡為私意對良知的偏離 [見英文版第75頁,下同]
陽明主張“心即理”,“吾心即物理”。“心”與“理”的定位俱在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聯系到陽明所言之“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即是良知本體的發用,那么,良知本體的發用何以成“惡”呢?
(一)惡生于性之蔽 [75]
牟宗三先生以經驗心理學方式理解陽明雜糅善惡之意,以為心體本體自無不善,但意之有善惡乃因私欲氣質阻隔心體,“心之自體是如此,然其發動不能不受私欲氣質之阻隔或影響因而被歪曲,因此‘有善有惡意之動。其發動即得名曰‘意。故‘意可以說是經驗層上的”。不過,這種闡釋將惡之產生純粹歸結為外部因素,似乎與陽明論學之主旨不符。
陽明弟子徐愛曾經請教吾心即是物理如何可能的問題,對話如下:
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徐愛所發之問,大致是承襲朱子格物窮理而來。格物窮理之理是“理一分殊”之理。在理一分殊的語境中,陽明良知所知的是理一之理,理一之理明白,則分殊之理自然明白,每個人都可以憑借良知回到心的本然狀態,“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于孝親的心……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后有這條件發出來”。因此,在陽明看來,有此心自然能夠知理,以心知理,并非“心”能不能而是為不為的問題。
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
在陽明看來,“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人之本心能夠使人視、聽、言、動,所以有不需通過格物窮理而“一點靈明”“感應之幾”的本能,這一點靈明就是天地萬物之本體,也就是天理。人心與萬物有相同的本心本體,從而,人的良知即是心之本體,人便能夠明理、明道、明德。雖然心之本體即是良知,良知恒照,但人也無法做到時刻彰顯良知。由此,即便欲矯正程朱性即理之主張,他也無法忽略人可能因稟賦差異而導致“私欲遮隔”本心的情形。“惡安從生?其生于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就表面而言,惡來自性所寓于其中的氣質對心之遮蔽。氣質或因承繼而有,或因后天之社會風習熏陶而來,或為教育塑造而成。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人不能對氣質進行選擇,私欲則不然。陽明主張人性乃一,是普遍的,而氣質是私人的,具有差異性:“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然其為性則一也。”私欲即私意,指的是人在倫理中的意欲,例如,意欲為盜即有盜竊之心。人欲是意識層面的意向與思慮,表示人之“意”所趨向,有其主觀的理解與取舍,歸屬于心的范疇,但又不是本心,而是在個體的人所具有的差異性之中所表示的欲求、期望、判斷等。由此,私欲之所以為惡,便是人因相關差異性而造成的對本心的遮蔽,換言之,即私人性的意向阻礙了普遍人性的彰顯。
但是,在強調以良知為價值根基的心學體系中,私意或私欲為何具有可以遮隔本心的能動性?人因良知而具有善之本質,為何陽明天泉證道時還要強調“有善有惡是意之動”,要有“為善去惡”的工夫?
(二)“軀殼起念”與“分別善惡”俱為心之所發之惡 [76]
知行合一是陽明學說的核心主張,良知是凌駕于任何經驗與念慮之上的價值標準,良知的發動不僅包含了對道德價值的認知,也是道德行動的動力來源。當良知應事接物而發出好善惡惡的意念時,人能依此“一念(之)知好善惡惡”。因此,必須承認的是,現實中的諸多情念意欲,于人而言是無法回避的,惡也是心之所發的一部分。在與弟子薛侃談論“去花間草”的內容時,陽明有如下闡釋:
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
“意”的生發場域“凡應物起念處”,即良知與外物相交感之處。在陽明看來,能生好惡之“心”已非本體良知,而更近于心之所發之私意、私欲。“汝心好惡所生”之善惡便是人以私意、私欲對外在事物的判斷。具體而言,花與草都是客觀存在之物,因人的判別而有花草名稱的不同。對于花草而言,名稱之別乃是我們“隨軀殼起念”的私念私意動氣于外的結果。因此,由心所決定好惡的狀態為“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與之相對,“無善無惡者理之靜”,當心體之發用不是著意于人自身(主觀的)私意私欲之好惡,而是依循于理即良知進行判斷時,便是無善無惡。如果意念不循心體本身而發,便表現為“著意”“作好作惡”,此時,便是“動氣”,“便是惡”。由此,我們可以說,陽明以私意發用、著意造成氣的擾動來定義“惡”。換言之,陽明所言之惡,不是一種與至善相對的存在,而是由心之所發之私意私欲著意于物的狀態。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陽明認為無論是“私念”抑或“好的念頭”,只要一有留滯,便構成對人之良知的障蔽:“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前者不難理解,但為何“好的念頭”亦復如是呢?學者錢明曾精辟地指出,“意”在陽明學說中具有“誠意”與“私意”之分的“二重性”,即由良知自身所發的意念乃是純善無惡的“誠意”;但當任何意念有所“留滯”,離乎良知自身掛帶“別念”而在心中存在“人為”的意思時,便會有所偏失而淪為“私意”。良知原本呈現好善惡惡之用,但如果一味著意于好善惡惡,心中有所掛念,則勢必造成以內心主觀好善惡惡的判斷迎合甚或取代天理良知的情形,這與良知所要求的廓然大公之心背道而馳。在此,筆者認為需要補充的是,雖然人對天理并非無所思慮,而只思只慮天理,在陽明看來便是所謂的“何思何慮”。人思慮天理只是復其本來的體用,而非私意安排思索,否則就不是廓然大公,故而陽明又言:“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雖然著意為善有淪為“用智自私”的可能,但陽明致良知之教仍然重視這一工夫,例如,陽明認為:“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由此可見,無心為善與有心為善在不同層面均為陽明所肯認。
除此之外,“分別善惡”也是惡的一種表現。“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陽明認為,人有七情是自然的,如果七情自然發用即循理而發,便是良知的彰顯,便無處不是良知,無處不是天理流行;但如果“有所著”而“分別善惡”,便意味著個人在分別之心的造作下對自然情感進行劃定,并賦予其不同層級或位階的價值,七情就會成為私欲,進而成為良知之蔽。因此,個人主觀的“分別善惡”也因有違“順其自然之流行”的良知而成為一種惡。
綜上可知,陽明所言之“惡”,應是泛指心之所發的根源不是循理,而是因私意“軀殼起念”導致的執著于物的狀態,或心之所發之意著意于情感所導致的以個人主觀價值定義善惡的情形。
二、惡源自知行不能合一 [77]
如果我們重新檢討“有善有惡意之動”,心之所發之意為循理而發時,意便是天理流行,是為有善;反之,則是有惡。不過,若對陽明所論之惡之考察止步于此的話,尚無法回答良知為何會被私欲私意所遮蔽的問題,即惡之來源尚存疑慮。
聯系到陽明在薛侃請教“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的問題時即以“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來批評——薛侃把善與惡看成可由人隨己任意而定者,可由人自行選擇確定何者為善何者為惡,才會有前述疑問。軀殼是私人的,軀殼之說把善惡看成具有純粹私人屬性的存在,“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隨己意所定之善惡,是相對于私人而言的,但人之善惡不是隨己任意界定的,因為在人所組成的社群當中,人與人之間都是主體間性的存在,善惡之界定便不應完全以私人屬性而論,不可孤立地從軀殼所起之念界定,否則人人所持之善惡皆由己意界定,無復良知天理存在,而是必須與心之本體相關,此即陽明所持之善惡一物說,“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心之本體乃是至善,這是一種人皆有之的普遍與定然的善,惡不是這一至善之外的另一種獨立存在之物,只是人對普遍與定然的善的偏離過當。在陽明看來,惡之所生處,即是人偏離或過當于本心的普遍與定然的善而已,其根源在于知行不能合一。因此,我們對惡的辨析,便有必要回到陽明所主張的知行合一的原則上來。
在心學傳統中,“知”作為良知之知,其普遍性是不被懷疑的,故而陽明引用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上》)進行說明。孟子所言良知,乃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道德先驗能力。良知之知即指知理,知是非,“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良知在陽明思想中占有本體的位置。良知既是本心,又是本體,既是萬有的存在根據,又是能活動的創生形而上實體。陽明既以良知等同天理,那么,知天理,知是非,以辨善惡,便是良知之知。陽明所引孟子之說,揭示了人在知愛其親中已有愛之行,也就是說知中蘊涵了行的態度,不是知之后再決意如何行,此即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良知之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知與行本源地為一,乃善的最高根源。人為地將知行分開為二,便造成對善的偏離過當。因此,前述私欲私意之根由,乃在于人對知行關系認識的偏差。具體而言,善為知行合一,惡即知行為二,后者乃基于心的自主之意的發動而偏離本心。那么,這種偏離本心的心之發動,是不是人的一種自我決定?私欲私意是對本體“何思何慮”之偏來說的,是人之“好色、好利、好名”等“閑思雜慮”之根。若非人自主地接納、承受,私欲私意便不足以決定人;只有在人的自主之意的縱容之下,它們才有發揮作用的空間。經此一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惡之來源乃生于人有主意地以其私欲私意遮蔽本性而將良知之知行二分。
陽明以知行合一之旨,揭示本心之蔽之所以為惡,在于割裂知行。“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學必須實踐其所學,否則,將窮理與行分開,是學而不行,“知行之合一并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陽明將知行二分歸因于人視良知為未足轉而向外求之,即增補良知。但是,知行二分造成了人們割裂地理解良知本體,即對良知之理解縮限于行的認知上,“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
由此反觀前述陽明關于惡來自性寓其中的氣質所遮蔽的說法,氣質之影響故然為惡的成因,但并非起決定作用的主體之因,亦非本質意義上的內在之因,而是更接近于外在的起催化作用的客體之因。基于這一定位,我們有必要回到人對心之本體的認知上才能明晰惡的根源。要體察明辨善惡真妄,需從人的本心中去求。在陽明的思想脈絡中,如果不知反求諸其心,即為知行相分,亦即人對其本心良知之蔽,對良知理解與思慮之偏差。
三、去惡即致良知之體用合一 [78]
既然陽明認為人因私意私欲而將原本與行合一之知從行中拘蔽開來,卻在良知之行以外尋求天下之理,那么,去惡便需要將工夫用在致良知之上,以使人無蔽于私意私欲。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既然惡發生于心之所發處,是否意味著應從心之所發的根源處完全將私意、私欲去除呢?惡能否從根源上完全去除?特別是,在知行合一的視野中,如何做到去惡呢?
(一)去惡是從偏離良知到中和的歸返 [79]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二十九日,陽明卒于南安,留下“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的遺言。這段臨別之言,在日后引起極多回響。陽明曾以日光作喻良知,指陳心是光明體的想法。
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云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
以日光比喻良知,良知恒照;以云比喻人之七情,日光雖有被云遮蔽的可能,但太陽本身始終都存在。陽明以此闡釋人不能因為害怕私欲有遮隔本心的可能而從根本處斷滅情識。順此而言,既然人之情必然也必須存在,便無法避免有淪為私意、著意的可能性。如同太陽無法使云完全消失,因情而生的人的各種意念等心之所發的存在也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那么,陽明所言之“去惡”究竟意味著什么呢?為了回答前述問題,我們有必要就陽明所言之“心”做一考察。
先生曰:“……未雜于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陽明將人心定義為“雜以人偽”,而“未雜于人”者則為道心。人心、道心是一心發用的兩種狀態。顯然,這一分類源自《中庸》的未發和已發——喜怒哀樂等情緒未發時即為中,是體,已發時為和,是用。在陽明看來,當心之發用循于理之時,可以說是在已發之中,見其良知。“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別者也。”未發與已發呈現出體用一源的關系,即在用中見體,體必含用。當心之所發未能循于理時,則“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全得即良知全幅彰顯,未能全得并非表示不中節之心所發沒有良知,而是指良知并未徹底地呈現。由此,即便是私意私欲,也不能否定其中存在良知心體的可能。不過,這與去除私欲遮隔便能明見心之本體的說法是否矛盾呢?
“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閑無事之地而為之主,于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于優閑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于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于良知也。
陽明以“良知雖不滯于喜怒憂懼”回應對良知“于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的疑問,主張良知無善無惡,是有別于世間對待善惡的道德至善。在心之所發之意這一環節,才開始分成能循理而發與未能循理而發兩種狀態。故而言良知為體,即在其中,只是不滯。良知是不滯于內的,動氣之極的情識也并非在心體發用之外。“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當發顯于外的情識是循理而發時,便是發而中節的用,其中包含著未發之體。那么,在擾動、造作的情識中,是否依舊有心體存在呢?對此,陽明是持肯定態度的。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陽明使用氣來說明心之所發的擾動狀態,不但私欲、私意等惡之狀態可以用擾動之氣、客氣來表達,循理之意也可用氣來表現。四端之情循理而發用,也屬心之所發,即體即性。陽明認為惡也是天理,是至善的心之本體在表現時“過當些子”“過與不及”而形成的。
聯系到前述未發、已發體用一源的理論框架,循理發用的體與用、性與氣的渾然狀態即所謂的“致中和”。“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后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后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在理想狀態下,心之所發無不是致中和的,但如果在發之時過與不及,就形態而言,此即轉為“客氣”,就運動而言,便呈現為“擾動”。職是之故,良知本體與惡是同一心之發用的中和與偏差的差別,并非有一個與天理完全相對的物存在。如果本體的發用是暫明暫滅,則與之消長的私意、私欲等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以客或暫來彰顯良知本體與惡之狀態兩者之間關系的話,則陽明所言之至善與惡便接近于一種在光譜上的此消彼長的圖像。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將“有善有惡意之動”與“有善有惡氣之動”的說法進行比較的話,前者是由分別心定義出的善惡,后者是在著意的情況下體驗到的善惡,兩者雖然俱可視為心之所發之意所造成的擾動,但氣之動所生之善其背后的意念不屬于循理的范疇,而更接近于私意的造作。因此,“氣之動”所生發之善惡不能與“意之動”當中的善惡相比附,而是不分或善或惡,皆屬于“意之動”之中的“有惡”范疇。“意之動”的善指涉循理而發的意念,有別于“氣之動”之下的分別善惡之心,“知善知惡是良知”之“知善”才有體驗的實處,如果僅是分別心下的善惡之善,在良知的判斷下,也只有惡而無關乎善了。
陽明這種人性本原上無性氣可分的說法,從心性論而言,性之源頭即氣本來就是天理的表現,兩者在本原上應是純善無惡的,因為性與氣的表現有所過當,兩者才有所偏差,淪為私欲的流弊。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惡的出現在先天的人性中并沒有根據,也絕不能歸咎于“氣質”,這也為犯惡者改過遷善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根據。就工夫論而言,由于天理與欲求不是對峙的關系,而是偏正關系,則為學工夫也不是天人交戰,而是讓流失的意念重回本心之初。“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于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于正也”,由此,我們似可做一論斷,即惡為意念情感的偏離與執著,至善與惡的差別表現于同一心之所發之意的消長,惡與良知之間是從偏離到中和的歸返,陽明所謂“去惡”,并非從根源處將著意的個人意念完全清除,而是應從私意私欲等情識之處歸返中和。
(二)立志克己以“誠其意” [80]
“善惡只是一物”與“善惡皆天理”表明惡是對善的偏離或悖反。心之本體是知行合一之體,是無善無惡之至善,因此,惡不在心體。意是心之發動處,由于人的私意私欲有可能把本為合一的知與行二分,便呈現為善與惡。惡出于人人之私意私欲,而私意私欲是由意所發動的,那么,治惡就需要“誠其意”。由于私心發動之意為惡,故而誠意即正此私心,即陽明所謂之正心。就知行合一而言,在誠意處對治惡,便相當于揭示了惡是內在與人的意念之中,惡由意念所起,即陽明所謂的善惡在心不在物。從而,去惡之工夫便在于遏止為惡之意念,實現知行合一。
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故責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于多歧,疑迷于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
由上述引文可見,立志為靜時的“存天理”之功,“責志”為遭遇困難時的“去人欲”之功。無志之人因不將成圣之學視作人生的終極關懷,往往受到世俗習染的影響,導致私欲橫流。立志未純或為摻雜私欲,將學問視作利祿之階,或為“認不真的志”,雖以立志于性命之學為依歸,卻有所錯認。除去前述兩種情形之外,陽明亦言:“吾儕議論之間或為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所謂彼,即陽明眼中“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于行不著,習不察”的程朱學者。而即便是服膺心即理之人,由于著意、溺情、勝心與崇浮氣作祟等而導致行為矯激,也會與道漸遠。
既然克治私欲客氣的工夫關鍵在于立志責志,那么,是否意味著立志真切,即可去惡呢?事實上,聶雙江便曾有過疑惑,是否只要立志,肯認良知本心,實修實為的工夫就不再重要?由于陽明立志之說源自知行合一的本體即工夫的方法論,因此,在他看來,與存心養性的工夫是否間斷相比,通過工夫所欲達至的境界或工夫本身之所以可行的前提是否“真切”即“志道”純全與否是更為令人憂慮的。他以建造房屋為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要求每一念頭都是無所偏倚地對良知的肯認。
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為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于起立移步之習哉?
勉然工夫實踐的前提是對盡心知性本質的確認,勉然漸磨又確保志于道的真切。故而,良知心體讓工夫實踐具有可行性,而工夫實踐也讓良知心體得以時時成就。
陽明認為人之氣質或剛或柔,呈現出現實中的駁雜多彩。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于善則為剛善,習于惡則為剛惡;柔的習于善則為柔善,習于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了。
“習于善”即習熟于志道本身,“習于惡”則是習于本體受蔽的狀態。本性為習氣所蔽與否,取決于人是不是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立志即致良知,致天理,以知行合一為志;不立志,則知行為異,即不肯存天理。由“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而論,不立志即不肯致良知本心。在天泉橋證道時,陽明說:
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工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工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
陽明所要強調的是,人的私欲的存在是在所難免的,也正是因為私欲的不可避免性,才使得為善去惡的工夫成為必然。“本性為習所勝,氣所汩者,志不立也”,人之為習氣所染,乃由不立志而生——“無志”與“勝心浮氣”者皆因私欲遮隔,“立志未純”者則受到外在之習的阻隔,但無論是習心或是習于惡,陽明所欲凸顯的是私欲而非任何外物才是惡發生的決定性因素,才是真正應歸咎之處——志若不立,便會以己意否定良知之知,使私欲有機可乘,本性隨之而受到遮蔽。由此可見,不立志乃蔽之因,蔽乃不立志之果。陽明以私欲為蔽,此蔽是人之自蔽。而陽明所謂“克己”,便可以理解為克治這一不立志的“己”。
四、知行合一即去惡:從存理去欲向彰顯良知心體的轉變 [80]
陽明從心發動為善、惡來理解意,曾受到晚明劉宗周的批判。在蕺山看來,既然有善惡,則意便不是無善無惡的心之體。
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揉,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即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為君子;誠其有惡,豈有不斷然為小人?吾不意當良知既致之后,只落得做半個小人。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后,無善無惡,則云“《大學》
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于致知,后之又欲收功于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
蕺山所云無善無惡的意,應是本心知行合一之體;善惡雜糅之意應為習心,而非心之本體。因此,他對陽明“把意字認壞”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誤讀。不過,這也揭示了陽明心之發動為意之說確實存在歧義,至少在受眾的理解層面易產生誤解。對此,有必要從意與物的關系維度進行深入探討和剖析。
(一)“意之所在”與“明覺感應”:物的不同界定與物工夫的展開路徑 [81]
陽明主張“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外在于人的客觀事物和人所發的知覺言動均通過“意”而匯合于“心”,在此語境中,物不僅可以指有形具體的事物,也包含了由心發用并賦予意義的觀念或意識。前者不難理解,基本上與我們在現實經驗層面的界定相同,后者則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物”頗有距離。
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于目,汝心之聽,發竅于耳,汝心之言,發竅于口,汝心之動,發竅于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
視聽言動之所以被陽明界定為物,是因其同時具備心之主宰與身之充塞兩大特征,會涉及人的情感發用,是意之所在。不管是具體事物,還是視聽言動,于陽明而言,皆為心之發用本身,都與人情相關聯,“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里”。那么,陽明為何對物進行如此不同的界定呢?在筆者看來,這涉及不同的為善去惡格物工夫展開路徑問題。
對陷溺于外在的具體有形事物的人而言,“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著軀殼外面的物事”;對陷溺于知覺發用的人而言,“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這兩種情形,在陽明看來,都可歸結為舍心而逐物,“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換言之,即沒有讓良知作為主宰所導致的。對此,陽明主張以格物工夫“去其人欲而歸于天理”。
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
省察克治私欲并非一蹴而就,陽明主張,“初學必須思”,所思者“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從而,存理便是去欲。陽明說:“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由此,省察克治(去欲)與存養(存理)是一體兩面,前者是人與現實中的具體有形事物或單純知覺發用時的存養工夫,后者是人與外物隔絕而知覺未發用時的省察工夫。明代習程朱學的士大夫往往將居敬、窮理對應靜與動二事,但朱子言“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其實只是一事”,陽明則認為“一心主一個天理”,則居敬就是窮理,窮理就是居敬,若是分開去體會,則“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因此,“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縱觀陽明的生命歷程,50歲以前重視的是有事無事皆存理去欲工夫,50歲以后直指良知心體,恰如其夫子自道:“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伴隨此種轉化,心、意、物之間的關系也做出了相應的改變,去惡之實踐也隨之有了新的要求。
就對物的界定而言,較之于前述意之所在,陽明又增加了明覺感應。
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
上述引文出自陽明與明代最杰出的程朱學者羅整庵(欽順)的書信,作于1520年,是年陽明49歲,平江西宸濠之亂,距離提出“致良知”之說尚有1年。在“意之所在便是物”的界定中,“意”包含著或善或惡的心之發用,因為惡的存在,陽明便不能直接說“意”是良知的發用,必須以省察克治的工夫去惡;“以其發動之明覺”中所謂之知,是良知本身。而上述引文所稱之“意”,是身之主宰的心即良知本體所發,屬于“有善有惡意之動”中善的部分。“以其發動之明覺”中所謂之知,是良知本身。其所界定之物,是本于良知的發用,較之“意之所在”注重格物工夫,此處或許透露出陽明對良知本身發用感應的重視,為其思想轉換的征兆。
陽明以“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形容把握致知后處事處物明覺感應的狀態。造化精靈不是指良知作為宇宙創生的實體,而是在描摹一種致知后與物無對的自然順應,即“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不過,考慮到陽明曾言:“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則之所以會有善惡的分判,是因為“軀殼起念”,而“軀殼起念”所衍生出來的惡是在“意之所在為物”的范疇內討論——惡可以相對地去除但不可以消滅,則在“明覺之感應為物”的范疇內便可絕對地去除,因其發生的可能性已然被否定。如果以天泉證道的四句教來理解,前后的差異即“為善去惡是格物”與“無善無惡心之體”的分別。
許朝陽將陽明思想中的良知視為存有論本體的前提,探討心體至善一元如何開出現象里善惡二元的問題,從心性修養而言,固然是本體工夫不二,但如果從存有本體來看。其實指的也是本體現象不二。一切存有源自一元本體,這表現在對惡的態度便與前述為善去惡的理論系統不同,而是對惡的涵化,甚至亦無惡可去。他并以陽明江西“知是知非”時期與居越“無是無非”時期來談論陽明從“道德”走向“超道德”的過程,認為“超道德”即讓“惡”得以涵化。那么,我們是否可以作此推論,即陽明晚年發明“致良知”之后,善惡分別已非其關注的重點,而是朝向心體的虛與無的面向,惡則因為心體的超越本質,故終將得以存在,或者說是消解?
(二)“有”“無”的辯證:致良知即知行合一 [82]
在“意之所在為物”的范疇中,因“軀殼起念”的私欲而產生惡;而在“明覺之感應為物”的范疇中,因有悖于心之“天”的特質與屬性而產生惡。在陽明思想中,這兩種心與物所代表的不同意義以及惡的不同產生場域,是否因陽明的生命歷程與學思轉變而呈現出兩層工夫的分野,事實上,陽明弟子中對此也不無疑惑。例如,周道通發問道:
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并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于無也。須是不滯于有,不墮于無。然乎否也?
針對周道通的疑問,陽明認為“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契悟未盡的原因在于將“必有事焉”與“何思何慮”分別成有與無,而兩者并非截然分開理解的兩件事。“何思何慮”者乃“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一個天理使這個能順應感通的良知同時具備了“有”的屬性。而周道通之所以會將兩者分開去談,原因很可能在于將“必有事焉”作為去欲的實踐工夫,而將“何思何慮”理解為“主一無適”的存養工夫。前者較易把握,至于后者,陽明認為“‘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那么,自然與勉然之分是否意味著陽明認為有與無分開與否應以根器即個人資質稟賦為判斷標準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
陽明將下學比喻為肉眼可以看見的栽培灌溉,上達則是不為感官所感知界定的生長過程。只要在下學處用功,自然能上達,“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前述之勉然即在下學處用功,而勉然工夫之所以可行,則在于良知心體作為內在依據。由此,聯系到“意之所在”之惡需要借助勉然的工夫克己去私,“明覺感應”便是“意之所在”處用功的良知根據。在陽明看來,程朱之學重視格物窮理,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乃是錯訓格物——“圣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后儒不明格物之說,見圣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如果直接跳過勉然的去欲工夫,便不能跨至“盡心知性”的階段。良知是無所不在的,如果能在去欲的過程中逐漸將良知認得明白,則人情物理與良知便也應為同一件事,而此番論述,也就同時解答了如何做到知行合一的問題。
聯系到陽明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由“意之所在”轉向強調“明覺感應”,或可解釋為陽明50歲提出“致良知”之后,其學說從原本的由用見體的存理去欲轉向由體見用的直指良知心體。但是,“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明覺感應”并不能說是超離于現實發用的“意之所在”的另一個“無”的層次,陽明以“明瑩無滯”定義心體,“明瑩無滯”是“無”,而心體能如鏡子般明瑩透亮辨別照物,這就是“有”,是在現實處勝私復理的實踐工夫,“無”與“有”是同一層次的存在。
天泉證道時,陽明弟子錢德洪重視現實經驗層面的去欲復理工夫,而王龍溪則直悟本源,認為不僅心體無善無惡,就連意、知、物皆應是無善無惡。在陽明看來,“汝中之見,是我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里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執一邊,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體各有未盡”。換言之,兩位弟子的教法分別對應到一般人與利根之人的需求。如果僅重視“有”的層面的去欲復理,則對心體之“無”便終少徹悟;如果僅重視心體“無”的氣象,卻不行為善去惡的實功,最終不過“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
嚴灘問答時,陽明對于“有”與“無”又有指點:
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
龍溪所言為陽明所贊同,亦可將之視為后者對于有無的看法:本體上說工夫,強調的是現實經驗處存理去欲的實功,是為“有”;工夫上說本體,強調的是心體無滯虛靈的存在本身,是為“無”。基于觀察視角的不同,本體、工夫分別呈現為“有”與“無”的面向,而以知行合一的整體理論框架審視,則本體、工夫合一。
《大學問》集陽明畢生思想之大成,其中的“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致良知”的整全表達。“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人心之仁即“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就是孟子所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在本質上本與天地萬物是通貫無礙的。唯有在私欲蔽錮時,這種“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良知才會被隔斷,形成知行為二的局面,惡的狀態也由此產生。職是之故,陽明主張,只要從蔽錮的狀態歸返于理,便是天地萬物一體無礙的展現。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明覺感應”即“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良知本體,“明明德”強調的是良知具有通貫無礙的本質,“親民”則旨在說明良知通貫無礙的本質是如何具體“達用”的。“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至善即良知心體。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明覺感應”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良知心體展現為現實中的格物工夫,是“意之所在”之發用呈現為或善或惡時的善惡判斷標準。陽明認為,如果僅強調良知心體本身,而沒有落實在現實中彰顯良知是非判斷的一面,便是僅重視“無”而遺失了“有”。如果僅是重視“親民”而沒有掌握良知虛靈的本質與善惡判斷的能力,便是僅重視“有”而迷失了“無”——雖然晚年拈出良知心體、由強調誠意實功轉向重視致知,但并不代表陽明認為“無”超越“有”,也不代表“明覺感應”與“意之所在”的判然分離。未有知而不行者,有無、實虛、格物致知之間實為一體兩面的關系——無論前者還是后者,均是割裂知行,將知行二分,導致惡的發生,自然無法完成去惡的任務。
五、結論 [83]
陽明在心之所發即“意”處談惡,惡不是與善對立而是善的偏離。從而,惡作為一種狀態,并不具有本體論意義,僅具有現象學意義。惡不能歸咎于外在的“習”或“物”的浸染干擾,而是源于人心私意私欲的遮蔽,根本原因則在于將知行二分,導致心之發用背離良知本體。因此,去惡工夫也應在心之發用即意處著手。雖然在陽明思想發展歷程中存在由用見體到由體見用的轉變,“明覺感應”不同于“意之所在”,直指良知本身,即心之所發無不是良知天理的流行,但并不意味著“無”超越“有”,僅有“明覺感應”而無“意之所在”或僅有心體的肯認而沒有去欲的實功,終究不是知行合一的致良知。在知行合一的框架中,“有”“無”、實虛、“明覺感應”與“意之所在”是即體即用關系。在“有”的過程中會因“軀殼起念”而生發出惡,在“無”的體驗中會因執著于情感發用與誠意工夫而陷溺,進而導致惡的發生。由此,去惡便意味著在意之所在的偏離處復返良知,在膠執于明覺感應處回復良知。換言之,致良知即去惡,去惡即致良知,二者同為知行合一也。
如果我們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陽明的全部生命歷程,則由強調“意之所在”的存理去欲到重視“明覺感應”良知心體本身的彰顯,其間蘊含了從偏重于以用見體到以體見用的轉變,或許與其晚年不再向上“得君行道”而是轉向普通眾生的“覺民行道”有關。能夠在意之所在處省察去欲的關鍵在于“勉然”,“明覺感應”之存在則構成了“勉然”之可行的內在依據。去惡不在外物,而在于人心本身。此心光明,則諸惡自然復返,這便是陽明對善的肯認與堅持。不過“蓋良知雖不滯于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于良知也”,陽明沒有回答這“不滯”但參與其中的良知,為什么會讓這些動氣之極的情感生發出來,以及良知為何不能防患于未然等問題。“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于賊,亦用知者之過也。”理論上的罅隙也導致后學流弊蜂起,有待后學予以闡發完善。
(責任編輯:楊翌琳 ? 責任校對:羅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