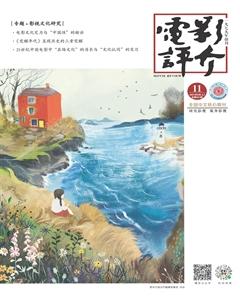由《出山記》至《進城記》:社會轉型下的歷史記憶與身份確證
付松
《出山記》和《進城記》都是由焦波導演的紀錄片,分別于2018年和2020年上映。《出山記》是全國首部反映易地扶貧搬遷的紀錄片,講述了貴州省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大漆村的脫貧故事。大漆村是極貧鄉里的極貧村,影片以一年的時間記錄了在脫貧攻堅進程中,這里發生的感人故事和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城記》是《出山記》的姊妹篇,持續跟蹤《出山記》中的搬遷住戶,記錄他們如何走進城市、融入城市,如何從移民變為居民的故事。這兩部紀錄片都以真實作為基礎的表達方式,沒有劇本的安排,沒有專業演員的出鏡,以客觀的視角記錄了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內心情感的轉變。尤其是在進入城市之后,他們是如何從不安、矛盾、糾結到逐漸適應,再到最后身與心都實現了“進城”的過程。
挺拔的大山連綿起伏,秀麗的景色云霧繚繞,陡峭的山路蜿蜒曲折,山里的人家一貧如洗……這是《出山記》的開篇鏡頭;灰白的樓房鱗次櫛比,優美的小區綠樹成蔭,配套的設施一應俱全,搬遷的群眾喜笑顏開……這是《進城記》的開篇鏡頭。兩組鏡頭的強烈對比,生動詮釋了易地扶貧搬遷帶來的山鄉巨變。在“十三五”期間,一場波瀾壯闊的大遷徙在貴州大地全面展開,近200萬人離開了自己生活的土地與村莊,將自己的生活空間轉移到城市。作為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貴州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按時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的創新舉措之一。從全國搬遷規模最大、任務最重的省份,到率先完成易地扶貧搬遷的省份,比宏大敘事更為激動人心的,是每一個貧困家庭、每一個貧困群眾在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中的悄然改變。從《出山記》到《進城記》,導演焦波用真實的鏡頭對準了遵義這片土地,用時代的厚度和視角的溫度,客觀、樸實、冷靜、深刻地記錄易地扶貧搬遷的人與事,為廣大觀眾帶來通俗的解讀和心靈的震撼。
一、敘事視角: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
費孝通將傳統中國概念化為“鄉土中國”,對于安土重遷的中國人來說,村莊與土地是與他們的生命與情感聯結在一起的。“鄉土中國的特征可以從農民與土地、農民與村莊的關系梳理出,因為人的行為與制度規則嵌于人與土地的關系以及人與村莊的關系中”[1],人們以村莊為基本生活單位,以村而治。他們以土地為生,同時也受到了土地的束縛。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從“出山”到“進城”的過程充滿了復雜性。在《出山記》中,我們看到了當地村民對“離開土地”所表達的本能抗拒,其中既有對土地的不舍,也有對城市新生活的恐懼。對于他們來說,這里是家園。基層干部反復地做思想工作,傳達國家脫貧攻堅政策及其必要性。
影片首先以客觀鏡頭記錄體現了這種必要性。在《出山記》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貧困的家園。大漆村陽井組村民申學王一家三口圍著土灶和鐵鍋站著吃飯,整個屋里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面對臥病在床的父親,在外務工的大漆村泉里組村民申學科被迫辭工返鄉。他不希望看到父親像母親那樣“弄都沒弄到醫院去看就過世了”。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申學科和大叔、小叔一起,輪換著把父親背下山去,坐車送到重慶治療……泉里組是大漆村39個自然組之一,坐落在懸崖之上,當時還沒修通公路,村民進出需要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本著“通不了就搬,搬不了就通”的原則,大漆村在修建通組公路、發展特色產業、完善基礎設施的同時,大力做好群眾工作,準備實施搬遷。規劃、測量、拆遷、建設,當村民們坐上了開往城市的大巴車,他們即將面對的是完全嶄新的生活。
費孝通認為,“人和土地在鄉土社會中有著強烈的情感聯系,即一種桑梓情誼”[2]。在談論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時,在經濟之外,政治、社會與文化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村莊對于生活在那里的人們來說,不僅是遮風避雨的屋棚,同時也是精神上的歸宿。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安土重遷觀念從未消逝,人們對于土地的感情已經成長為一種精神氣質。他們對于土地的割舍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一遍遍講政策、一次次擺道理、一個個算細賬……為了說服群眾搬遷,數萬名駐村第一書記和縣、鄉、村干部走進田間地頭,深入農家小院,召開田坎會、院壩會,逐一解開貧困群眾的心結。無論是《進城記》還是《出山記》,給觀眾展示的都是一個個真實的鏡頭,一個個生動的故事,矛盾沖突時常出現在干部群眾的爭執中。影片《出山記》以大漆村黨支部書記申修軍為典型代表人物,記錄了基層干部在此過程中的艱辛。在群眾的反對、妻子的埋怨、兄弟的指責等重重困難下,即便被群眾打折了手臂,申修軍仍然告訴村“兩委”干部,“我今天要去醫院檢查,這里的工作,大家不要泄氣,不要認為我今天發生這個事,思想上就覺得恐慌,工作還要繼續開展。”申修軍是中國數萬基層干部的縮影,他們直面困難、勇于擔當,和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苦干實干詮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書寫了一部部絕境突圍、決戰貧困的英雄傳奇,樹立起一座座令人敬仰、永不褪色的精神豐碑。
《出山記》的歷史與情感價值也正在于此。影片并不是一部政治宣傳片,而是以誠實的鏡頭記錄下了在搬遷過程中安土重遷的人們所遭遇的情感的破碎,同時也直接反映這種難以調和的矛盾;再通過對矛盾沖突的記錄與典型人物的塑造,呈現了在此過程中一心為民的基層干部的現實處境與情感訴求,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個縮影。在影片的最后,是一個無奈的提問,一個小男孩在新家門口對著鏡頭發問:“這是誰的家?這也是我的家?”情感上的矛盾或許比影片所呈現的更加瑣碎而深刻,但影片最終表達了一種樂觀的態度,即在無奈的現實之下,惠民政策切實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便利,以及他們對于新生活的逐漸適應。
作為《出山記》的姊妹篇,《進城記》圍繞《出山記》結尾的懸念,以2018年6月底遵義市易地扶貧搬遷群眾走出大山、進入城市開始新生活為素材,持續跟蹤搬遷住戶,記錄了以覃猛、楊多晏等為代表的搬遷群眾如何適應新生活、創造新生活的點滴變化。
在《進城記》中,觀眾看到的是一個安居的樂園,進城讓生活更加便捷。在新蒲新區的幸福社區,超市、醫院、養老院、學校、社區服務中心、就業車間等配套設施完善齊備,給來自大山深處的搬遷群眾帶來更多便利,使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勞有所得、學有所教。樹蔭下,老人們圍成一圈下起象棋,滿面笑容;廣場上,音樂響起、舞姿翩翩;校園里,孩子們在教室里享受優質教育,在足球場上踢幾腳球、賽幾趟跑,童聲回蕩、樂趣十足。同時,政府也為人們提供了就業保障。幸福社區為搬入的322戶1383人舉辦了多次招聘會和技能培訓會,就業率達80%以上,確保了有勞動力的家庭戶均一人以上就業的目標。在《進城記》的首映禮臺上,影片主要拍攝對象之一、社區書記熊文霖向觀眾介紹,影片中的這批移民現在已經漸漸適應了城市的生活,“這里有更好的教育、醫療資源,也有很好的工作。未來,我們會共同奮斗,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從“出山”到“進城”,四年的創作拍攝時光,1400多個日日夜夜,焦波用鏡頭真實記錄了遵義脫貧攻堅這一生動實踐,為時代留下珍貴記憶。
二、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建構
“記憶”一詞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既指個體或群體對于過去事件的認知(內容意義),又指人們獲得和保持自身經驗的一種活動(行為意義)。記憶對人類社會延續和個人生存有著重要影響……不論是個體記憶還是強調紀念,或由統治群體主導的集體記憶(或社會記憶),都是作為人類對于過去經歷的一種記錄和保存”[3],從某種程度上說,集體記憶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個體在此過程中通過由集體生活經驗所構成的記憶確立個體的身份認同,正如伏爾泰所說,“只有記憶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個人的相同性”[4]。大漆村的村民世代生活在這里,他們已經習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已經與土地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聯結,從鄉村搬進城市,搬遷群眾要面對的,不僅是生活環境的改變,還有生活習慣、生產方式、思想觀念、子女教育、社會融入等一系列問題,這是一個固守與突破同步進行的過程,也是一個痛苦和幸福相互交織的過程。
在《出山記》中,從申周一家搬遷前的一組對話,可以看出搬與不搬的矛盾交鋒,這表面上是一家人搬與不搬的爭執,而更深之處體現的卻是農村老年人面對城市生活的惶恐與擔憂、膽怯與退縮。當申周表示想要搬到務川去時,父親說,“搬下去容易嗎,連我自己都不敢決定,維持不了生活”,母親考慮的則是“搬下去豬、羊、雞都不可能養”。兩種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異,讓他們對自己“城里人”的新身份感到非常不適應。申周帶著父母去逛超市,琳瑯滿目的商品讓他們眼花繚亂。在內心感到新奇的同時,他們卻連標簽上的價格都看不懂,一支2元的牙刷以為是20元;“紅家伙不能走,非得要紅家伙變成綠家伙才能過”,在過斑馬線時,他們要像孩子一樣從“紅燈停、綠燈行”學起,逐步懂得城市的交通規則和生活法則……《進城記》記錄了社會與政府幫助他們建立起新的身份認同的過程,政府提供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免費住房、子女入學、醫療保障等各個方面都有所輻射。但對于脫貧攻堅工作來說,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只有解決好搬遷群眾的就業問題,讓他們有一份相對穩定的收入,才能讓他們真正能夠養活自己,讓家庭這個社會的最小單元維持穩定,從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出山記》中,30多歲的大齡青年申周最大的心愿,就是搬進城里、娶上老婆、開個超市,然而窘迫的生活讓他的這些愿望都遙不可及。他的父母常年生活在大山里,只跟莊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象搬去城里該如何生活。兩代人的觀念無法調和,甚至動起手腳,關系瀕臨破裂。一個小家庭的爭執折射出大漆村移民搬遷面臨的困境。和申周父母一樣,大漆村村民樸實、良善,但他們在人生的經驗中已經形成了固有的思維與生活方式。他們覺得自己離開了村子,便是“斷了生存的活路”。老家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們親手搭建和培育的,在他們心中,只有土地才是賴以為生的希望。從這個角度來說,易地搬遷無疑是農民與土地關系的一次深刻變革。農民走出腳下的大山困難,但翻越精神上的大山更難。
如何真正實現村民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進城記》嘗試性地給出了答案。例如,在影片開頭的招聘會上,“新市民”覃猛以陽光爽朗的形象首次露面。他來自務川自治縣石朝鄉一個貧困家庭,爸爸殘疾,媽媽有智力缺陷,但他始終積極樂觀地面對生活。覃猛和妻子在社區開了一家餐館,由于生意不景氣,小兩口經常鬧矛盾。在社區的幫助下,他結合自己的特長,組織親朋好友合伙開了一個婚慶公司,善于學習的覃猛最后成為一家影視公司的攝影師,“政府給我的這套房子不僅是一個房子,而是一個舞臺,展示人生的平臺”。能夠尋求新的謀生方式,意味著人們對于自我身份認同的一種轉變。再如,搬遷前,45歲的楊多晏在大山深處以養羊為生,一家人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搬遷后,楊多晏先是在一家社區車間工作,因為視力的原因被辭退。在多次應聘失敗后,他主動尋求社區的幫助,爭取到一筆5萬元的“特惠貸”,做起販羊的生意,生活逐漸好轉。
但相比年輕的覃猛,楊多晏一家三代三口人所面臨的生存壓力更大。楊多晏搬進城市的目的只有一個:讓兒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走出山村,改變命運。正因為如此,每當兒子貪玩調皮、不愛學習時,便是他最傷心難過的時候,為此他特意帶兒子回了趟山里老家。當看到昔日熟悉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再也找不到爺爺住的老屋、找不到曾經關羊的地方時,不禁唏噓。在眾多的“新市民”中,像楊多晏這樣的搬遷群眾不在少數,他們是易地扶貧搬遷后續工作中繞不開的幫扶對象。他們搬到城市,希望老人有良好的就醫條件,希望自己有滿意的就業崗位,希望子女有優質的教育環境,卻因為自身體能、文化、年齡等因素難以在城市謀生,無法在新的環境中實現自我身份的建構,面臨著成為城市“邊緣人”的困境。但在《進城記》中,我們欣喜地看到,社區積極想辦法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社區流轉周邊土地時,召集搬遷群眾開會,讓大家共同謀劃集體產業;打造蔬菜基地、開辦惠民超市等,讓大家真正成為城市的一分子,這是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后半篇文章”的生動縮影。
在惠民政策的幫助下,大漆村的村民在長久的村居生活中所形成的集體記憶雖已成為不可磨滅的印記,例如對土地的眷戀,老一代人依然喜歡在家中種菜等,但他們已經具備了能在城市中謀生的能力,實現了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年輕一代也有了更多的機會與人生的可能性,個體與環境產生了正向的聯結。在這個五彩斑斕的大舞臺上,他們努力地構建全新的自我身份認同。
結語
從《出山記》到《進城記》,搬遷群眾實現了從“身”到“心”的“進城”,他們對于未來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對于自我發展也有了更多的信心。從他們的身上,我們能夠看到黨的惠民政策一步步落細、落小、落實。金秋時節,大漆村的萬畝香榧開始有了收獲,以土地入股的村民第一次看到了收成……在幸福社區,以覃詩潔和楊子涵為代表的幼年一代正在健康快樂地成長。導演焦波用樸實的鏡頭記錄了這些發展變革,記錄了社會發展下的普通人、普通家庭,也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思考:原來便民利民的好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會遭遇這么多困難。并促使人們思考這背后的原因,這不僅僅關乎現在與未來,更關乎歷史與群體記憶,村民們的背井離鄉讓影片始終彌漫著淡淡的鄉愁,但社會的發展是需要向前看的,影片的現實意義由此體現出來。
參考文獻:
[1]劉守英,王一鴿.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中國轉型的鄉村變遷視角[ J ].管理世界,2018(10):129.
[2]費孝通.中國士紳——城鄉關系論集[M].趙旭東,秦志杰,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53.
[3]潘立川.記憶與敘述:口述歷史中的身份認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17:6.
[4][德]格賽羅.身份認同的困境[M].王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