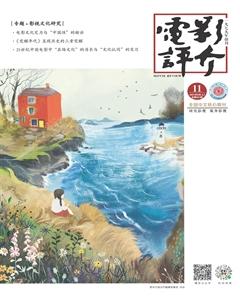電影之美、影像哲學與精神批判:羅伯特·布列松作品批評
王佳赫
法國著名電影導演羅伯特·布列松以哲學性的思想內涵與簡潔理性的影像風格聞名世界。在《扒手》(1959)、《驢子巴特薩》(1966)、《溫柔女子》(1969)、《穆謝特》(1967)、《錢》(1983)等藝術質量上乘的作品中,布列松在簡潔明快的電影語言中展現了電影之美,在超越性的哲學精神中對人生的孤獨與迷惘進行了富有價值的探索,并構成了對戰后資本主義世界控制社會的精神批判。
一、現代電影美學的不同呈現方式
布列松早年畢業于美術學校,其把握動作構筑畫面的能力遠超一般導演,但他的電影在電影理論體系中并非以直接與某種既有電影美學相聯系的形式出現,它們并不明確屬于“現實主義電影美學”或“形式主義電影美學”之類的既有范疇,似乎也無法將這些改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作家文學名著的作品清晰地劃為“古典影像”或“現代影像”之列。但毫無疑問的是,無人能否認布列松作品中的電影之美。勒克萊齊奧評價布列松的作品是帶有誠意地將感官的種種震撼形諸人前,“布列松的夢想是去分享生命的豐盈、生命的光輝。他鐘愛身體和面孔、少女的頸背、一副肩膊、一雙堅定地踏在地上的赤足”[1];布列松同樣自述他拍電影的過程猶如“我夢見我的影片在目光下自己逐步形成,像畫家永遠新鮮的畫布。”[2]這樣充溢著感性的認知為布列松的電影添加了難以忽略的現代審美要素。以《扒手》為例,《扒手》講述無所事事、愛好文學與藝術的年輕人米歇爾在目睹了一個小偷行竊過程后,被其偷竊的動作吸引而誤入歧途的故事。對于價值觀淡漠、信仰虛無主義的米歇爾而言,社會道德是虛偽的,但小偷自信優雅的手法卻是一門真正的藝術。布列松借米歇爾之口將偷竊時活躍的手部動作形容為“手指芭蕾”,他呈現扒手手部動作的方式并非突出其形式之美。布列松使用了一貫以非職業演員出演主要角色的方式,盡量淡化表情與動作的方式消除偷盜與被逮捕、逃跑與被抓回之間的情節沖突,將米歇爾塑造成一個以“偷盜的藝術”為信仰,卻既不缺錢也并不擅長此道的孱弱青年形象。在憂郁的表情與游離不定的目光中,米歇爾的動作既不自然也不協調,配合麻木無情緒的獨白,呈現出一種底層小人物惶恐不安、對生活毫無信心、也并不期待未來的絕望感。布列松用大量篇幅渲染了米歇爾的這些特征,極力塑造這一彷徨、笨拙而執著的形象。但人物形象鏡頭與鏡頭間似乎卻并不連續,每個對人物形象進行描繪的畫面都在零散的故事敘述中呈現出碎片般的質感。在他最終在賽馬場被警察抓住的場景中,鏡頭在他正面面部的近景與準備行竊的手部之間反復切換,游移不定的目光與行動預示了這次行竊的失敗。米歇爾的行動與結局猶如現實生活的走向一般飄忽不定,充滿不確定性與無法預見的結果。與笨拙的米歇爾相比,米歇爾在賽馬場目睹的集體偷盜在鏡頭中卻堪稱藝術,特寫鏡頭下一只手探入口袋摸到了錢包,修長的手指靈巧地將其夾出口袋;鏡頭持續拍攝,錢包在一閃間到了另一人手中,又隨即在外套的遮掩下再次轉手一人,黑白畫面中,暗色的服裝將偷盜者的手指反襯出一種蒼白卻靈巧、在簡單的動作中充滿力量的特性,一場多人配合的行竊看似一場精妙的藝術。
在古典或傳統美學的角度看來,特寫長鏡頭下呈現的行竊慣犯流暢的“手指芭蕾”似乎更符合美學形式的要求。但在布列松的作者意愿中,無論是行竊慣犯或笨拙的米歇爾,應該都是符合其現代電影美學原則的。近代以來的美學理論以感性領域與美學理論的二元區分解構了傳統美學,認為傳統美學被切割為兩個不可還原的領域,表象的體制將我們與感覺隔離,“美學的兩種意義合而為一,以至感性存在就在藝術作品中顯露自身,而與此同時,藝術作品也呈現為實驗。”[3]換言之,在古典藝術中,感性的審美保留了藝術與現實經驗相一致的部分,而理論的審美建立在現實的真實性基礎上;前者更容易被辨識為審美的材料,而后者更多被歸為美學理論層面上的思想要素。布列松的電影恰恰將感性之美從理論中解放出來,賦予它獨特的感性邏輯,將其還原為現實中可見的東西。在簡潔明快卻充溢著感性邏輯的畫面中,藝術顯示出其實在可見的一面。在對視聽感官的滿足之外,布列松將美賦予超驗的精神性。在以女性悲劇為主題的《溫柔女子》中,布列松描繪了身份低微的溫柔女子與當鋪店主身份不對等的戀愛悲劇。扮演女主角的多米妮克·桑達是法國著名的時裝模特,她的面龐在逐漸憂郁的影片氛圍中呈現出驚人的美麗。但影片中對女主角之美的描繪并非對其容貌的直接描繪,而是片頭與片尾反復出現的空鏡頭。在飽受丈夫的控制欲與經濟壓力的折磨后,女主角以跳樓的方式與丈夫的變態控制欲相對抗。“溫柔女子”在現實世界中離開丈夫的物質支持寸步難行,因此在影像中無法以固態影像的形式與其相對抗;將這一形象抹除在銀幕上,只留下披肩在空中飄蕩的鏡頭卻凸顯出女主角精神上的抗爭。這個鏡頭中“攝影機-意識變成了一種溢流,因為它實現于某種流動之節,并因此獲得一種物質確定性,一種流變-物質”[4],從而出現了一種非現實的物質美學形態。《溫柔女子》是布列松以黑白為主基調的影片序列中為數不多的彩色電影,這一鏡頭典型體現了布萊松電影中的美學實踐特征。
二、影像哲學與主體感知的結合
嚴格說來,哲學中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影像哲學”分支,電影不是哲學的研究對象或哲學思想的圖解,電影也不必通過哲學定義自身。所謂的“影像哲學”更多的是認識論層面上一種將電影的敘事方式與哲學思想相聯系,在二者間建立平等對話、相互交流關系的思考方式。布列松的電影作為一種蘊含豐富哲學思考的創造性活動,在跨學科的視野中可以構成開放性的討論與對話空間,從而將電影與哲學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式結合起來,獲得新的批評可能性。電影的影像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與哲學同等的創造材料,是因為影像既是客觀存在、向物質世界敞開的圖像,又可以通過放映與觀影的儀式,進入觀影主體的精神內在之中,在觀眾的精神生活留下印記,將主體精神世界整合進影像世界的關鍵便是電影的觀看與放映。愛因漢姆的格式塔心理學或與借助精神分析學產生的第二電影符號學,都提出了電影影像作為一種作用于主體的精神影像生產。但對于布列松的電影影像哲學而言,他的電影對主體的必要性卻并非來源于單純的情感蒙太奇,也并非依賴主體的無意識生成。其中最關鍵的,是讓影像主體獲得一種純粹的觀看體驗。純粹的觀看并非一般意義上觀眾對銀幕形象的觀看乃至凝視的體驗,而是以影像本身的感知進入自身的潛在“生命”的體驗。攝影機不單純跟隨或描述人物,而是作為感知的主體加入人物當中。
在以一頭驢為主要角色的《驢子巴特薩》中,這一趨勢尤為明顯。導演沒有取消驢的動物性賦予其人性,也沒有按照驢的主觀視角展開放大觀眾對旁觀者身份的認知,而是以非人亦非動物的自然視角,冷漠而悲憫地看待平等的眾生在苦難面前的無能為力。在一些人類與驢同在的影像中,鏡頭以半觀看者半客觀的視角分別拍攝了人類與驢的動作,在影像保持半主觀視角的同時,被表現的人物角色與驢子巴特薩也在以其自身的方式感受著沉默與痛苦,他人施加的暴力與充滿不確定性、沒有意義的世界。此時的攝影機視角不等同于人物,也不外在于人物。在驢被轉手賣給農民時,布列松以固定機位的空鏡頭等待驢入鏡,驢出鏡后繼續拍攝長椅等一般景物,以凸顯出攝影機意識的方式將影像歸還于純粹的意義中;在一場驢反抗人類暴力的場景中,驢拉著載滿稻草的車沖下了田埂,將車上的稻草與農民一起摔倒在地,自己趁機逃走。這段密集而富有沖擊力的動作在布列松的鏡頭中僅僅呈現為一系列短時間特寫鏡頭的剪接:首先是一對中景鏡頭從運動的兩個方向,大體交代了驢拉著稻草車,趕車的農民坐在車上的運動狀況;接下來分別是驢蹄、車軸、農民想要拉緊韁繩的手部動作、車輪飛速碾壓在路上、車輪從路上偏離、翻倒在地的稻草車車輪等一系列特寫,這時布列松以驢從稻草堆中站起的動作結束了這個組合段。這個段落中,布列松并未用全景展現稻草車傾倒這一過程,也沒有展現車夫驚恐的表情或對驢車失控的反應,或以音樂為影片渲染緊張焦慮的氣氛;而是執著于現實景物(驢車、車輪、驢蹄)的運動節奏,通過在同一段落中不斷切換統一景別的不同鏡頭強化影像對這一事件的純粹觀看體驗。這一段落在一般導演的處理中,可能會以日常性的感知方式令觀眾體會翻車瞬間的視聽沖擊;而布列松選擇同時從影像的外部與精神的內部著手,一方面在有節奏的運動中整合稻草車、驢子、車夫等要素之間的運動,另一方面也在碎片化的空間中通過純然的力量將原本分散的局部全部銜接起來,如同《鄉村牧師日記》中的站點與路途兩側的景物,《圣女貞德的審判》(1962)中審判貞德的角落、貞德的單人間、死囚牢房,《湖上的蘭斯洛特》中的水族森林,《扒手》中的跑馬場、里昂火車站一般。這些電影對整體空間的建構方式使主體自身的觀看位置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觀眾也得以感受到自身在先驗領域中本然存在的問題。影像本身的情感直接出現在一個與之相應的空間里,體現在碎片化的景物中。這些碎片化的景物不僅是對外部世界的還原,更是在精神世界內部發生的認識精神活動,但它們的存在不依賴于觀眾的觀看,也不圍繞敘事主體的運動發生或附著在主人公等特定角色上。“精神每碰到一個部分,就像碰到一個封閉角度,但在局部的重新銜接中,享有體力的自由……不僅顯示了任何表達中自由間接話語的增加,還顯示了發生的和被表達的事的可能關聯,呈現了空間與被作為純可能性表現的集合。”[5]在排除影像所表達的社會性、文化性的內涵建構之后,布列松的電影以一種自在和自為的方式,向著永恒的時間綿延敞開。潛在的生命出現在影響自身生命的層面上,影像哲學也通過對人類思維活動的比喻與中介成為一種主體哲學。
三、對資本主義控制社會的精神批判
布列松的作品在電影美學與影像哲學方面都具有豐富的內蘊與特色,同樣也從未停止對現實中小人物生活狀態的關注。盡管他并不通過具有辨識性的正反兩方博弈行為提出對社會的批評,但對資本主義控制社會的批判卻內在于他的大多數作品之中。控制社會中的“控制”并非普遍意義上某一主體對另一主體的控制與規范,而是由布勒斯提出來的專門術語,它被福柯用來描述不遠的將來中權力所有者用以支配社會的方式之一。福柯將18至20世紀的社會視為規訓社會,提出規訓社會中的規范是個體在多個封閉空間之間的遷徙與過渡,社會權威在極大程度上仰賴于傳統的社會規訓場域;而德勒茲提出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依賴規訓的傳統空間與規訓社會逐漸被消解,控制社會正在取代規訓社會。德勒茲與加塔里將規訓的權力視為一臺抽象的機器,有許多機構或社會層次同時構成,并分享其中的權力;而在控制社會中,從社會研究開始權力擁有者就將牢牢將社會把握在權力的結構中,權力的控制絕對化必然導致權力機器對個體的暴力行為。[6]在布列松的電影中,權力機器并不顯影于某個確切個體或團體中,但無辜的個體始終遭受著來自控制社會的暴力行為,呈現出一種被外部場域所控制后無能為力的狀態。
取材于真人真實的影片《死囚越獄》(1956)中,被判死刑的弗朗西斯在納粹行刑前的幾個小時內策劃越獄。他積極準備,在洗漱時試圖得到隔壁囚室獄友的幫助,卻在準備中途被判立刻執行死刑。弗朗西斯克服了內心的軟弱與恐懼,在獄友的幫助下毅然帶著另一名年輕男囚犯一起從監牢中越獄。監獄作為權力直接作用于個體的重要象征性場域,經常在各種電影中充當敘事空間,以囚犯越獄為題材的電影也由于囚犯與獄警之間權力與地位的懸殊而富有內在張力,成為電影常關注的題材。人生自由受到控制、生命權即將被剝奪的死囚與支配其生命與自由的獄警或監獄管理者相比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兩者之間的沖突對抗經常成為電影敘述的核心矛盾。然而布列松的《死囚越獄》卻在具有先導性與決定性的環境中,以物理上與外界隔斷的囚犯與其異化內心的斗爭為中心,冷峻地觀察死囚弗朗西斯追求自由的個人意志與內在化的社會控制之間的反復搏斗。對于是否能突破堅不可摧的監牢,弗朗西斯的內心不斷地產生自我懷疑的想法,這些想法導致了他行動的虛弱與躊躇。福柯在論述規訓社會的觀點時,曾借用邊沁的“全景監獄”描繪規訓社會中權力控制個體的方式。在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中,將被管理者放置于彼此隔離的封閉空間中,并告誡犯人們是被權力監視的。無論管理者是否實際監視被管理者,被規訓后的犯人們都假定著管理者的監視存在并自覺遵守其中的秩序。弗朗西斯面臨的則是規訓社會與控制社會的結合,規訓的權力或資本同時以兩種方式實現著自身的管理,前者體現為納粹牢房中的管理訓誡,后者則體現為不斷迫近的死刑;規訓權力作用于全體囚犯,控制權力則以更加暴力的形式直接作用于個體——同時也激起了個體的反抗。弗朗西斯在獄友的支持與內心信念的勝利之下勇敢地踏上了突破納粹監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路。
布列松的最后一部電影《金錢》則通過一個中學生花了一張假幣最后在蝴蝶效應中引發災難性后果的故事,更加直接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權力對個體生命的毀滅。這名中學生用自己的手表與同學換到500元假幣,在照相機店買回一臺相機,店員將假鈔找給了工人伊萬,伊萬在餐廳用餐后用假幣付賬,服務員報警后伊萬被逮捕,丟掉了工作。伊萬不得已參與搶劫被捕,出獄后對社會失望不已,殺害了旅館老板一家。影片以冷峻的目光審視并批評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圍繞拜金主義產生的階級壓迫、道德淪喪、底層生存艱難等問題。被市場所圍繞的商品社會屈從于資本,國家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籠罩下一個用來實現資本主義公理化的組織結構。資本積累行為超出國家的控制,徹底滲透進整個社會。在微觀層面上,中產階級父母為兒子賄賂證人作偽證,相機商店店員在獨自看店時擅自提價,克扣差價,只有處于社會底層的打工者伊萬被卷入金錢的控制機器中。在無處不在的、致力于資本積累的社會機器上,工人與消費者在商品生產的過程中成為金錢機器中的零件,并在機器的精細奴役下成為控制社會中的一部分。
結語
布列松的電影從影像內部建構起特殊的電影美學與影像哲學,讓電影影像成為充滿感性與哲思的獨特認識領域。在客體影像與主觀精神的共同作用下,布列松的電影接觸了富有現實性的社會命題,對資本主義控制社會作用于個體的暴力方式提出了深刻的批判。
參考文獻:
[1][2][法]羅伯特·布列松.電影書寫札記[M].譚家雄,徐昌明,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3,15.
[3][法]吉爾·德勒茲.差異與重復[M].安靖,張子岳,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70.
[4][5][法]吉爾·德勒茲.電影1:運動-影像[M].謝強,蔡若明,馬月,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10,174-175.
[6][法]吉爾·德勒茲.哲學與權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M].劉漢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