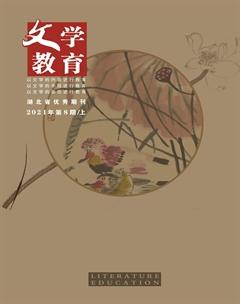大地上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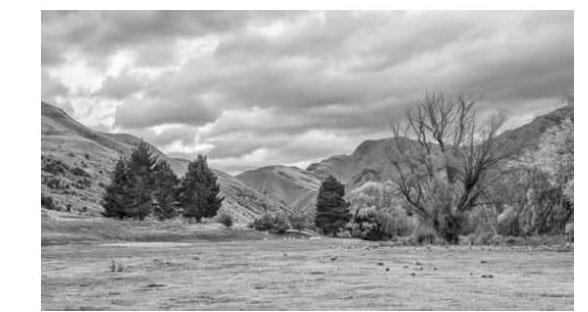
大地是“自然寫作”無法繞開的命題,那些奔走在大地之上的動物,依賴大地生存的植物,試圖改造大地的人們,以及大地自身呈現的自然景觀,共同建構著大地的倫理。龐余亮的《在那個濕漉漉的平原上》是一組以大地為書寫對象的散文,平原上的一草一木、童年經驗的吉光片羽、父子間的情感互動,在作者的筆下顯得格外動人。對于如何書寫自然,作者曾說過:“自然是我們恩情的胎衣。書寫自然,溯流而上,一起尋回最初的筆畫。”自然給予我們生存空間與精神的養料,是毋庸諱言的。在濕漉漉的平原上,作者聚焦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動植物,記憶中的人和事,換句話說,大地上的事情,就是作者心中的風景線。
先來看大地上的動物。《早春的鹽巴草》從破冰的捕魚人起筆,漫長而寒冷的冬天,比人生存得更艱辛的是那些畜生門。雞也好,狗也好,都不如豬“難受”,因為飯量大的緣故,豬的飼料成為冬天里困擾一家的難題。“我”拾豬草的童年經歷再次重現,破冰,搖船去田里扯鹽巴草的日子被喚醒了。這是一種生存的姿態,人與動物都竭力在大地上尋找生存的空間。鹽巴草的甜味寄存著生活的希望,那是一種“窮日子里的那些頑強”。鹽巴草、爬根草、鐵線草、狗牙根,不同的命名方式傳遞出其骨子里的堅韌與抗爭。《最先醒來的蟲子》則刻畫了一群忙碌的動物群像。“我”在土縫里摸蛇蛋的經歷躍然紙上,蛇蛋里的幼蛇攜帶著冬天的氣息;蜈蚣鉆洞,也是把頭“鉆到寒冷無法侵入的深度”,經過冬眠的沉睡,才逐漸蘇醒過來;蜈蚣的天敵是公雞,公雞與蜈蚣像是有血海深仇;蚯蚓的冬眠常常會遭到釣魚人的打擾,卑微的它們時常會成為魚竿上誘惑魚的香餌;青蛙和癩蛤蟆的冬眠也是寂靜的,“蟄伏”是它們的“沉默中的苦熬”。螞蟻在入冬前先運蟲草,但經不起人們一泡尿的摧毀……季節的更替,不以人和動物的意志為轉移,忙碌的蟲子們,才是平原上過日子的群體。《浩蕩的春風吹遍》寫的是燕子,春風送來了我們的老朋友燕子,燕子的壘窩筑巢與孵小燕子是春風的饋贈。在春風的浩蕩之下,稻場上的草垛也不見了,“那些跳躍在麥田深處的野兔們的笑聲”也消失了。
再來看植物。《暮春的平原是最佳的掩體》寫到了蠶豆和豌豆,“那個被玩伴遺忘的下午和黃昏,我吃下了平生最多的蠶豆和豌豆”,作者得出了“嫩豌豆甜,而蠶豆再嫩,也有一股青草的味道,留在我們的舌根處,揮之不去”的結論。“我”的味覺是一種有效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于是,“蕎蕎兒”,“薇”,“采薇”,詞語之間經由味蕾串聯起來。在作者的筆下,童年的記憶是貫穿行文始末的,“我們把那個在平原深處躲迷藏的孩子給忘記了”就是明證,植物的書寫與童年經驗的呈現是互為補充的。《那只害羞的南瓜》記錄的是父親教給“我”給南瓜套花的故事,這段近乎啟蒙的經歷定格在“我”的記憶深處,當初的臉紅與身體悸動,傳遞出父子之間微妙的情感互動。經“我”套過花的南瓜,最后宛如一只地球在平原深處隱秘地長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大地敘事中,“我”始終是在場并參與敘述的。“我”的童年記憶、生活經驗,早已與那些動物、植物融為一體。比如《早春的鹽巴草》中的打豬食,“我”是重要的參與者;《暮春的平原是最佳的掩體》中,蠶豆與豌豆也是在“我”的童年回憶中逐漸呈現的;《那只害羞的南瓜》中,套花的親歷者就是“我”……在我看來,《在那個濕漉漉的平原上》是一種有溫度的寫作,這種綿密的情感來自“我”的記憶與體驗,“我”的參與程度高低,直接決定著情感的濃淡。
在眾多的“大地書寫”的自然文學作品中,龐余亮的作品給人的感覺非常親切,與那些冷靜的白描式的自然景觀呈現的作品有著明顯的藝術分野。龐余亮善于將敘述的筆觸伸向一只燕子、一只蚯蚓,一顆南瓜、一株鹽巴草,當他把目光從容地投向書寫的對象身上時,“大地”并非是以一種圣母或曰哺育者的形象出現的,平原只是靜悄悄地在那里,大地的那種母性的“偉大性”退卻了,取而代之的是關于“我”的童年經驗,關于“我”母親與父親的故事,這種處理方式不顯山不露水,但最能觸摸讀者內心最柔軟的部分,因為那些動物、植物,那些童年記憶,都是我們曾經熟知現在忘卻始終無法重返的精神伊甸園。
周聰,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湖北省作協第二屆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