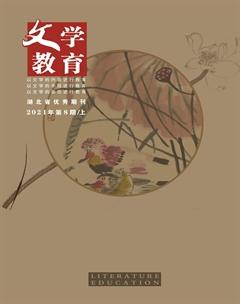論蕭紅小說中東北農民的生命意識
黎曉華
內容摘要:蕭紅是一位才華橫溢卻英年早逝的女作家,短暫的一生卻給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學財富,她對東北故鄉的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這些農民有著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既淳樸又狹隘,既熱情又懦弱,既殘忍又堅強。蕭紅對他們總是抱著希望卻又一次次地失望,失望之余又不得不敬佩這些農民對于苦難的堅韌的生活態度,要說蕭紅的作品,就不能不涉及到農民,刻畫農民形象幾乎就是蕭紅作品的中心,從作品人物刻畫形象出發探討五四時代東北農民如何在亂世中殘忍而又堅強地活著是另外一種角度。
關鍵詞:蕭紅 農民 殘忍 堅強 生命意識
五四時期人的發現以及思想的覺醒導致文學作品的大繁榮,蕭紅作為東北作家群現實主義作家的一位女性,她雖然出生在地主家庭,對東北黑土地有著深沉的愛,對東北黑土地上的農民有著最深厚的感情,用她獨特而細膩的女性視角對東北農民的生命意識進行深入感觸。蕭紅的小說里描寫最出色的除了女性就是農民,她用富有詩意的語言和深沉的基調寫出了東北黑土地農民特有的生命意識——殘忍而又堅強。
一.東北農民悲劇的源泉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中國的主力軍,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唯一條件,但是當時的制度之下,占著中國人口80%的農民卻擁有不到20%的土地;同時在20世紀30年代,東北三省被日軍侵略,由此淪陷,如此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戰亂環境,注定了東北農民的艱難處境的客觀因素。再由于農民自身的弱性,小農意識及目光短淺,這是造成東北農民悲劇主觀原因。蕭紅雖然出生在東北的一個地主家庭,但由于家庭環境的影響使她對東北這片黑土地的農民有著深沉的感情,所以蕭紅小說里面的農民形象原型大多數取材于東北故鄉,在如此內憂外患的環境中,東北的農民還是舍不得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承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虐待,在這一片深沉的土地上殘忍而又堅強地活著,但大多數都以悲劇的形式地活著,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種:
1.封建制度的剝削
農民也就是以土地為生存工具的人口。在我國的封建制度里,全國只有20%地主擁有了國家80%的土地,而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卻只有20%的土地,農民為了生存,不得不租種地主的田地,而每年的苛政雜稅壓迫得農民喘不過氣來,即使遇上好的豐收年也只是剛好夠交地主的租稅而已,更不用說遇上天災人禍了,且看《生死場》里的每一個農民,他們在黑暗的社會制度之下水深火熱地活著,農民生活的意義僅限于生存。
蕭紅本身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首先為了逃避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逃避婚姻失敗之后又面臨被未婚夫拐賣的局面,幸得蕭軍救贖卻又被其輕視以及背叛,奔波坎坷的生活來源于封建制度的毒害,所以在蕭紅的小說里,她雖受魯迅諸多影響,卻不能像魯迅一樣站在客觀的角度上批判中國農民的劣根性,她更多的是把自己融入其中,深刻理解和同情農民,刻骨銘心地體會社會宗法制度對農民的毒害。
埋葬在封建制度之下的典型犧牲品數非《呼蘭河傳》中的小團圓媳婦莫屬,“我”還以為團圓媳婦是一個很好看的媳婦,實際看到了,那卻是一個小姑娘,才12歲,活脫脫一個童養媳,嫁到老胡家之后因為“太大方”“不知道羞”“婆婆要給媳婦一個下馬威”而不斷地挨打,從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姑娘到面黃肌瘦憋出病來,有病了不看醫生卻不斷地跳大神,燒香火,最后被大神用滾燙的熱水活活燙死了。
在封建家長宗法制的社會中,注定了小團圓媳婦的悲劇,而這個悲劇恰恰說明東北農民在封建制度的毒害之下的封建迷信,封建迷信的觀念在東北農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在不自覺中斷送自己性命的同時也充當著社會的劊子手。
2.東北三省的淪陷
一二八事件之后,東北三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在東北三省建立了自己的統治機構,不斷地燒殺淫掠,給農民帶了很多災難,導致農民家破人亡,在《朦朧的期待》里,李媽本來在家鄉和一個男子約好了結婚,但是因為東北的淪陷導致男子去當兵卻一去再也沒有音訊了,現在李媽和自己東家的守衛金立之剛剛有了曖昧,但是金立之又要上戰場了,李媽的第二段婚姻眼看著也就沒了,小說通過朦朧的期待來控訴日本的侵略和國家戰亂給小人物帶來的災難。
日本帝國主義侵犯東北三省之后,在殖民地大力推廣日本帝國主義的傳統文化,為了同化東北農民,不斷發揚“王道主義”,這也就是說,對東北的青少年灌輸的是奴化思想,肅清民族意識與反日思想,以便成為任其宰割的奴隸。如在《曠野的呼喊》也是,陳公公的兒子去鋪鐵路去了,陳公公以為兒子能掙錢了很高興,不久之后卻聽到了兒子被日本軍逮捕的消息,從此陳公公瘋了,剩下陳大媽一個人,這個家從此就破了。
在《北中國》里,耿大先生的兒子耿振華投奔革命軍去了,很久都沒有消息,耿大先生每次來人都想著要寄一封沒有地址的信給兒子,上面寫著大中華民國抗日英雄,后來得到消息兒子瘋了,耿大先生因為思念兒子也瘋了,但還是想著要寫信給兒子。后來為了避免日本軍看到耿大先生寫信封上的大中華民國抗日英雄幾個字,不得已把耿大先生關在一個亭子間里,最后因為一個意外被碳熏死了。
東北地區農民不僅要受著封建社會制度的壓迫,還要受到帝國主義對自己家國的蹂躪,加上傳統小農意識的困擾,外來文化的沖擊,身心均受到內憂外患的雙重壓迫,這是造成東北農民悲劇生命的客觀因素。
3.東北農民自身的性格弱點
作為土地的附屬品,農民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里沒有獨立的話語權,長久的壓抑讓他們失去了獨立的人性,東北農村的農民性格很淳樸,善良,但眼光相對狹隘短小,看不到自身和階級的根本對立,缺乏斗爭的動力,即使是抗爭,也只僅僅是為了活下去而已。一旦得到一點物質上的恩惠,就會產生良心上的救贖與不安,服從統治階級的安排。《生死場》里面的趙三,本來和李青山組織了一個“鐮刀會”抗議東家地主的加租,結果因為趙三打斷了小偷的一條腿差點吃官司,少東家為他說了幾句好話讓他免吃官司就覺得自己不能沒有良心,于是天天進城,弄一點白菜給東家送去,弄一點土豆也給東家送去,為此他老婆激烈地吵打,他也絕對地保持他的良心,不僅同意加租,還把自己家唯一值錢的牛賣了,一半給了少東家當雜費,自然而然,地租也就這樣加成了。農民自身麻木、冷漠是導致東北農民悲劇必然因素。
二.東北農民的悲劇形象刻畫
1.殘忍的看客
農民的悲劇形象,在蕭紅小說的定義里,即是處于劣勢的農民和優勢的社會環境斗爭過程中慢慢被社會環境所侵蝕,成為社會環境的犧牲品甚至是社會環境的殺人工具。蕭紅小說筆下的農民形象,不僅是東北農民的典型,更是中國農民的縮影。
在人們心目中,農民應該是淳樸實在的,但在蕭紅的筆下農民的形象卻是殘忍的看客,這種農民性格中的殘忍是由于知識的缺乏以及人性的弱點所造成的,他們的殘忍不同于劊子手的殺人如麻,也不同于土匪的燒殺掠搶,更不同于軍閥的強力鎮壓,而是一種作為看客的殘忍。
我們看《呼蘭河傳》里面趕車的一家,這家里的老太太終年生病,兩個兒媳婦為了給老太太治病,經常在家里跳大神,周圍的人沒有意識到跳大神不能治病,反而每一次跳大神就跑去看熱鬧當做一種消遣;到了他家小團圓媳婦來了之后愈演愈烈了,小團圓媳婦因為被婆婆打出了心理毛病,家人卻以為她的靈魂被閻王勾去了,不斷地請跳大神,一跳大神,周圍人就當看新鮮地絡繹不絕地跑來看熱鬧,看怎樣把小團圓媳婦脫光放到沸騰的開水里面去洗澡,周圍的人沒有一個人去阻止,反而覺得自己沒有白看一場熱鬧到底是開了眼界,見了世面,總算是不無所得的。
長期惡劣的社會環境腐蝕,讓農民不僅愚昧,還殘忍看著一個人活活燙死卻還覺得新鮮,覺得自己開了眼界,不能不令人觸目驚心,不能不令人反省我們生活在底層的農民是否有人的權力?是否有自由意識?是否存在生命意識?
蕭紅小說不注重個體農民形象的塑造,而是一群群模糊化的農民形象,這些模糊化的農民形象就像是冷漠而麻木的眼睛,看不清現實,看不到希望,世界笑,他們也笑,世界哭,他們也在笑。蕭紅小說中故意把農民形象模糊化,更讓人反省中國對待農民的模糊態度,意在引導讀者撥開迷霧,喚醒農民生命意識!
2.堅韌地生存
堅強本來是一個褒義詞,在這里用來描述東北農民的形象,其實是反義詞。因為東北農民的生命意識不強,他們只是遵循著動物本能地走完這一生,那不叫生活,充其量只能叫生存。
蕭紅小說的農民有著頑強的生命力,無論生活多么艱難,他們總能活下去,這是東北農民的最堅強的生命意識,《呼蘭河傳》其中有一節是這么寫著的,磨房里邊住著馮歪嘴子,這是一個貧窮靠著磨粘米糕來勉強過活的小個子,人人都以為他永遠就這樣一個人地活下去了,但是有一天卻被“我”發現了馮歪嘴子有了女人和孩子了,大冬天的,女人和孩子的鋪上蓋的是面口袋,下面墊的是草,后來還被大掌柜趕出磨房到南頭的草棚子去了,人人都以為他們活不下去了,但是看到的卻是“他媽的,沒有死,那小孩還沒有凍死!還在娘懷里吃奶呢。”后來馮歪嘴子的女人死了,東鄰西舍的都說馮歪嘴子這回非完不可了,但是馮歪嘴子卻活著,帶著兩個兒子活著,一直到大兒子可以拉著小驢到井邊喝水去了,好像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揭示了農民堅強的一面,同時也在暗示著人生就應該是苦難和希望相伴隨!
三.東北農民的生命歸宿
完整的小說一定會有一個結局,每一個人物都有他存在的意義,當他在小說里完成他的使命時,就會離開,這是人物形象的歸宿,也是小說的歸宿。戰亂和貧窮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害,蕭紅小說里面的農民的歸宿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繼續麻木地活著;一種是蒼白地死去。
1.麻木地活著
人生總是充滿了苦難,幸福是短暫的,苦難卻是永恒的,客觀的因素和自身的弱點更是讓靠天吃飯的農民雪上加霜。上帝給你關上了一扇門,就會給你開了一扇窗,長期的惡劣環境的鍛煉使農民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只要一點碳水化合物就可以頑強地生存下去。同時農民思想上的麻木,身體上的麻木,眼光上的狹隘以及長期掙扎在溫飽線上讓他們失去了追求幸福的能力,讓他們對人生缺少思想上的欲望。他們人生的唯一目標就是活著與生育繁衍,像《呼蘭河傳》的馮歪嘴子,人生的磨難和貧窮不斷地折磨著他,妻子死了丟下兩個哇哇學語的兒子,貧窮使他的兒子沒有任何營養,眼睛很大,胳臂、腿越來越瘦,當所有人都認為這兩個娃娃活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居然還活著,像動物一樣活著。這就是東北農民的生存現象,也是全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就是麻木地活著。
在蕭紅的小說里,這些東北的農民就像是一群動物,沒有喜怒哀樂,沒有理想,也沒有沒有靈魂般的行尸走肉,世界如何發展,生活如何展開,彷佛都和他們無關,他們一邊淡漠地冷視世界,一邊淡漠地看望社會,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沒有絲毫的反抗。農民們不想折騰,也不愿意折騰,每天過著一樣的生活,做著愚昧而又不自知的事情。作者作為旁觀者,想要改變而又無力改變的痛苦和無奈感染著每一個讀者。
2.蒼白地死去
小人物離開世界是不動聲色的,東北農民的逝世就像他們的性格一樣,蒼白而默默無聞。離開這個惡劣世界,這是蕭紅小說里面大多數農民的生命歸宿,或者自殺,或者餓死,或者被捕之后死去,或者是受刺激之后瘋了再死去,在蕭紅看來,這戰亂的世界沒有給農民留下任何美好的東西,充斥著她們生活的只有戰亂、貧窮、壓迫,作者想以這種方式喚醒農民改變自己生命歸宿而努力,也是以這種方式控訴農民人生的血和淚,更以這種離開的方式默默反抗這世界的不公平。
蒼白的死亡對于東北農民來說也許是他們最終的歸宿,但對于蕭紅來說,這正式反襯了農民麻木地活,在作者的觀念里,是寧愿轟轟烈烈的地死去也不能麻木地生活,但令作者沒有想到地是,東北農民地生命悲劇不僅在于麻木地活著,還不知所以然地蒼白地死去,這才是令作者既痛恨又無力改變的深深無奈現狀。
中國一直都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的生命意識和最終歸宿一直都文學家所關注的問題,他們生活在最底層,是貧窮與落后的象征,卻擔負著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糧食物質基礎,他們的生活、身份、思想都應該得到相應的社會關注,城市的發展讓農民進城成為農民工,但他們的思想境況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更陷入了融不進的城市和回不去的農村尷尬的境地,我們文學應該給與反思,這正是小說的本質意義之一,從現代的目光審視蕭紅小說農民的生命觀,我們對現代農民、農村、農業的發展或許會得到一些啟發。
參考文獻
[1]劉貴.蕭紅的邊緣體驗與鄉土民眾想象[J].綏化學院學報,第37卷第11期, 2017年11月
[2]林幸謙.蕭紅小說的女體符號與鄉土敘述—《呼蘭河傳》和《生死場》的性別論述[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
[3]阮素丹.蕭紅小說《呼蘭河傳》中的悲劇意識[J].南平師專學報,第26卷3期, 2007年7月
[4]郭軼峰.從翠姨看蕭紅小說的女性悲劇[J].北方文學
[5]蕭紅.蕭紅選集[M].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2
[6]季紅真.蕭紅全傳[M].現代出版社,2012.1
基金項目:本文為廣東省普通高校青年創新人才類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9GWQNCX040).
(作者單位:廣東茂名幼兒師范專科學校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