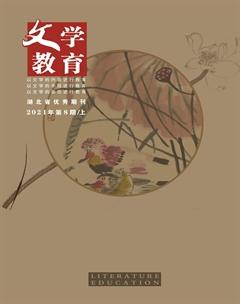林語堂翻譯理論中的道家精神
周可悅
內容摘要:林語堂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翻譯學家,其翻譯代表作品有《老子的智慧》即《道德經》,《浮生六記》等。在林語堂的翻譯巔峰時期-旅居美國時期中,通過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比較,在博覽中國傳統優秀文學哲學作品的基礎上,堅定了要讓西方人不僅要知道更要“讀懂”中華文化的目標,希望能通過翻譯將中國優秀傳播文化輾轉至西方,并將此作為自己的翻譯動力,傳播了許多經典哲學思想和中國理念,其中就包括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精神。林語堂一生都在提倡道家精神,并將其作為自己的生活理念。為了能夠對林語堂的翻譯作品翻譯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必須要對其翻譯作品中所體現的道家精神進行分析總結,體會其翻譯作品所傳達的道家思想,使更多中西譯者收到啟發。
關鍵詞:林語堂 道家精神 中西影響
林語堂曾言“老子的雋語,像粉碎的寶石,不需裝飾便可自閃光耀。”可見,道家精神在林語堂心中就像自閃光耀的粉碎的寶石,其地位不可被替代。林語堂之所以一生都崇尚道家思想,離不開時代背景,家庭環境,個人經歷這四個方面的影響。
1925年中國人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府內部存在嚴重腐敗,國內革命形勢高漲,越來越多的人主張打到段祺瑞執政府,林語堂就是其中之一。在此時期林語堂與周作人共同主張“費厄潑賴”(Fair play),主張在新舊矛盾沖突中找到一種力量的平衡,不要窮追猛打,不要過于固執執著于結果,對失敗者不攻擊。但是這一理念被魯迅等人所抨擊,魯迅為此還寫以《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進行抨擊。由此,林語堂深刻意識到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與“自由”等先進獨立思想在中國還無法實現。緊接著,1927年“四一二”政變與1933年6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楊杏佛遭國民黨特務襲擊重點身亡事件的相繼發生,更讓林語堂希望破滅,厭倦革命,從而選擇去脫離革命,逃避社會,回歸自然,追隨道家思想的生活理念。同時,當時社會上流行著文化復古主義,讓林語堂對中國傳統道家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分析,并堅定傳播道家思想的決心。
林語堂曾言“在造成今日的我的各種感染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深受者為最大。”林語堂出身于一個相對貧苦的家庭,其父林至誠是一個鄉村牧師,是林語堂最珍貴的啟蒙老師。即使當時家庭環境貧苦,但是其父堅持讓林語堂學習西方知識,拓寬眼界,這給林語堂在日后研究西方文化決心從事翻譯工作為西方翻譯到家道家文化打下基礎。在童年經歷中,令林語堂印象深刻的是高山。年輕的林語堂總喜歡高攀上高山,從高山頂上俯瞰人群,感嘆人類的渺小,對自然產生敬畏之情。這一思想與道家的自然思想不謀而合,并讓他在成年后形成了所謂的“高地人生觀”。“高山”在林語堂心中不僅是一種自然景觀,而已內化為一種符號,一種象征,甚至是一種宗教信仰的砝碼,成為影響林語堂一生的東西。[1]
一.林語堂翻譯作品的道家精神
1.崇尚自然
林語堂欣賞自然的美麗,崇尚生命的可貴,贊揚安靜閑適的生活,這是他致力于文學的原因,也是他接受道家理念的基礎。[2]傳統道家主張要順應自然,遵循自然規律,以自己的存在為前提,強調萬物的變化性,并強調樸素辯證法。而林語堂在自然思想的基礎上更強調生命的可貴性,在生命中痛苦與快樂是并存的,強調自身在心理上的舒適與安逸,不追逐名利,不給自己施加過分壓力。他認為“人生這種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種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種對人生的自然態度。”[3]在作為具有“西洋性”的中國近代文學性質小品文《浮生六記》的譯文中,林語堂也在第六章養生之道的原文基礎上進行了自己的理解,并在翻譯過程中提出“the type of gaiety that bears sorrow so well”,最悲慘同時也可以被認為是最活潑快樂的生活方式就是善處憂患的活潑快樂的生活方式。在《道德經》的譯文中,更突出自然的理念。在《道德經》的第二章中老子提出“萬物作而弗始”,要求人們要聽任萬物自然的興起而并為其創始,強調要讓萬物自己生長興起不加以干預,在林語堂的譯文中,林語堂將“弗始”翻譯為“do not turn away from them”,我們都知道“turn away from”指的是遠離,可見,在林語堂心中始終要順應自然,親近自然是更重要的,要在感受自然的神奇魔力,充分發揮自己對于自然的想象力,并將自然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
2.主張“為我”思想
林語堂曾言“在一切人類的歷史活動中,我只看見人類自身任性的不可捉摸的難預測度的選擇所決定的波動和變遷。”[4]傳統道家提倡不以天下為根本的原則,并強調國家統治者不能損害個人利益,要減少對私人活動的干預和控制。作為西方的重要文化特征,個人主義并非是利己主義和以自我為中心,其強調的是自我意識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強調將自我價值社會中的體現。在中國五四運動“人的解放”思想運動高潮的時代背景下,深受西方文化和道家文化影響的林語堂也進一步提出了精神自由,個人不可被替代,個人具有無限可能等思想。在林語堂的譯作種,他將“情理”解釋為“Reasonableness”,這個單詞在字典中有兩個意思。其中一個是“the state of having good sense and sound judgement ”還有一個是“goodness of reason”.林語堂很好地把握了情和理的關系,他不單單強調reason,即客觀存在的不可改變的宇宙規律和事實,還強調sense,即人心理所想所感知的情愫的重要性。只有將情與理相結合才能更好地認識事物,尋找價值。林語堂是把“情理”放在人生之根本,即只有懂“情理”的人,才是最貼近人生和最有教養的人。[5]
3.“上善若水”與“返璞歸真”
在林語堂的翻譯作品中存在一種“文化補償”的現象,我認為這種現象體現出林語堂翻譯中的陰柔一面,也就是注重歸化,將譯文翻譯得更加富有“情感”,更具有細膩的美感。在翻譯作品中,譯者不得不基于作品本身,以作者角度將原文知識轉化為另一種語言,那么林語堂則以一種文化補償的形式,既具體闡釋作者思想使讀者更易讀懂,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不改變原譯作基礎上表達自己的思想。文化補償作為一種思想交流過程中信息傳遞的一種方式,采用語言變通與補充等方式,將原文的信息意思傳遞給外國讀者,其實用性和有效性得到很好的證明。在中英翻譯中,林語堂常常在翻譯完整整句話之后用()來補充說明自己的見解,幫助讀者更有效的接收信息。例如在《道德經》的第二十八章中,林語堂將 “知其白”譯為“he who is conscious of the white(bright)”, 在字面意思翻譯“白”這一字為“white”之后,林語堂又在其后添加了“bright”一詞,意思是明亮,幫助外國讀者更好地理解“白”這一詞的含義(明亮單純的狀態)。通過在單調的本義后加以自己理解的詞句,也無異于是一種回歸原文意義的返璞歸真的行為了。
二.道家思想的西方傳播
林語堂先生通過對《道德經》《莊子》等代表道家思想的作品的翻譯,使西方人更明白道家中“自然”“萬物”“無為”等思想的真實含義,不止浮于表面,并將其融入自我的生活中,尋求自我的真正價值。其次,林語堂先生用道家精神的傳播架起了中西兩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下,使中西文化間的距離拉近,在保存兩者特色的同時結合西方民主自由獨立思想的影響以及許多外國人無法深刻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情況,林語堂先生將道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以西方思維呈現出來,使更多外國人對道家文化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認識。他希望西方社會減少對東方的敵意和誤解,糾正西方文化對東方的誤解,降低中西方文化差異。[6]
通過對林語堂先生在翻譯作品中所體現的“為我”“自然”“上善若水,返璞歸真”的道家思想的分析,以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我們可以深刻了解道家文化在林語堂先生的生活與文學創作中的突出作用,通過傳播道家思想,更讓更多西方學者理解道家思想,體會中國傳統文化,并使更多中西翻譯者受到啟發,秉承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的宗旨,產出更好的譯作供中西學者借鑒交流。
參考文獻
[1]彭英艷.時代的澆鑄 心靈的指向[J].邵陽學院學報,6(3):116-119.
[2]葉雯昕.弦論儒家與道家對林語堂思想的影響[A].文學評論.現當代文學,? 2136(2018):43-44.
[3][4]林語堂.中用哲學,生活的藝術[M].華藝出版社.
[5]李喜華.論道家文化對林語堂“為我”思想的影響,22(3):121-126.
[6]林語堂.論翻譯[M]//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7]秦楠.目的論視角下林語堂漢譯英翻譯策略研究[J].聯運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9(1):43-46.
(作者單位:中國計量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