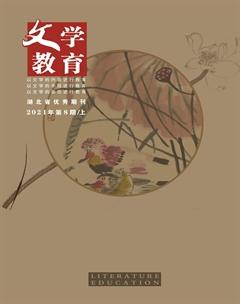論丁玲延安時期的農(nóng)村婦女書寫
馬曉娟
內(nèi)容摘要:“女性”與“革命”是丁玲文學(xué)的兩大元素,其在關(guān)注女性命運的同時,不斷追求主流革命話語。延安時期的丁玲擔負著現(xiàn)代知識分子、女性、革命者三重身份,視野逐漸下沉,從過去的關(guān)注資產(chǎn)階級女性知識分子下沉到了解放區(qū)農(nóng)村婦女的現(xiàn)實困境。書寫并探討了女性身體和心靈長期積累的痛苦轉(zhuǎn)化下的現(xiàn)代“新女性”,以及對于孤弱無奈、軟弱無能的落后農(nóng)村婦女生活和命運的關(guān)切。
關(guān)鍵詞:丁玲 革命立場 女性意識 農(nóng)村婦女
丁玲是一位獨具女性魅力的作家,也是一位堅定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戰(zhàn)士。“文變?nèi)竞跏狼椋d廢系乎時序”,丁玲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伴隨著中國的時代變化和社會發(fā)展的,其文學(xué)話語不斷隨著社會主流話語的轉(zhuǎn)變進行自我調(diào)適。丁玲前期寫作緊緊跟隨五四思想革命和個性解放的命題,作為“新女性”的她敏銳地洞察了在西方文明和傳統(tǒng)文化的碰撞中覺醒后的知識女性在走出封建家庭以及面對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所存在的尷尬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上的幻滅感。以處女作《夢珂》敲響了文壇的大門,而《莎菲女士的日記》更是轟動了整個文學(xué)界,發(fā)出了“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chuàng)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絕叫”①,彰顯了新時代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真實的生命感受。隨后《阿毛姑娘》《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自殺日記》等一系列作品,都書寫著莎菲式的個人主義者的現(xiàn)代女性主體的困境,挖掘出女性在面對病態(tài)的社會、追求上的失望和孤獨中大膽地控訴封建禮教的極具叛逆精神的一面。20世紀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中國革命形勢發(fā)生了巨大轉(zhuǎn)變,知識分子走出狹小的生活圈子走向了革命,革命文學(xué)運動發(fā)展起來并且在左翼思潮的推動下,促使更多作家走向轉(zhuǎn)型,而此時也正是丁玲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變期,集體主義的革命主題開始替代了前期小說中的個性主義主題,女性意識也在逐漸消退,創(chuàng)作了《韋護》《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文本,而《田家沖》之后的《水》則是丁玲成功轉(zhuǎn)型的標志之作,隨后又創(chuàng)作了《法網(wǎng)》《消息》《夜會》等作品。而在30年代后期至以后的延安時期,經(jīng)歷了歲月的動蕩和生命的沉潛,女性意識的再次復(fù)蘇,使得丁玲在革命書寫和女性書寫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此時關(guān)注的視點則從早期的知識女性下沉到農(nóng)村婦女,如《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等文本。延安政治環(huán)境的差異及變化,現(xiàn)代知識分子、女性身份、革命戰(zhàn)士的多重身份,都使其面臨對著更多的矛盾和掙扎。文章通過梳理和深入分析丁玲在延安的創(chuàng)作文本中的農(nóng)村婦女書寫,揭示其在延安時期具有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啟蒙與批判意識,身為女性的生命體驗以及作為革命者的民族國家的革命熱情等種種復(fù)雜纏繞的訴求。
一.延安時期丁玲小說中的農(nóng)村婦女形象
“到延安后,丁玲的小說努力摒棄先前的自我情緒創(chuàng)作向主流意識形態(tài)靠攏,但此時的女性意識與階級社會意識并不能充分地融合,預(yù)設(shè)的理念往往與創(chuàng)作效果出現(xiàn)斷裂,導(dǎo)致事態(tài)發(fā)展變得突然或牽強。”[1]從前線退回到延安修整的時間里,丁玲的心境從一開始的昂揚豪邁轉(zhuǎn)向低落沉郁。革命的想象、戰(zhàn)斗的豪情沉靜落實到解放區(qū)的生活常態(tài),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丁玲在矛盾與沖突中去面對、認知外在世界,并在創(chuàng)作中重新構(gòu)造自他、主客關(guān)系,形成新的女性自我,或是具有強烈自我意識與主觀訴求轉(zhuǎn)化形成的“新女性”,或是幾千年來“依然故我”的落后農(nóng)村婦女。
從1937年到1942年,丁玲先后創(chuàng)作的文本凸顯了解放區(qū)婦女的現(xiàn)實困境,視點從過去的資產(chǎn)階級女性知識分子下移到了落后的農(nóng)村婦女、受侮辱的婦女、革命勞動婦女,是丁玲關(guān)注女性命運、女性意識的重新復(fù)蘇。而知識分子自覺地批判意識和啟蒙意識下形成的暴露書寫,顯示了知識分子在自我和大眾的轉(zhuǎn)換中的矛盾與反復(fù),是宏大敘事中集體語言遮蔽下的個體言語掙扎。
1.女性身體和心靈長期積累的痛苦轉(zhuǎn)化下自立、自尊、自強的現(xiàn)代“新女性”
丁玲從男權(quán)文化深根固柢的性別暴政中深入關(guān)注到女性生存的困境,并試圖以此為切入點尋求婦女解放,以及在政治化、社會化過程中女性的個體價值的凸顯。不同于丁玲早期筆下的莎菲、薇底們是苦悶、迷茫、封閉,有著極度自我情緒的女性,《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等文本中,丁玲塑造了一群有著全新社會經(jīng)驗和政治信仰的具有新的時代特征的女性形象,即敢于面對命運、反抗社會壓迫的陳老太婆、貞貞,她們是在女性身體和心靈長期積累的痛苦轉(zhuǎn)化下積極的現(xiàn)代農(nóng)村“新女性”,她們在生活中面臨著的真實的困境、肩負的責任擔當和在社會歷史中艱難的抗爭和成長,并最終升華為新的歷史主體。
1938年7月丁玲創(chuàng)作了《新的信念》,以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宏大敘事為題材,主人公是被日軍強暴的陳老太婆。駱賓基高度評價文本成功地“雕塑了一個農(nóng)村老婦有著倔強靈魂的塑像。那靈魂是早已銹蝕的,在大風浪的沖擊之下,開始剝落,開始透明,開始帶著銹蝕斑痕而發(fā)光了”。“這已經(jīng)是一個新的老太婆了,…… 新的中國農(nóng)村婦女。”[2]在親眼目睹孫女兒慘死在日本鬼子的蹂躪下,孫子英勇赴死,以及太多的罪惡后,老太婆憑借令人震撼的生的頑強意志,活著回來,徹底發(fā)生轉(zhuǎn)變。她從前是脆弱無助的,即使在家庭內(nèi)部也沒有存在感,可能如許多普通農(nóng)婦一樣悄無聲息的過完一生。這次悲慘遭遇使她與鄉(xiāng)親們在差不多的思想中建立了新感情,最后加入了婦女會,到處奔走,控告敵人惡性,喚起全村父老鄉(xiāng)親奔向革命的“洪流”。老太婆“新女性”形象的“新”體現(xiàn)在哪里?她不是忍辱偷生、在他人的指指點點中對女性失貞感到屈辱沉默地承受一切的傳統(tǒng)女性主體,“她宣說那些殘酷的事實,她又看見了眼淚……她跟著就來撫摸那些受了傷的靈魂,她又把那些興奮人、鼓勵人的故事,渲染出來,于是人們又笑了。她便在這時勸大家都上隊伍去,只要別人一遲疑,她就吼起來”②,老太婆是敢于正視自己慘痛經(jīng)歷的,她向大眾揭開自己的傷疤克服沉重的恥辱感,并對經(jīng)驗進行整理、重新編排構(gòu)造,通過分享在自我與大眾中建立了一種共同的對于敵人的仇恨的共情紐帶,鼓舞激勵人們奔向革命的洪流。她將女性身體和心靈長期積累的痛苦進行積極地轉(zhuǎn)化,主動地肩負起了一份“啟蒙”鼓舞大眾的責任擔當。當然,丁玲的描寫是理想化的,老太婆覺醒的人物形象崇高,真實性不足,但是具有很深的歷史意義的,顯示了革命和女性的共同成長。
馮雪峰評論《我在霞村的時候》時說“作者所探究的一個‘靈魂……在非常的革命的展開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這在落后的窮鄉(xiāng)僻壤中的小女子的靈魂,卻展開出了她的豐富和有光芒的偉大”[3]。十八歲的解放區(qū)鄉(xiāng)村女孩兒貞貞在遭到日軍的糟踐后,以慰安婦的身份成為邊區(qū)的情報員,患上性病,為著革命工作舍棄了個人康健和女性貞節(jié)。這樣忍辱負重的貞貞,是有個性、有自我、有著倔強“生”的信念的社會底層女性,同時也是有著自我犧牲精神的革命同志。貞貞是防御型人格,在受到巨大的心靈和生理創(chuàng)傷后,她平靜不動聲色不是因為忘記,而是在平靜背后有著一顆傷痕累累的心。同時,貞貞的心靈純潔坦然、開朗堅韌,她只是愿意去好好活著,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并過好以及追求更好的明天,不去背負受害的經(jīng)歷和旁人的議論。她在認同傳統(tǒng)的同時又狠狠反抗傳統(tǒng),貞貞早就表示無需任何人的同情可憐,于是她決定離開,忙忙碌碌地活在不相識的人面前,比活在家里,活在有親友鄰里的地方好些。到了延安,還別有一番新的景象,還可以從新再做一個人。霞村有著一套千百年來形成的“正常的”農(nóng)村倫理機制,貞貞面對個人受害經(jīng)驗的大方與坦然“理應(yīng)”是不應(yīng)該且不能存在的,她應(yīng)該是羞恥的、接受人們同情的,但也正是因為貞貞的這一份傲氣,使她在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遭際時,能夠在動蕩的時代洪流中拓展自身的生命體驗,而坦然面對及為邊區(qū)政府送情報時她選擇的生存的姿態(tài)和意義,也是她在長期經(jīng)歷了身體和心靈積累的痛苦中升華為“新女性”的艱難成長。“新的東西又在她身上表現(xiàn)出來了”。
2.孤弱無奈、軟弱無能的落后農(nóng)村婦女
丁玲在《三八節(jié)有感》(1942)中說女人“她們不是鐵打的。她們抵抗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4]不是每個人都是陳老太婆,都是貞貞,此時農(nóng)村婦女多數(shù)仍是孤弱無能的,《夜》里何華明的老妻以及清子,都是此類婦女的書寫,顯示著丁玲對農(nóng)村婦女問題的關(guān)注。
《夜》文本最初部分書寫了傍晚回家的何華明的心路歷程。何華明眼里的清子“發(fā)育的很好。長而黑的發(fā)辮上扎著粉紅的絨繩,從黑看見的兩邊伸出條紋花布袖子的臂膀”③,這是對清子身體性的描寫,包含著何華明隱秘的性的欲望。而在這種奇異的感覺之后,而隨之而來的則是為了壓抑這種欲望產(chǎn)生的鄙夷,即政治上的“落后”。同樣引起何華明“奇異的感覺”的侯桂英,她的政治優(yōu)勢是“落后農(nóng)村婦女”無法比的,她同樣是有女性魅力的。而到了老妻這里,徒留下的只是嫌厭和不耐煩,認為她是“老怪物”“老東西”。這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她孤弱無耐,落后軟弱,丁玲隱含的女性意識有著對她的同情和關(guān)注。她大丈夫十二歲,滿是灰塵的長發(fā),蒼白的瘦手,年老色衰;她在情感上被丈夫厭惡嫌棄,也無子女依靠,封閉的家庭中無人過問,政治思想意識是落后的。她用放肆的哭泣、捶打、大聲咒罵來企圖激怒丈夫,換來的仍是丈夫的冷落和無視,“好像他的脾氣變得好了,而她的更壞,其實是他離去的更遠,她毫不能把握住他”④。《夜》描繪出了這類農(nóng)村婦女群體的真實處境,像何華明的老妻,她甚至連名字也沒有,作為母親的些許溫馨回憶也沒有,失去肉體的光鮮和做母親的權(quán)力,淪落拋棄的下場。但這樣可憐卑微的女人并不是一無是處的,她為他守著這個家,燒好的飯,新孵的豆芽,炕角上的簍子里新生的一窩小雞。文本末尾寫道“黃瘦的老婆已經(jīng)睡熟了,有一顆眼淚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這顆淚把人們帶進她們苦楚的精神世界。何華明苦惱于“宣傳工作不夠啰,農(nóng)村落后呀,婦女工作等于零……”卻沒有想過如何幫助他老妻這樣的落后婦女群體。《夜》顯示了新政權(quán)推選的部分革命工作者情感上的冷漠以及在思想和工作中的局限,同時也是革命政權(quán)下新、舊兩類婦女都隱含著的主體性危機,尤其表達了對那些孤弱無奈的落后婦女的生活和命運的關(guān)注[5],在革命與權(quán)力話語中凸顯女性問題。
二.作家身份與丁玲書寫革命與女性的原因
丁玲及丁玲創(chuàng)作的復(fù)雜性源于其身份的多重性。她既是作家,也是女性,同時還是自主尋求革命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其在社會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聯(lián)結(jié)纏繞并于生活和作品中彰顯,形成復(fù)雜的文學(xué)形態(tài)。丁玲一生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折射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的發(fā)生、發(fā)展和轉(zhuǎn)折,她也是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縮影,折射出中國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知識分子個人的命運和心路歷程,反映了知識分子與文學(xué)、政治間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當然,她也是一個極具個性的人,在不斷追尋靠近主流話語的同時,并未放棄自我個體的言說,將個性追求融進時代革命。她作為一名女性作家和革命者,以女性的生命體驗,獨特的個性和文體風格以及自發(fā)的革命熱情,表現(xiàn)出強烈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和情緒邏輯;同時,因為她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識,她與延安主流之間的抵牾又包含了明確的性別觀念的沖突在內(nèi)[6]。多重身份的交織,使其創(chuàng)作的文本呈現(xiàn)相互矛盾或話語裂縫的特點。丁玲也在通過書寫不斷地調(diào)試和確定著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因此通過探討丁玲的身份問題及對文學(xué)活動的影響來研究和理解丁玲及丁玲文學(xué)書寫有著重要意義的。
三.延安時期丁玲農(nóng)村婦女書寫的價值和意義
對于女性命運的關(guān)注是貫穿丁玲整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始終的。其早期是對“新女性”困境和出路的思考,延安時期農(nóng)村婦女的書寫拓寬了對于女性命運的關(guān)注視野。直到四十年代左右,延安的農(nóng)村女性仍然是處在戰(zhàn)爭、封建觀念、貧窮、勞動、生育等重壓下,雖說不斷在進步,但改善農(nóng)村婦女的精神和生活仍然面臨著多重困境。革命話語下的女性言說是被壓抑掩蓋的,而丁玲是具有著強烈女性批判意識的,她的視線下沉,在貼近并真正深入到這些失落的農(nóng)村婦女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后,內(nèi)心有了不一樣的聲音,在質(zhì)疑與矛盾中,從《新的信念》到《夜》試圖展現(xiàn)這些婦女真實的困境和艱難的成長過程。因此延安時期農(nóng)村婦女書寫時有價值和意義的。
中國婦女解放的漫漫歷程是艱難的,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是社會變遷的結(jié)果,與民族危亡、社會革命相關(guān)聯(lián),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婦女解放運動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主要集中在延安時期,被壓迫被剝削的婦女開始慢慢覺醒,并不斷參加到反抗民族壓迫和社會解放的戰(zhàn)斗中”,黨動員婦女參與日常勞動生產(chǎn)和邊區(qū)建設(shè)、社會管理中,鍛煉了婦女的能力并提高了社會地位。但不可否認,延安時期婦女解放運動仍是稍顯艱難的,物質(zhì)和精神的雙重匱乏,是經(jīng)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想要在朝夕間讓女性從思想上認識到自己困境并試圖去擺脫,顯見是不容易的。從早期的城市知識女性到延安時期的普通農(nóng)村婦女,女性解放與發(fā)展的正確道路從來都是丁玲在書寫中不斷探索的主題。而丁玲深入探討在身體和精神中都幾被忽略的農(nóng)村婦女面臨的生活困境,顯示中國農(nóng)村婦女在尋求自我解放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挫折和障礙,對于探索女性解放和發(fā)展的正確道路是有重要意義的。
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史中,丁玲占有著獨特的地位,她不僅是一位獨具魅力的女性作家,也是一位飽含革命熱情的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女性”與“革命”是丁玲文學(xué)繞不開的話題。與生俱來的女性主義意識、五四啟蒙思想的影響以及自身的人生經(jīng)歷,注定著丁玲對女性命運的關(guān)注;而其文學(xué)話語又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政治的變革不斷地在進行著自我調(diào)適和變化,“左聯(lián)”時期追求主流革命話語過程中,走向“政治化”的過程中一度放棄了性別書寫,而延安時期女性意識的再次復(fù)蘇,并與革命話語交織纏繞,表明丁玲并未放棄自我個體的言說,而是將個性追求融進時代革命,這也正是其不同于其他作者的特殊之處。
參考文獻
①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現(xiàn)代作家論》,鄭州大學(xué)中文系一九七九年十月印,第101頁。
②丁玲:《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頁。
③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頁。
④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頁。
注 釋
[1]論丁玲小說女性意識與革命意識的歷史化呈現(xiàn)[D].王珍.重慶師范大學(xué).2017.
[2]戰(zhàn)爭、家國與“新女性”的誕生——論丁玲延安時期對農(nóng)村婦女的書寫[J]. 冷嘉.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19(05).
[3]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記[J].馮雪峰.中國作家,1948,(1).
[4]“三八”節(jié)有感[A].丁玲全集(7) [C].丁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5]知識分子、革命與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轉(zhuǎn)”問題的再思考[J]賀桂梅.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05(02).
[6]建構(gòu)與失落:丁玲早期小說主體身份言說的特點[J].凌菁.湖南師范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2016(06).
(作者單位:西安工業(yè)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