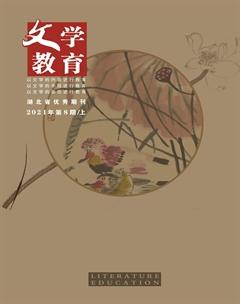穆旦譯作《拜倫詩選》淺析
楊霓
內容摘要:本論文從奈達提出的動態對等翻譯理論出發,分析詩人穆旦先生翻譯的《拜倫詩選》,鑒賞這部譯作在詞匯、句法、篇章、文體及文化內涵方面的特色,為后來譯者提供一個可供學習參考的借鑒范本。
關鍵詞:動態對等論 穆旦 詩歌翻譯 《拜倫詩選》
美國語言學家尤金·A·奈達(Eugene Nida)的翻譯理論在西方及中國翻譯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80年代,奈達的‘動態對等和‘讀者反應在中國譯學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譯界無人不曉奈達的‘讀者反應和‘動態對等理論”[1]。奈達曾提出了翻譯動態對等理論,也就是功能對等理論。何謂“功能對等”?即譯者在翻譯外國作品時不要一味追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對應,而注重于在兩種語言間達成功能上對等。奈達的動態對等先是基于 “等效原則”,倡導翻譯得自然貼切,否定字對字的翻譯。之后,奈達提出“功能對等理論”,“主張從語篇角度出發,用恰當和對等的語言,將原文本中的信息再次展現出來”[2]。“動態對等”中的對等包括四個方面:詞匯對等,句法對等,篇章對等和文體對等。但這四個方面都是一種形式對等,當形式和文化無法兼顧時,奈達認為譯者可以舍棄形式對等而把重點放在追求文化對等上,要盡力消除文化上的差異。運用奈達的動態對等理論闡釋穆旦的詩歌翻譯實踐,可以帶給我們更多的翻譯啟示,為我們的翻譯實踐提供了較好的借鑒。
穆旦,原名查良錚,是我國著名外國詩歌翻譯大師。從1955年到1973年,他主要翻譯西方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拜倫、濟慈等人的作品。《拜倫詩選》就是這一階段他的譯作。拜倫,是英國19世紀初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正因他有著十分豐富情感經歷,他寫下了許多優美的詩歌,這些詩歌富含熱情、浪漫、自由、想象與美好。穆旦在譯介拜倫詩歌的時候說:“我相信他的詩對我國新詩應發生影響;他有些很好的現實主義詩歌,可又是浪漫主義的大師,兩者都兼,很有可學習之處,而且有進步的一面。”[3]
一.穆旦譯作的動能對等
奈達“動態對等”理論在翻譯學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動態對等理論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依然是有爭議的。黃葵龍認為文學翻譯之形式至關重要,文學翻譯的目的一是要準確傳達原文承載的內容信息,二是要最大限度地再現原文的風格。而奈達的動態理論重心在于意義的轉達,而非風格的再現。“在文學作品中,內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因為形式本身就是為傳遞文本內容信息服務,其重要性不亞于內容”[4]。奈達功能對等理論認為,一部優秀的譯作是要在語言形式和文化內涵這兩方面都同時再現源語的風格和精神。因此,功能對等的實現并非文學翻譯中的易事,小處著手,方法適當,才能逐步構建目的語文本和原文本之間的對等關系。從奈達的動態理論考查穆旦譯作的功能對等可以從詞匯、句法、篇章、文體四個層面來分析。
1.詞匯對等
語言是可變的,它可以用不同的形式來表達相同的意義,所以詞匯對等的重點就在于如何在目的語中找到最恰當的那個詞匯來表達與源語對應的意義。穆旦在翻譯拜倫的詩歌時,他不局限于原文的本義,多用直譯法和描述法傳達原詩的實質。
以《雅典的少女》第三節為例,穆旦是通過直譯的方法按原文順序翻譯下來,但是在直譯的過程中又運用了描述性的詞匯,很好地表現出了源語的意義。這一節的第二句“By that zone-encircled waist”,穆旦翻譯成“還有那輕盈緊束的腰身”,原文中“zone-encircled”,zone在古時的意思是encircle as or with a band or stripe,用帶子圍繞。穆旦在翻譯時沒有去糾結于這一“帶子”,而翻譯成“輕盈”二字。古有“盈盈一握楚宮腰”來形容女子纖細的腰身,穆旦的翻譯既體現出我國文化的韻味,也表達出原文贊美女子身材好的意義。
2.句法對等
句法對等涉及到英漢兩種語言之間單復數、性別、時態一致、語法順序等的差異問題。在句法問題上,穆旦通過調整語序和重組句法結構的方式來使譯文更加連貫流暢。
以《想從前我們倆分手》第一節為例,“Half broken-hearted/To sever for years”,穆旦對此句做出了語序調整,他將其譯為“預感到多年的隔離,我們忍不住心碎”。在這句話中,有著明顯的因果邏輯關系,“broken-hearted”心碎是一種結果,導致心碎的原因是“sever for years”多年的別離。在表達因果關系的語句中,英文習慣“果”在前,“因”在后;但是中文正好相反,我們習慣先說原因,再給出結果。基于漢語的語法習慣,穆旦做出了語序調整,這樣使得譯文更符合漢語的語言習慣,從而方便中文讀者閱讀時更加連貫流暢。
3.篇章對等
篇章對等,又叫語篇對等,要使得語言在特定的語境中體現其意義和功能。簡單來說就是在翻譯時要聯系上下文語境、情景語境和知識語境。
以《哀希臘》第一小節為例,“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要想傳達出這句話的意義,就必須得了解Sappho,只有了解背后的知識語境,我們才能夠明白為什么用“burning”來修飾Sappho,明白什么是她loved and sung。莎弗是古希臘第一位女詩人,她為少女們寫下了許多動人的情詩和婚歌,她歌唱愛情的詩以熱烈的感情著稱,千百年來,她被人們視為描寫女性愛情的圣人。基于此,穆旦將這句話譯為“火熱的莎弗在這里唱過戀歌”,因為莎弗熱烈的感情,所以她是“火熱的”,因為她歌頌著的是愛情,所以她唱的是“戀歌”。
4.文體對等
譯作要體現原作的文風,要考慮不同體裁作品的文化差異。例如本文所分析的詩歌體裁作品,譯者應當要把握詩歌的風格,譯出詩歌的特色。詩歌與其他文體的不同之處就在于詩歌有韻律和節奏上的優美性,穆旦在翻譯拜倫的詩歌時,沒有機械式地模仿原詩韻腳,在盡力保留原詩的格律與韻腳同時,又適當地調整韻腳,“因意用韻”。[5]
以《意大利的一個燦爛的黃昏》第一小節為例,原文基本上是按照隔行交互押韻的方式來押尾韻,以四行為劃分點,前四行是ABAB模式,第一行“night”和第三行“height”押韻,第二行“sea”和第四行“free”押韻。后五行是CACAA模式,第五行“be”和第七行“Eternity”押韻,第六行“West”、第八行“crest”和第九行“blest”押韻。而穆旦在譯文中明顯采用了雙行韻和隔行韻混合交錯的韻式,“晚”“海”“彩”和“島”押韻,“巔”和“峰”押韻,基本上保持了譯詩的音律美,保持了意象的靈動性,傳達了原詩的內容和思想感情。
二.穆旦詩歌翻譯的風格再現
穆旦雖未曾提出一套完整、系統的翻譯理論體系,但是通過鑒賞、分析他的詩歌譯作,仍可以看出他個人的詩歌翻譯風格。他追求體現詩歌的意義,但也注重詩歌的形式,他認為意義只有通過特定的形式才能夠充分表現出來。在形式上,他不死板恪守原作的模式,而是根據源語的文化內涵以及目的語的表達習慣來自由地進行再創造。在翻譯西方詩歌時,他會靈活運用補償、改寫等多種翻譯技巧,來使得譯作更加流暢自然,在保留原詩的意象與意境的同時,還體現原詩的文化內涵,做到“以詩譯詩”。[6]
綜上所述,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經過長期以來的實踐檢驗,具有其翻譯的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然而,文學翻譯的功能對等的很大難度在于形式、風格和意義的多重對等的共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特別是翻譯詩歌比詩歌創作還要難,詩歌翻譯要兼顧形式與內容,傳達信息,表現詩意。盡管如此,從奈達的動態對等理論視角來看,穆旦《拜倫詩選》的翻譯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優秀的上乘作品,基本做到了從語言形式和文化內涵兩個方面來再現源語的風格與精神,運用詩的語言充分表現了其浪漫主義精神。從對穆旦先生譯作的賞析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譯者穆旦先生深厚的雙語功底,對詩歌語言意境的準確把握,而這也是成為一名優秀譯者的必備條件。
文學作品以形式美、風格美、音韻美呈現其形態。詩歌更是以其特殊的文學體裁明顯地區別于其他文本,是承載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和美感功能不可或缺的載體。因此,本論文認為:文學翻譯,特別是詩歌翻譯完全不必拘泥于形式的僵化和死板。詩歌翻譯的 “叛逆性創造”可以借鑒文學批評的方式對原作的形式與內容進行取舍,尋求譯者與原作者文學思想、情感共鳴的對等,而非一味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又或是意義上的對等,從而實現譯作兼修的意美、音美、形美,更能呈現文學翻譯的獨立特征。這就需要文學翻譯者開拓文學、美學、文藝學、翻譯學等多學科、跨學科視角,增強文學內涵修養與知識底蘊,才能在文學翻譯中保持其文學創作的原汁原味,最大化地實現奈達的功能對等效果。
參考文獻
[1]付艷艷.奈達翻譯理論的跨際旅行與誤讀:“讀者反應論”再思考[J].成都師范學院學報,2020(7):84-88.
[2]黎佳林、李志成.翻譯對等理論的發展及應用研究[J].公關世界,2020 (24):41-42.
[3]熊輝.論穆旦的詩歌翻譯思想.文學與文化報,2016:33-42.
[4]黃葵龍.試論動態對等理論在文學翻譯中運用的可能性—以詩歌翻譯為例[J].海外英語,2019(3):128-129.
[5]蔣瑩.以激情還激情——論穆旦詩歌翻譯中的藝術再創造[A].海外英語報,2019:129-130.
[6]張曉玲.查良錚的詩歌翻譯及其翻譯思想[A].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986-991.
(作者單位:中國計量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