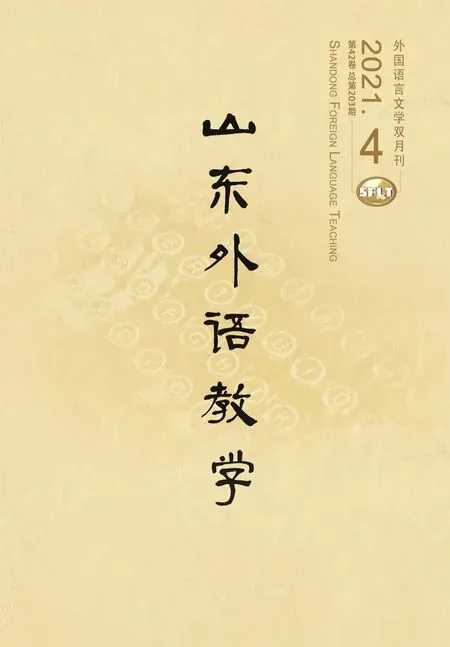“前”“后”時空隱喻表達時間指向的參照模式解釋
陳曉光 張京魚
(1. 西北政法大學 外國語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2;2. 西安外國語大學 英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8)
1.0 引言
一直以來,漢語時空表達都是學界的熱點議題之一(劉寧生,1993;周蓉、黃希庭,1999;張建理,2003;董為光,2004;蔡淑美,2012;梁曉暉,2012;王燦龍,2016;曹琳琳、邢苗苗,2017;孟瑞玲、王文斌,2017;張京魚、陳曉光,2019;王佳敏、王文斌,2021)。其中,尤以漢語時空隱喻中的“前”“后”指向問題①討論最為激烈。
前人多認為漢語“前、后”空間詞既可表“過去”又可表“未來”的原因是不同時間認知模式選擇的結果:“前”表“過去”,“后”表“未來”(后簡稱類型一)屬于“時間在動(Time Moving,以下簡稱MT)”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未來”向著觀察者運動,觀察者靜止面向未來,如“前/后天”“以前/后”“之前/后”“解放前/后” “希望還在后面”等;而“前”表“未來”,“后”表“過去”(后簡稱類型二)屬于“自我在動(Ego Moving,以下簡稱ME)”模式,此模式中,時間隱喻為靜止的路徑,觀察者在其中做向前運動,觀察者前方要走的路為“未來”,身后已走過的路為“過去”,如“前途”“前景”“希望還在前面”“往后看”等(劉寧生,1993;周蓉、黃希庭,1999;Yu,1998,2012;董為光,2004;蔡淑美,2012等)。
近幾年,王燦龍(2016)、曹琳琳、邢苗苗(2017)、劉正光等(2018)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重新關注,王燦龍(2016:176)指出僅僅依據ME和MT兩種認知模式對漢語進行分析往往會出現“捍格不通”的現象,如蔡淑美(2012:130)將“人們有了更精密的洋流儀器和人造衛星等的幫助,對洋流的認識又向前邁進了一步”視為ME模式,其實并非如此,“向前邁進”的主體是“認識”,而非時間自身。此外,他還指出盡管“前、后”均可指向“過去”和“將來”,但這兩種不同的用法內部并非對稱,類型一屬于無標記用法,而類型二屬于標記用法。曹琳琳、邢苗苗(2017:105)則進一步指出所謂的“前”表將來和“后”表過去的標記用法來源于人們將想象的“虛擬空間”和時間混為一談。“前景”“前途”一類詞表示的是“虛擬空間”,是空間基本義的引申用法,而“前塵”“后世”一類詞則表示的是時間,是基本義的轉指。王燦龍(2016)認為“前、后”時間指向的問題關涉構式類型、表達視角和參照時間三個因素,而表達視角的選取,參照時間的確認,都需要根據構式的類型來考慮。王燦龍的三因素論在解釋“希望在前面/*后面”與“麻煩在后面/*前面”的積極與消極事物語義限制中已被曹琳琳、邢苗苗(2017)證明是不完美的(如“好事在后面/前面”)。而曹琳琳、邢苗苗(2017)對有標記用法的“虛擬空間”解釋卻無意中將這一用法打回到“原空間”領域,不承認其為“時間”意義,貌似創新而已。劉正光等(2018)則大膽的提出英語時間表達從空間映射而來,而漢語空間詞既表時間義又表空間義,兩者并存(即時空同態)。他們還指出英語以運動方向為指向,而漢語則以事件的發生與否作為判斷標準,當事件已發生,則“前”表過去如“前日”等,未發生則“后”表未來如“后天”。 但是,這一理論仍然沒有為我們提供滿意的解決方案,比如“前期”劉正光等(2018)認為指過去,但是我們可以說“運動會的前期準備工作將于2021年完成”,這句中的前期定位于“未來”。其實,這表達的是ME和MT之外的時間順序性,屬于時間參照點模式(Time Reference Point,以下簡稱Time-RP, Moore,2006;Núez & Sweetser,2006 )。
Time-RP模式指以序列中的其他時間作為參照,強調時間的順序性。Time-RP模式的提出是近些年時空隱喻模式研究精細化的結果。原有的ME和MT模式劃分為了以參照點(Reference point)為標準的Time-RP模式和“自我參照點”(Ego-RP)模式(Moore,2006,2011,2014,2016;Núez & Sweetser,2006;Evans,2013)。Ego-RP模式涵蓋了原來的ME和MT兩個模式。具體而言,在Ego-RP模式里,MT名稱變為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時間在動”(Ego-centered Moving Time,以下簡稱EMT)模式,其基本內涵與原來的一致。Time-RP模式實際上是“日心說”時間認知模式(張京魚、陳曉光,2019)的具現。以太陽為中心的時間認知模式指出太陽是時間概念形成的源頭,時間的實體化表征。時間運動就是太陽運動,該運動構成了時間的序列性。
2.0 時間參照點理論
2.1 “以自我為參照的時間認知模式”(Ego-RP)及其判斷標準
在語言層面,Ego-RP的判斷標準大致有兩點:①語言表達中含有或隱含指示詞;②目標時間的定位以觀察者的“現在”,即話語發生時間為參照。Ego-RP包含ME和EMT兩種次級模式。例(1)至(3)為ME模式,如圖1,時間靜止不動,觀察者向著時間運動。例(1)中觀察者從所處位置(話語時間“現在”)向著“summertime”(夏季)運動,例(2)中觀察者已走到“the moment of truth”(關鍵時刻)的位置,兩者重合,例(3)中觀察者已走過“the deadline”(最后期限)。

圖1 自我在動(Moving Ego,改編自Moore,2011)
(1) We’re approaching summertime. → (4) Summertime is approaching.
我們正在靠近夏季。 → 夏季正在靠近。
(2) We’ve arrived at the moment of truth. → (5) The moment of truth has arrived.
我們已到達關鍵時刻。 → 關鍵時刻已到達
(3) We’ve passed the deadline. → (6) The deadline has passed.
我們已過最后期限。 → 最后期限已過。
例(4)至(6)為EMT模式,如圖2,動體為時間,觀察者處于靜止,以觀察者所處位置為參照,例4中目標時間“Summertime”(夏季)從未來向觀察者運動,例(5)中“The moment of truth”(關鍵時刻) 已經走到了觀察者所處的位置,目標時間和觀察者的“現在”重合,例(6)中“The deadline”(最后期限)穿過觀察者向著過去運動,目標時間定位于過去。

圖2 以觀察者為中心的時間在動(改編自Moore,2011)
例(1)-(3)是觀察者向著目標時間運動的不同階段,例(4)至(6)描述的則是目標時間向著觀察者“現在”運動的不同階段,均是從靠近到重合再到分離,參照點均為話語發生時間“現在”。ME和EMT這兩種模式屬于圖形(Figure)和背景(Ground)之間的互換,也是視角之間的轉換(Dewell,2007;Evans,2013;Moore,2014)。
Ego-RP模式對應McTaggart(1908)的A系列,強調時間的運動性,“現在”永遠處于變化之中,時間切分為“過去、現在、將來”。除語言證據外,手勢方面的證據也為Ego-RP的真實性提供了證據,對于英語母語者而言,常用前后手勢表示Ego-RP時間認知參照,將來的事件在觀察者前面,現在的事件與觀察者重合,過去的事件則在觀察者之后(Casasanto & Jasmin,2012;Cooperrider & Núez,2009),漢語也同樣如此,當表達“飛到未來”時,右手呈現出向前運動的趨勢,而在表達“很久很久以前”時,右手五指伸開向后揮動(李恒,2014)。
2.2 “以時間為參照的時間認知模式”(Time-RP)
Time-RP模式也可稱為順序時間參照模式(Sequential t-FoRs)(Duffy,2015),如圖3,時間被概念化為空間運動中的序列,目標時間的定位以序列中其他時間(也可為觀察者的“現在”)為參照,Time-RP模式對應McTaggart(1908)的B系列,強調時間的序列性,時間表達為“早于和晚于”,時間的早晚關系來自序列內部,無論采取哪種視角,其順序關系不變,如例(7)-(8)。

圖3 時間參照點模式
(7)Christmas is before New Year’s Eve. 圣誕節在除夕之前。
(8)New Year’s Eve is after Christmas. 除夕在圣誕節之后。
與Ego-RP模式相似的是Time-RP模式也可以采取兩種視角(Evans,2013),視角點可在前(早)、后(晚)之間轉換。例(7)中,視角在Christmas上,目標時間Christmas(圖形)的定位參照New Year’s Eve(背景),例(8)中,視角為New Year’s Eve,目的時間New Year’s Eve(圖形)的定位參照Christmas(背景)。盡管Time-RP時間認知模式中的時間序列看似是靜止的,但是也可用運動形式表達,如Christmas precedes New Year’s Eve(圣誕節先于除夕),precedes(先于)顯示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動態關系。與Ego-RP一樣,Time-RP在手勢中也有體現,英語母語者在語言表達時常用左右手勢表達時間的順序性 (Casasanto & Jasmin,2012;Cooperrider & Núez,2009),盡管在語言中沒有左右方位的時間表達,但是在手勢中左表示前時間(早),右表示后時間(晚)。漢語也采用相同的手勢策略,在表達“接著”“之后”意義時,采取雙手一起向右運動的手勢,這說明過去在左-未來在右(李恒,2014)。
2.3 Ego在兩種模式中的不同作用
Ego-RP和Time-RP這兩種模式都可以Ego為參照,不同的是Ego在兩種模式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Ego-RP模式中,Ego提供“前、后”參照的同時,也提供方向來源,其前后來自觀察者的身體結構,時間定位與觀察者有關,目標時間被定位于過去或未來,如(9)中,ahead為前,指觀察者之前(運動方向及臉部朝向一致),less fire peril定位于未來。在Time-RP模式中,Ego也可以作為參照點,但是其前后定位并非來自觀察者身體結構,而來自其序列的運動方向,如例(10),before也為前,參照點為說話時間“現在”,但是這里的前并非來自觀察者身體的前,而來自時間運動中的序列性。
(9) Cooler air, less fire perilahead.(Moore,2011)前面天氣更涼,火災危險更低。
(10) We have playedbefore.(Moore,2011) 我們以前玩過。
其實在空間中,我們也會遇到這種情況,如例(11)-(12):
(11) Mount Shasta is north ofhere. 沙斯塔山在這里的北面。
(12)Build the campfire to the north ofme. 在我北面筑篝火。
例(11)中,Mount Shasta以here為參照點,例(12)中me與here同位置,但是前者并非以觀察者的身體結構為參照,而后者則與觀察者自身結構息息相關,這一點十分重要,前人(Alverson,1994;Ahrens & Huang,2002;張建理,2003)多認為如果以話語時間“現在”為參照,其方向指示性就一定來自觀察者自身,由此來看,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有可能以觀察者的方向為參照,也有可能以觀察者所處位置作為參照,如果是后者,觀察者的前后就不是方向定位的來源,這一部分在涉及到具體漢語時空隱喻時們再做詳細分析和解釋。
3.0 Ego-RP和Time-RP模式下的漢語“前、后”時空隱喻分析
漢語“前、后”存在詞匯和句子兩種層面時空隱喻表達,詞匯層面主要由以下幾種形式組成:“前+N”“N+前”“后+N”“N+后”,N即可為時間段,如“前/后三年”,“三年前/后”;也可為時間點,如“1998年前/后”,亦或者事件,如“解放前/后”。句子層面也主要有兩種形式:靜態表達和動態表達,靜態如:“希望還在前面”“好事還在后面”等,動態形式為“向/往+前、后+動詞V”,如“往前推、往后退、往前看、往后看”等。本文詞匯語料來自《現代漢語大字典》,句子語料來自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3.1 “前”“后”詞匯層面時空隱喻表達分析
詞匯層面屬于Ego-RP的語料很少,主要集中于“前+N”形式,如:“前途、前景、前路、眼前”等。“前途、前景、前路”這類組詞的理據很明顯源自觀察者運動的路徑隱喻(自我運動),用觀察者之前的路徑轉喻未來時間,其指示性來自觀察者自身,因為人的運動方向與朝向一致,總是向著面部朝向的方向運動,也即向“前”運動。相比而言,“眼前”表現在或馬上就要發生,其指示性更加明顯,詞中的“前”毫無疑問來自觀察者自身。與“前”還少量存在相比,這種模式中以“后”為構件表過去的時間詞幾乎沒有②,“腦后”算是代表,指過去。如老舍 《四世同堂》:“老人努力地想把日本人放在腦后,而就眼前的事,說幾句話”。
漢語中大部分“前+N、N+前、后+N、N+后”時間詞都屬于Time-RP模式,表示早晚關系,如:前塵、前科、前愆、前嫌、前提、前言、前緣、前兆、前震、前奏、前仇、后步、后塵、后發制人、后福、后果、后話、后患、后記、后繼、后進、后勁、后來、后怕、后起、后晌、后世、后市、后事、后手、后效、后行、后續、后學、后遺癥、后援、后帳、之后、然后、午后、爾后、絕后、身后、隨后、從此往后、從今、以后、今后等。其中具有系統性的大致有以下幾類,如表1:

表1 “前、后”時間順序性詞匯表
值得注意的是,單純空間詞表時間的用法均以說話時間為參照,這是因為在無特殊明示的時間參照點外,話語時間對于交際雙方是最凸顯的參照點,盡管以話語時間為參照,其“前、后”指向源自時間序列的方向性,表早于或晚于“現在”(說話時間),凸顯的是時間的序列性,如例(13)-(14):
(13)這個道理,前面/前邊已經講的很清楚了。
(14)這個問題,后面/后邊我們再講。
上面的詞匯大多已固化成詞,不具能產性,而“前/后+時間段”和“時間段/時間點/事件+前/后/之前/之后/以前/以后”則具有很強的能產性,如“前/后50年、前/后期、前/后半年、前/后半夜、前/后半晌”等,均把時間段看成一個整體,“前”為早,“后”為晚,這種用法常以對稱形式出現。“半年前/后、1998年前/后、解放前/后”中“前”表示早于參照時間點,“后”表晚于參照時間點。所不同的是,這種形式中如果參照點為時間段時采取的實際參照依然為話語發生的“現在”,這是因為時間段不如1998年和解放具有定位功能,因此“半年前”指從話語時間往前(早)數半年的時間。
下面再來看看“之前”“之后”與“以前”“以后”。這兩組詞既可以“現在”為參照,又可以其他時間為參照,其語義均強調時間的序列性,即“早晚”,如(15)中參照點為“改革開放”,所指時間早于改革開放,(16)以說話時間“現在”為參照,所表時間早于現在。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兩種情況均可以說話時間“現在”作為參照點,但其時間意義并不表示過去或未來,而表示的依然是時間的序列性中的早晚關系。
(15) 改革開放之前/以前,戶籍制度把農民束縛在農村這塊小天地里,國家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剝奪農民,以損害農業為代價實施工業化。
(16)之前/以前,我并不認識他。
3.2 “前”“后”句子層面時空隱喻表達分析
除固定詞匯外,漢語“前、后”時間句子也可以分為Ego-RP和Time-RP兩種模式。前者中的自我運動,在句子中主要以指示詞“我們”作為主語,以“現在”作為參照點,可通過圖形(F)和背景(G)間的互換轉換為以自我為中心的時間運動,如例(17)-(18),括號中為轉換后的EMT模式。
(17)白嗣宏是莫斯科華人華僑聯合會主席,他對記者說,“我們都是龍的傳人,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我們即將進入龍年(龍年即將到來),相信祖國在龍年還會有更大的發展”。
(18)我們即將進入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新世紀(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新世紀即將到來),振興中華的宏偉大業需要包括婦女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奮勇開拓。
除上述表達外,Ego-RP還常用“向/往+前/后/回+看”形式,這種表達類似前面提到的“眼前”,其指示性明顯,“往前看”指觀察者自身的前,時間指向未來,“往后/回看”指向過去,兩種表達常常以對稱的方式出現,如例(19)-(20):
(19)丘吉爾的一句名言說得好:“你越是回頭看,你就越是能往前看。”歐洲近幾年向后看的勁頭不亞于向前看的努力,這該不是一種巧合吧?
(20)訪問張忠謀的過去,是一大困難,他可以天南地北,談歷史、談科技、甚至談文學,惟獨不善于談自己,尤其是自己過去的成就。他說:“這一行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后看”。
Time-RP模式中早為“前”,晚為“后”。在前的早于在后的,句子層面常以“前/后/之前/之后/以前/以后”表時間的早晚關系,上面已經提到過“之前/之后/以前/以后”的用法,這里就不在累述。下面兩例為“前、后”單獨使用時附著于其他時間或在句中表不同時間之間的早晚關系,如例(21),周一在周二之前,無論視角怎么轉換,其順序關系不變;例(22)中“文字改革”開始的時間在“解放”之前,兩者也呈序列性。總的來看,Time-RP模式具有很強的能產性,既可以序列中的其他時間,也可為序列中的“現在”為參照。當以“現在”為參照時,其方向性并非來自觀察者自身,而是序列的整體運行方向。
(21)周一(圖形)在周二(背景)前。 → 周二(圖形)在周一(背景)后。
(22)解放前,文字改革就已經開始了。
4.0 兩種容易混淆的“前”“后”時間表達分析
漢語“前、后”句子層面時間表達常出現混淆的表達,比如“希望(更大的危機)還在前面”和“希望(更大的危機)還在后面”,“ 前面”和“后面”方向相反,卻表達相同的時間定位。前者中的“前面”其實源自Ego-RP模式下的自我運動,后者中的“后面”則屬于Time-RP。下面我們選取“往前/后+看”“在前面/后面”兩者常見易混淆時間表達作為語料,進行更進一步的說明。
首先,“往前看”“往后看”即可表未來,也可表過去,如(23)-(26):
(23) 聞一多的手稿指出:“一個民主主義者是一個勇敢的往前看的人而不是一個偷偷摸摸向后看的人”。
(24) 我們現在批判的東西你回頭去看,這個胡適的時代批評過,你再往前看,梁啟超的時代批評過,你再往前看,恐怕龔自珍也批評過,所以就是歷史不斷地重復自己,每一次就是以不同的語言來表達。
(25)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向前看”和“往后看”并不應該是排斥的。糾纏歷史舊賬和細枝末節,固然不夠豁達的氣度,但鼓勵和制造健忘癥,起碼也是對人,對未來的不負責任。
(26) 如果從單糖轉化成酒再往后看的話,酒還可以被轉化成醋酸。
例(23)和(25)中的“往前看”和“往后看”屬于Ego-RP模式中的自我在動,“往前看”指向未來,“往后看”指向過去;例(24)和(26)則屬于Time-RP模式,前指向早,后指向晚,例(24)中雖用了“往前看”,但是這里面的前并非觀察者的前,而是句子所呈現出的序列的前,胡適的時代晚于梁啟超的時代,梁啟超的時代晚于龔自珍的時代,三者呈時間順序排列,因此龔自珍時代在梁啟超時代之前,梁啟超時代在胡適時代之前。因此盡管文中用往前看,其實這里的“前”是這三者時間順序的前,而非觀察者,也正是這樣的原因“往前看”之前可以加“再”字。
再來看(27)里的“往前說”。雖然“說(話)”為人的專屬,與人有關,但是這里的“前”并非以人為參照,而是與例(24)里的一樣,也是時間順序的前:
(27) 他像個中日現代史上的名人,去中國現代史館翻書,有關他的生平資料隨處可見。其實,肥原就是幾年前來裘莊尋寶的那個洋鬼子,那個尋寶不成反倒丟下一個亡妻的倒霉蛋。再往前說,二十年前,肥原是大阪《每日新聞》社駐上海記者,曾以中原的筆名,撰寫過一系列介紹中國文化和風土人情的游記、通訊,在日本知識界頗具影響力的。再往前說,說到底,四十年前,肥原于出生在日本京都一個與古老中國有三百多年淵源的武士家族里,其源頭是明末反清名士朱舜水。
其次,“在前面”和“在后面”均表未來,但兩者意義并不一樣。“在前面”表未來,指人的期望、期待,與人主觀愿望有關,而“在后面”則指晚于“現在”將要發生的時間,后者強調的是順序性, 如(28)-(29):
(28)美國調解人霍爾布魯克在協議達成后承認,更困難的談判“還在前面”,并認為,薩拉熱窩問題尤其是難點。
(29)對于克林頓來說,真正的考驗還在后面。
簡言之,“前”表未來,“后”表過去屬于Ego-RP模式中的自我在動。“前”表早,“后”表晚屬于Time-RP模式。無論是詞匯層面還是句子層面,漢語中主流的“前、后”時間表達為Time-RP模式,Ego-RP中的ME模式屬于次模式。我們的這一發現與王燦龍(2016)的分析結果一致:類型一(“前”表“過去”、“后”表“未來”)是我們認為Time-RP主模式,對應王燦龍(2016)中的無標記形式,類型二(“前”表“未來”、“后”表“過去”),即我們認為ME次模式,對應王燦龍(2016)中的有標記形式,只是他沒只有指出無標記的形式其實就是時間的序列性。
5.0 結語
本文從漢語“前、后”時間隱喻表達矛盾入手,指出Moore (2006)及Núez & Sweetser (2006)提出的Ego-RP和Time-RP分類模式能夠很好解決前文提出的有關漢語“前、后”認知模式的爭議。Ego-RP中的ME模式的體驗基礎為人類路徑隱喻,將要走的路途隱喻為未來時間,用現在所處位置隱喻現在時間,已走過的路隱喻過去時間,其指示性來自觀察者自身。Time-RP模式的體驗基礎為不同動體在排列順序中的運動,先出發的為早為前,后出發的為晚為后。此模式既可以現在為參照又可以其他時間為參照,以“現在”為參照時,其方向來自運動序列的前后,而并非觀察者自身。我們的Ego-RP和Time-RP模式分析不僅對漢語“前、后”時空隱喻時間表達指向矛盾給予一個統一解釋, 而且具體指出漢語“前”“后”隱喻時空表達的主模式是Time-RP,而ME只是起補充作用的次模式。
注釋:
① 漢語中“前”“后”既可指將來也可指過去,如“前天”“前途”“后天”“往后看”。
② Yu(1998,2012)指出“展望、瞻念、回首、回望、回顧、回溯、回憶、回想、回念、回思”也屬于“自我運動”模式,但是本文關注的語料是由“前、后”組成的時間詞,因此這里就不再進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