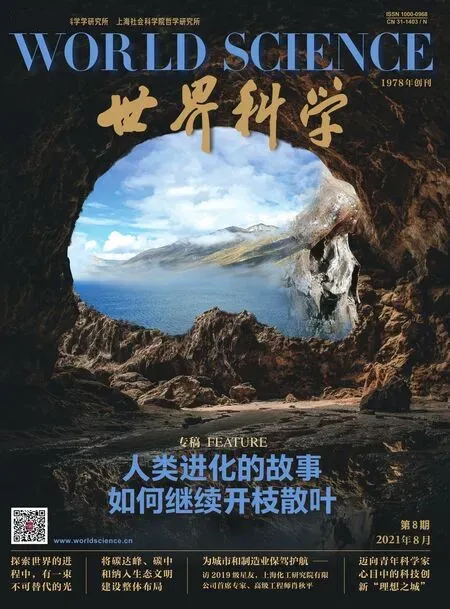自我認知的力量
編譯 莫莊非
更深刻的自我認知或許是成功的秘訣。
當你的目光掠過眼前的這些文字,你很可能不光光是在閱讀,還在思考自己所閱讀的內容。你能看清并理解字句嗎?你能集中注意力嗎?你有足夠時間閱讀這篇文章還是只能匆匆掃過它?
心理學家用一個術語定義這類意識:元認知,即對認知的認知。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的一個決定性特征就在于我們能審視和反思自我。不過我們經常忽視它在塑造我們生活方面的力量(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良好的自我認知似乎不如數學運算能力或記憶能力那么實用。在某種意義上,對于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元認知就像管弦樂隊的指揮,有時會引導演奏者向正確(或錯誤)的方向施展技藝。
現在,我的實驗室和其他研究同行正在揭開自知的面紗,這會讓人們對反思性思維的力量有全新的理解和尊重。我們已經找到了測量它的方法,甚至能使用大腦掃描儀觀察它的運作。
我們的發現表明人們需要重新思考對癡呆等疾病的理解;此外,自我認知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影響:提高自知可以讓我們做出更優的決定,更敏銳和理性地分辨假新聞,幫助我們在壓力狀態下更清晰地思考。正如一個優秀的指揮家可以區分常規排練和世界級的表演,元認知的微妙影響可能決定生活許多方面的成功或失敗。
我們在各種情況下都可能要依靠元認知。例如,在復習準備考試時,你或許會反思自己對知識的掌握情況,或者是否需要針對性地復習某些主題——這是關于記憶的元認知。又例如,在拜訪配鏡師時,你可能會被問到佩戴一副新眼鏡后,你的視力是不是更好了——你要做關于感知的元認知。就更廣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嘗試采取某種第三人稱視角來審視自己個性、技能和能力。

了解你的想法
人類很早就開始認為自我認知是有益的,甚至古希臘人以前的思想家就已經提出,人們應該努力學會自我認知,它是幸福生活的根基。
即便如此,直到最近,元認知才成為一個正兒八經的科研目標。幾百年前的勒內?笛卡爾靠自我認知得出了著名的結論“我思故我在”,并指出“沒有什么比我自己的頭腦更容易或更清晰地被我感知了”,但這種觀點幾乎無法引申出自我意識可能只是一個大腦過程——且與其他過程一樣容易出現錯誤或功能障礙——的觀點。19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認為,自我反思可能是一種心理過程的想法屬無稽之談,大腦根本不可能將其思想轉向自身。鑒于此,我們曾認為,自我意識是神秘的、不可定義的,而且是科學的禁區。
我們現在知道孔德擔心的前提是錯誤的,也不再將人腦視作一個單一的、不可分割的器官。當我們反思自我時,特定的大腦網絡就會進入活躍狀態;而如果它們遭遇損傷或疾病,元認知也會因此出現破壞性損傷。
我在倫敦大學學院的實驗室致力于了解人類元認知的機制和神經基礎。我們對“人們對他們所做的和不知道的事情的自信心”這類問題特別感興趣。例如,在問答測驗(pub quiz,在英國非常流行的一種一問一答形式的社交活動)中,你可能會跟你的隊友確認,他們是否知道正確的答案(這種行為測試了他們對自己記憶的信心);或者,你可能會質疑朋友所說的“剛剛在擁擠大街上看到的名人是否真為本人”(這測試了他們對自己知覺的信心)。如果對了,我們的信心更強;如果錯了,信心受挫,我們的元認知敏感度(我們的自我評估對自身表現變化的敏感程度,心理學概念)就會增強。這與我們通常情況下的信心水平有著微妙但顯著的不同,這種不同被稱為元認知偏差(metacognitive bias)。許多問答測驗團隊都受到了元認知敏感度差的人的影響。
正如一個優秀的指揮家可以區分常規排練和世界級的表演,元認知的微妙影響可能決定生活許多方面的成功或失敗。
在實驗室中度量這些不同方面的自我認知的一種方法是使用基于計算機的測試。在一項任務中,我們要求人們快速判斷兩個圖像中哪一個包含更多的點,然后在同一個尺度上評估他們對自己判斷的信心。通過多次觀測某人的信心并記錄其隨后回答的對錯,我們可以建立關于此人元認知的詳細統計圖。這也使我們能夠將他們的元認知能力總結為一組參數——比如敏感性和偏見,被稱為元認知指紋(metacognitive fingerprint)。
心理學家對支持這種自我認知的大腦回路有了越來越深入的了解。腦損傷可能導致元認知問題的第一個線索出現于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當時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工作的亞瑟?島村(Arthur Shimamura)正研究因顳葉(已知對記憶很重要的區域)受損而失憶的人。令人驚訝的是,其中一些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存在記憶問題。在實驗室測試中,他們表現出了元認知方面的重大缺陷:他們無法評估自己對正確或錯誤答案的信心。而事實證明,這些有元認知缺陷的人的前額皮層(PFC)也存在損傷。前額皮層是大腦中涉及復雜思維、決策和性格的部分——更具體地說,PFC 損傷會影響到決定人類擁有最高層次智慧的核心體系。
這與我們從動物模型發現的情況相符。一項研究表明,嚙齒動物大腦前部的眶額皮層中的神經元決定著它們對氣味判斷的自信心,衡量標準是大鼠在做出決斷后愿意等待獎勵的時間。來自同一實驗室的另一項實驗表明,使這些神經元回路失活會損害元認知,而氣味決定的準確性并不受此影響。
在另一項研究中,我和同事發現健康人前額皮層的細微結構差異可預測其元認知指紋。從那時起,我的團隊開始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MRI)技術描述不同前額葉亞區的激活模式如何預測人們對決策的自信程度。
不過除了自信,元認知還有一個更復雜的方面,它或許是人類獨有的,使我們能有意識地思考自己的思想和他人的思想。這種“外顯”形式的自我認知出現于3 ~4 歲,會在整個青春期持續發展,并與心智化(我們對他人心理狀態的認知)共享同一套神經機制。
事實上,現在看來,引發此種外顯元認知的大腦計算很可能是一個“二級”(second-order)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通過各種線索推斷出自己對自己決定或行動的自信程度——同樣地,我們通過他人的所做所說來推斷他們大腦里正在發生的事情。外顯元認知的大腦回路有一個“廣角鏡頭”,因此它能匯集來自不同來源的信息,并標記這些信息以創建對我們技能和能力的抽象估計(我們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此項研究告訴我們的是,人類大腦擁有特定的自我認知的算法;反過來,這也意味著腦損傷對自我認知的影響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廣泛。
癡呆癥患者可能會經歷臨床醫生所說的疾病感缺失或“洞察力”喪失——不知道自己有認知問題。了解洞察力喪失成因的一種方法是,該疾病不僅影響與記憶和認知有關的大腦回路,還影響負責維持正常自我意識的大腦回路。如果元認知能力受損,我們可能意識不到自身能力的變化,也無法理解我們失去了什么,這可能會導致人們不愿意尋求幫助,或采取某些措施(例如寫清單)來應對記憶力衰退。雖然臨床醫生敏銳地意識到缺乏洞察力是早期癡呆癥的一個主要特征,但元認知還沒成為癡呆癥的標準神經心理學評估的一部分。
更好的決策
正如古希臘人也相信的那樣,準確的元認知對于一系列的努力能否換來成功至關重要。如果學生清楚地了解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他們便能就下一步學習什么做出正確的決定。這些決定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它們最終或許會成為考試通過與否的關鍵。
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擁有進行“認知反射”的能力——可避免選擇“最初感覺是對的,但其實是錯誤”的答案——能幫助我們抵制錯誤信息和假新聞。
元認知的最后一個好處在于它可以幫助我們與他人合作。實驗室研究表明,與隊友分享有關信心的信息有助于團隊做出更好的決策。
我們的元認知指紋出現在童年時期,但即便在成年期,元認知也并非一成不變,且可能受到壓力或心理健康差異的影響。在我的實驗室的一項研究中,我們要求數百人回答有關不同心理健康癥狀的問題。從他們的回答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出每個人在心理健康的三個核心維度——焦慮和抑郁程度,強迫行為和侵入性思維的程度,以及社交退縮程度——上的位置。他們在這些維度上的位置可預測他們的元認知指紋。更焦慮和抑郁的人自信心較低,而元認知敏感性則更高;有強迫行為和侵入性思想的人則表現出相反的模式。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元認知依賴于特定、可塑的大腦過程,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能否改變這種神經回路進而提高自我認知?
大量的自我幫助類書籍和博客鼓勵我們“找到自己”并提高自我認知,但鮮有人關注它的實際運作方式,或使用客觀工具評估元認知的潛在收益。問卷形式的自我認知評估不太有價值,因為根據定義,如果你的元認知能力很差,那么其實你就不太可能準確地了解并報告這個“差”。因此,這些自助類方法尚無定論。
元認知神經科學的工具是更好的選擇,因為它們可以幫助我們直接瞄準自我意識機制。愛爾蘭都柏林圣三一學院的研究人員發現,將經顱直流電刺激(簡稱IDCS,一種非侵入性的,利用恒定、低強度直流電調節大腦皮層神經元活動的技術)施用于前額皮層,可以讓老年人更容易意識到他們在處理簡單任務時犯的錯誤。
增加大腦多巴胺水平和降低去甲腎上腺素水平的藥物也被證明可提高元認知敏感度(同時不改變其他方面表現),有利于自我認知。
日本國際電氣通信基礎技術研究所(ART)的研究人員開發了“實時”腦部掃描技術,可用于訓練人們激活與其元認知信心水平相關的特定神經活動模式。之后的實驗項目也證明,參與者借助此技術訓練兩天后,自身元認知即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接受過增強“高自信”大腦模式訓練的人對不相關的任務抱有更大自信,而那些接受了增強“低信心”大腦模式訓練的人則表現出相反的變化。
大腦刺激和設計藥物是提高自我認知的極端方法,而我們中的更多人可能更愿意用相對簡單的方式訓練元認知。鑒于此,我的實驗室一直致力于開發合適的工具,用以提供關于元認知判斷的反饋。我們要求志愿者每天花大約 20 分鐘來練習一個簡單的感知辨別,即在兩個圖像中選出更亮的那個。我們發現,那些獲得元認知反饋的人——無論他們的信心判斷是準確還是不準確——經過兩周訓練,自身的元認知敏感度都得以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元認知的提升也同樣出現在不屬于上述針對性訓練的記憶任務中。換句話說,如果你已經通過某項訓練任務提高了元認知,那么當你參與另一項非針對元認知的訓練時,也會更主動地去反思自己判斷的對錯。這意味著元認知訓練似乎能磨煉一個更通用的自我認知系統。
實現類似效果的另一種方法可能就是定期冥想了。直到最近,研究者才開始探索冥想對元認知的影響,而且初步研究結果令人鼓舞。一項研究發現,兩周的冥想訓練可提高記憶測試期間的元認知敏感性。其他工作表明,相比新手,更高階的冥想者擁有更高的元認知敏感度。
不過,提高自我認知最有效的方法或許是辨別可能遭遇損害的情況。在崇尚效率和生產力的文化中,花時間反思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反倒成了一種非必需的奢侈品。而令人矛盾糾結的是,往往我們最需要自我認知的時候,可能恰好是它遭受損害的時候。
當工作壓力變大,或是經濟和家庭問題讓我們感到困擾,進行有效的元認知或許會帶來極大好處,它能幫助我們識別錯誤,或意識到何時需要尋求幫助或改變策略。但實驗室研究一致表明,壓力增加與元認知敏感度受損之間存在聯系。例如,相比使用安慰劑的志愿者,那些接受了小劑量皮質醇的參試者體內皮質醇水平短暫飆升,而這也足以降低他們的元認知敏感度。
如果能系統地提高自我認知,那會有怎樣的感覺?一種見解來自科學家對清醒夢(做夢者于睡眠狀態中保持意識清醒)的研究。影像學研究表明,當人們進入清醒夢狀態,他們的大腦會組建起類似清醒狀態下支持元認知的大腦網絡。我發現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提升自我意識可能就像在夢中變得清醒一樣,這很有吸引力——我們可能會注意到自己過去沒注意到的事情。這些變化可能滲透到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因為自我認知是我們體驗世界的核心。我們珍視的這種認知,它讓我們能夠回味咖啡的香醇,欣賞日落的美麗或懷疑自己的感官體驗是否被魔術師欺騙,它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