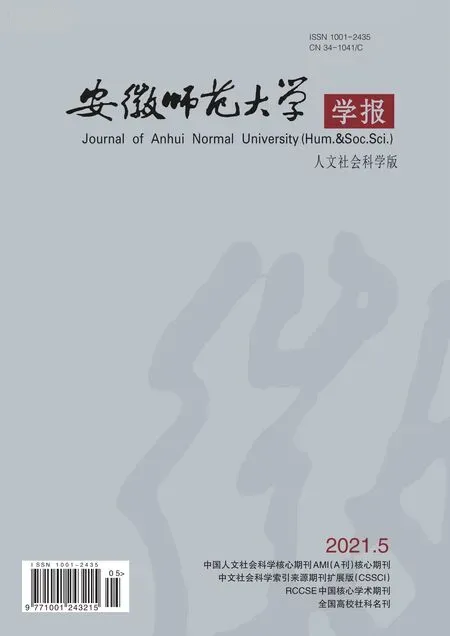20世紀美國詩歌建構中國形象的方式論*
趙小琪,周秀勤
(武漢大學文學院,武漢 430072)
當來自英國維多利亞末期浪漫主義華麗繁冗的陳舊話語在美國文壇進退維谷時,20世紀的美國詩人在遙遠的中國發現了嶄新的世界圖式與美學范式。隨后,對于中國的想象成為其反觀自我的重要方式。然而,長久以來,學界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拘囿于“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和“美國詩人如何看待中國詩學”兩條路徑。關于20世紀美國詩歌建構中國形象的方式,僅零星散見于個別學者有關美國文學的部分章節論述之中。在這些研究中,中國被解讀為向現代邁進的美國詩人懷舊心理的想象性替代物,儒、道、禪作為這種想象的表征不斷被闡釋。概而言之,20世紀美國詩歌建構中國形象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種:再造性想象、互文性想象、相反性想象。通過對中國器物表征與視覺空間的再造,20世紀美國詩人希圖在“發現”中國的同時來言說自我。通過對中國詩歌文體、句法結構、立意的仿擬和對中國字、句的直接粘貼,20世紀美國詩人意在“師法”中國文化的同時來豐富自我文化的表現空間。通過對混亂、稱霸的美國與和諧、友善中國的比較,20世紀美國詩人意在“正視”中國的同時來反思作為自我的美國。
一、再造性想象
對于20世紀的美國詩人來說,再造性想象是他們想象中國最主要的方法。當時,大量中國文物流入美國,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的載體,這些文物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美國知識界對于中國的想象。從思維認知的角度來看,這種經由本已存在的客觀物體,來達成新的認知經驗的行為,屬于再造性想象。在格式塔心理學中,此種想象可以看作是對過去經驗的一種創造性加工。首先需要明晰的是,再造性想象與再現性想象不同。再現性想象強調的是對真實的歷史文化知識經驗的選擇性聚焦與凸顯。再造性想象更強調在所觀之物基礎上對其外在形貌與內在意義的再生產。具體到這一時期詩人們的創作來說,這種創造性的加工一方面表現為再造器物表征,另一方面表現為再造視覺空間。
(一)再造器物表征
20世紀美國詩人對中國的再造性想象首先表現為對中國傳統器物表征的再造。斯圖亞特·霍爾將表征定義為“在我們頭腦中通過語言的各種概念對意義的生產”。[1]再造器物表征,亦即在觀看器物之后進行文本創作時所形成的對器物意義的再生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器物不僅具有世俗的功用,而且反映著上下等級的分野與社會風尚的差異。而在20世紀美國詩人那里,來自中國的器物被簡化為用來建構異域形象的符號。對器物的書寫,關涉的也不是激活器物本身的歷史文化記憶,而是重新發明其意義來言說自我。正是在此種有意誤讀的基礎上,器物表征意義得以再造。
在對中國傳統器物表征進行再造的20世紀美國詩人中,瑪麗安·摩爾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詩歌《九油桃》(Nine Nectarines)正是對一件來自乾隆年間的瓷器的摹寫。據清瓷鑒定家陸明華先生研究,“八桃五蝠,為雍正朝典型風格,乾隆朝則多繪九桃”。[2]90因此,摩爾詩中所描繪的正是乾隆年間的粉彩九桃瓷器,寓意祈福長壽。可以確定的是,瑪麗安·摩爾對“九”在中國文化中的寓意十分了解,詩里“鮮紅的桃子/雖不能還生,及時食之亦能延壽”表達的正是此意。有趣的是,摩爾進一步對九桃的排列秩序進行了再造式解讀。詩歌開篇,摩爾將九個油桃的排列秩序描述為:“Arranged by two'sas peachesare,/……eight and a single one.”此處,詩人將九顆桃理解為“一顆與八顆”之間的關系。在她看來,八顆是偶數,且兩兩相傍使桃子得以存活、抵抗凋謝:“at intervals that all may live/……which cannot aid thedead.”[3]顯然,這是對九桃瓷器的過度解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九”代表至尊,九桃在瓶上的排列秩序,多為與枝葉相稱,整體造型平衡得當。無論是一、二、二、四的排列秩序還是一、三、三、二的排列秩序,都不會改變瓷器本身平安祥順、萬壽無疆的寓意。由此可見,詩人的這種創見,是基于美國本土文化與新詩精神需求所創造的新觀念。一直以來,摩爾在詩歌中一直注重用詞精準,大到形狀描繪,小到詞匯選擇,皆安排得極為嚴謹。詩人顯然并不在意對這個精美中國瓷器的摹寫是否真實,因為她真正的目的是要借眼前這九個精心排列的油桃來想象中國。在她看來,九個油桃體現了中國人的“荒野精神”。事實上,正如辛西婭·斯塔米所指出的,荒野是美國最突出的地形特征,在與自然的長期斗爭之中,“荒野精神”早已作為一種民族情感嵌入美國文化內部。作為美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荒野精神”寓意著對自然的征服、開拓和對新世界的無畏與創造。從愛默生、杰克·倫敦,到約翰·繆爾,再到戈特曼,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作家為此種精神的繁盛補充養料。此處,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瑪麗安·摩爾將“荒野精神”賦予中國人,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有意的誤讀。在她看來,這種精神孕育了優秀的中國人,而優秀的中國人才能創造出眼前的杰作。
史蒂文斯在詩劇《三個旅行者看日出》中,則賦予了中國瓷瓶以抽象的哲學內涵。1916年3月上旬,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過一場宋瓷展。史蒂文斯詩劇《三個旅行者看日出》中的核心意象“三個旅行者”正是出自此次展覽上“畫在瓷瓶上的三個人”的形象。表面上看來,該詩講述了一個關于中國的故事:三個中國人,日出之前,在山頂遇到兩個黑人,日出之時,發現自縊而死的意大利人和他的情人。而結合情節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瓷瓶都僅是詩人構建其抽象王國的一個符號,而與實際的中國毫無干系。歷史地看,從元青花梅瓶“追韓信”“王昭君出塞”到清代末期的淺絳彩人物畫,瓷瓶人物畫往往題材固定、筆法古樸,概括起來主要有“文人雅集圖”“高士圖”,以及“嬰戲圖”。顯然,中國瓷瓶上的文人與高士,屬于另外一個過去的時空。斯蒂文斯無意再造那種閑適與隱逸,“這個世界上的鮮活的事物,人,動物,植物——不像觸動濟慈或華茲華斯那樣觸動他;……自然形式,即便得之于特別的賓夕法尼亞或康涅狄格風景,在他的詩歌里也幾乎變得籍籍無名”。[4]47因此,瓷瓶上古樸的人物形象在《三個旅行者看日出》中以擅長思辨的伊壁鳩魯主義者、理智的老者、以及唯美主義者出現。而瓷瓶作為統率全篇的關鍵符指,也被賦予了哲學內涵。瓷瓶在詩中一共出現兩次。第一次是唯美主義者提出“有一處瓷器的幽居,人類從未入侵”,第二次是理智老者的附和“瓷瓶就像大地,它是世代隱士所用”,這兩處對于理解全詩至為關鍵。其實質是在表明,詩歌與美的永恒。但不能否認的是,無論是以瓷器隱喻詩歌,還是將瓷瓶比作大地,都是對現實中中國瓷瓶的一種再造式想象。換言之,詩人選擇瓷瓶與中國人來承載其詩學理想,僅僅是為了給詩歌增添一絲東方情調——“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比那更美的地方了,或者比中國人更美的人了”。[5]
(二)再造視覺空間
所謂再造視覺空間,指的是用文字符號建構空間的色、光、影、線、形,來達成特定時空的藝術在文本中的再造,進而召喚讀者獲得與詩人相似的視覺體驗。通過對這一時期美國詩歌內部存在的天人合一的賓主布局、從心所欲的散點透視視角、象在境外的留白構圖進行辨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山水畫是20世紀美國詩人的靈感繆斯,同時也是他們建構詩意中國的模板。
自1894年費諾羅薩在波士頓美術館籌劃展出了宋代繪畫《五百羅漢圖》以來,不斷有中國繪畫經各種途徑流入館內。這些曾經見證過中華民族風雨與輝煌的遺珍,給許多從未有機會接觸中國古代藝術的美國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華萊士·史蒂文斯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可從他與女友的通信中,確證這段歷史。在一封寫于1909年3月18日的信中,詩人提到了看到這些繪畫的激動心情。他評價其為“我見過的最為奇妙的東西,因為它是如此包羅萬象”。當時,重“直覺感悟、無為和穩靜”的詩人,正苦于有些詩意“用本土文化講不清楚”,而南宋山水畫的出現為其打開了思路:“中國的山水畫畫家的創作靈感和我的詩歌創作的沖動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4]作為南宋山水畫四大家之一的馬遠,擅畫象外之境。他的畫全景不多,多取邊角小景,畫面內容大多是孤舟泛雪一人獨坐。在史蒂文斯的《六幀意義深遠的風景畫》(Six significant landscapes)其一中,我們看到了與馬遠的畫相似的構圖。詩歌開篇:“An old man sits/In theshadow of apinetree/In China”,[6]106構畫出了一個靜坐神思的中國老人形象。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一形象脫胎于馬遠畫中仙風道骨的高士形象。與西方繪畫里人物不同的是,中國山水畫中的人物不會正視畫家或者觀畫者,而是將目光投向客觀物象。于是詩人筆鋒一轉,借老人之眼將目光投向飛燕草與河流。“He sees larkspur,/Blue and white/At the edge of the shadow”,[6]106與此同時,與擅用焦點透視法的西方繪畫不同的是,中國山水畫慣用散點透視來表達空間層次關系。因此,其所呈現出來的空間是流動性的:“He sees larkspur,/Blue and white/At the edge of the shadow,/Move in the wind/His beard moves in the wind./The pine tree moves in the wind./Thus water flows/Over weeds.”[6]106上面的詩句中三次出現“Move in the wind”的動態意象,在賦予了整篇詩歌以境在象外的留白韻味的同時,亦凸顯了宇宙萬物的浩渺無窮。從更深意義上來說,此種空間再造,同樣是在實踐史蒂文斯一直倡導的主觀整理客觀的詩學命題:外在世界是混亂的,只有哲人和藝術家能賦予它秩序和形態。詩篇開頭的中國老人是哲人的化身,同時也是統攝自然萬物的靈魂,飛燕草、河流、不停舞動的風,都因為他的存在而呈現出秩序井然的形態。
斯奈德對中國繪畫的喜愛程度不輸史蒂文斯。自幼年在西雅圖博物館初見中國山水畫,他就一直對其深深著迷:“那年我十一、二歲,走入西雅圖博物館的中國展廳,看到了中國的山水畫。我驚呆了!……中國人眼中的世界與我看到的不謀而合,而隔壁展廳里的英國與歐洲風景畫對我卻毫無意義。”[7]為參透其中所蘊含的創作法則與哲學意蘊,詩人不遠萬里走訪了中國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館。在小說《達摩流浪漢》中,他更是借杰費(小說中的斯奈德的化身)之口表達了自己的創作野心:“你知道我將做什么?我將寫一首新詩,叫做《山河無盡》,在一幅畫軸上一直寫一直寫,打開畫軸,總有新的驚奇,……像真正的絲絹中國長軸畫,有兩個小人在無盡的山水中行走,有扭曲的老樹,還有群山,山高到融入絲絹空白的云霧之中。”[8]157此處,斯奈德所描繪的畫面出自中國佚名山水畫卷《宋人溪山無盡圖》。而其《山河無盡》的卷首詩《溪山無盡》,便是對這幅畫卷的絕佳臨摹。
關于《宋人溪山無盡圖》的作者,學界尚沒有定論。鑒賞家楊懋稱其為:“誠得真山水之深趣,非當時名筆有大才者,不能至此。不必問其誰何,可為神品。”[9]313因此,關于此畫作者為誰,又如何流入波士頓美術館,這里不再贅述。在中國山水畫《宋人溪山無盡圖》中,居于主位的是重巒疊嶂與無盡溪流,小山、小路和行人居于賓位,對整個畫面進行烘托。因此,在《溪山無盡》中,詩人盡量縮小敘述者“我”的存在,將自我消融在山川溪水之間。“Clearing the mind and sliding in/to that created space,/a web of watersstreamingover rocks/air misty but not raining,/seeingthisland froma boat on alake/or abroad slow river,/coasting by”[10]5而詩歌布局方式,則借鑒了中國山水畫常用的散點透視構圖法,即視角不受空間限制,隨意移動。由此,全詩擺脫了“只合見一重山”,不見“溪谷間事”的視覺局限性,最終達到“重重悉見”的理想效果。個體觸目所及,仰視有山寺屋頂,如花蓬現,遠視有懸崖絕處,古剎隱嵌,平視旁有幽徑,逶迤至此,天地萬物,并置于方寸之間,整體上卻呈現出廣闊浩渺之感。待到游覽完畢,詩人仍沒有忘記運用山水畫中的布白來模擬溪山無盡:“grind the ink,wet the brush,unroll the/broad white space:/lead out and tip/the moist black line”[10]9一如馮民生所言:“中國繪畫空間既不是對物理死寂的空間描摹,也不是任意想象的空間臆造,而是在對宇宙空間生命的感受中所展開的重構和再生。”[11]21事實上,正是這種對宇宙空間獨特的感受方式,賦予了中國山水畫境在象外、綿綿無盡的浩渺之感。可以說,斯奈德從中國山水畫中習得了其獨特的自然詩歌創作模式,而牽引著詩人師法中國山水畫的動力,則是詩人想要在有盡的詩歌里尋求無盡的詩學理想。也正是在此種意義上,《溪山無盡》奠定了整部《山河無盡》的時空結構。
二、互文性想象
互文性想象是這一時期美國詩人建構中國形象的又一重要方法。“互文”指的是符號系統間的一種互涉關系,它生成于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強調的是“文本間性”。在克里斯蒂娃看來:“任何文本內都是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另外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編。”[12]3620世紀美國詩歌對中國形象的建構,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互文性想象生成的,具體可分為仿擬性互文與粘貼性互文。
(一)仿擬性互文
熱奈特將具有派生關系或嫁接關系的互文本分為底本與承文本。底本即原文本,承文本指由原文本派生或嫁接而來的文本。所謂仿擬性互文,意味著承文本從底文本中提取某種富有特征的文本范式,以表達不同于底文本原有文化語境的意義。讓·米利對仿擬性互文如此定義:“仿作者從被模仿對象處提煉出后者的手法結構,然后加以詮釋,并利用新的參照,根據自己所要給讀者產生的效果,重新忠實地構造這一結構。”[13]47具體看來,此種互文既包括對文體的仿擬、對句法結構的仿擬,也包括對立意的仿擬。
雷克斯羅思的《金斯河峽谷》是對元稹悼亡詩《遣悲懷》的文體仿擬。該詩為詩人哀悼妻子安德烈·雷克斯羅思所作。開頭詩人筆調哀婉,“我的悲傷寬得/一眼望不到邊/深得永遠探不到底”[14]289,仿擬《遣悲懷》首句“閑坐悲君亦自悲”,直抒對亡妻刻骨銘心的思念。極致的悲傷后,詩人將視角轉向自然界,天上的月亮并不知道人間的疾苦,“月亮落入幽深的霧中,/好像金斯河峽谷/裝滿了細密、潮濕、溫暖的紗布”[14]289,詩人觸景生情,回想起與妻子相處的點點滴滴:在望景崖,“我們第一次/窺見月亮的這個峽谷”,“在秋天安靜的/池塘邊,/我給你烤了一個玉米生日蛋糕。/你畫出你最美的畫作”[14]290。言語之間的不舍與憐惜,頗有元稹“昔日戲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來”之感。與西方悼亡詩多選取抽象意象表達感情不同的是,中國悼亡詩多選取現實意象來借景抒情。因此,在妻子過世后,元稹回憶她時,想到的是:“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一如蔣寅所指出的:“自韋應物之后,夫妻間日常生活瑣事和喪葬經過寫入悼亡詩中,成為詩家慣例。”[15]此處,露營、烤玉米生日蛋糕以及作畫,皆是夫妻間一些瑣碎之事。但在妻子故去之后,卻顯得如此美妙。想到斯人已去,滿月依舊,雷克斯羅思悲從中來,“想起元稹偉大的詩篇/凄切得叫人無法忍受”。[14]291傳統西方悼亡詩,神圣、充滿希望。勃朗寧在《最后一次同乘》中,希冀自己死后能與妻子重逢在天堂:“讓這一瞬間化作永恒,/——證明天堂就是我和她永遠同乘,/同乘,同乘到永遠?”[16]191彌爾頓在《悼亡妻》里則將對妻子的愛升格為基督之愛,“我的妻,由于古戒律規定的凈身禮/而得救,洗凈了產褥上斑斑的玷污/這樣的她,我相信我還能再度/在天堂,毫無障礙地充分地瞻視”。[17]而此處,詩人寫出的是與元稹《遣悲懷》中“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同樣的絕望之愛,“在春水邊,我孤獨,/比我以前能想象到的/更為孤獨”[14]291,將中國悼亡詩的凄美、哀怨展現得淋漓盡致。可以說,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雷克斯羅思重新激活了中國文化空間的象征意義,打開了一個關于中國詩學與美國詩學的對話空間。
威爾士的詩集Quietly in Harpswell.Poems after Wang Wei則是在仿擬王維詩歌句法結構的基礎上寫成的。在詩集序言中,詩人坦陳:“The verses that follow are based on poems by the celebrated poet-painter Wang Wei…in so many ways to the environs of the cottage in Maine where I have spent over thirty happy summers,I have undertaken a somewhat novel,though by no means wholly new,type of literary transposition.”[18]3此處,威爾士所謂的新奇的文學轉換,指的便是跳出西方詩歌的傳統,在句法結構方面師法王維的五絕山水組詩《輞川集》。我們以集子中的兩首詩作簡要對比:

《輞川集》的特色在于詠景五絕的體制形式和幽玄淡遠的風格特征。Morning After Rain對《輞川集》的仿擬,主要取其句法結構。首先是斷句。傳統英語詩歌,斷句多以韻腳劃分,而此詩卻以意象劃分。除詩歌第一句以外,全詩每句都在兩個意象之間斷句(Evergreens shine,Spring smoke veils wood,Mayflowerswither,Sunriseclouds,Birdssing,Oneguest)。這種斷句法,脫胎于《輞川集》中每句在二、三字間停頓的節奏(舸和迎、悠和湖、軒與對、面與芙)。其次是用韻。“英國詩歌之父”喬叟所開創的詩歌雙韻體,發展到17世紀,逐漸被“素體詩”所取代(即五音步抑揚格詩行,不用韻),隨后,美國詩人惠特曼更是以無韻自由詩《草葉集》奠定了20世紀美國詩壇的創作傳統。然而,在《安靜地在哈波斯維爾:擬王維》組詩中,威爾士卻重拾了詩歌用韻的魅力。只是,與傳統英語詩歌多用多元韻式不同的是,這首詩的用韻格式仿擬了《輞川集》的一元韻式,即一首詩一個韻腳。《輞川集·臨湖亭》二、四句押陽平ai韻,Morning After Rain的第二句和第四句末尾詞hill和still也進行了單音節押韻。可以說,《輞川集》為威爾士提供了一個書寫自然的新視角,而通過對這一文本句法結構的仿擬,威爾士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渴慕。
斯奈德《松樹頂》則是對蘇軾《春宵》立意的仿擬。據斯奈德本人介紹,《松樹頂》師法了《春宵》通過日常事物來表達禪理的藝術。蘇軾原詩為:“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秋千院落夜沉沉。”全篇用語通俗卻立意深沉。在對外在物象的描寫中,含蓄委婉地表達了對醉生夢死的人的譴責。斯奈德的《松樹頂》全詩為:“藍色夜晚/霜的霧靄,月亮/讓天空閃光/松樹之冠/被藍雪壓彎,漸漸隱入/天空,霜,和星光。/靴子吱吱響。/野兔的痕跡,鹿的痕跡,/我們只認得這些。”[19]213在對藍色的夜、微微發亮的天空、融入天空的松樹頂,以及瀉下的月光與漫天的星光等自然的描寫中,詩人表達了對美麗神秘的自然界的崇敬之情。末句“我們只認得這些”,含蓄地批判了現代人類面對自然時的無知,倡導了人類和自然需要協調融洽的環保意識。從此種意義上來說,斯奈德正是在對中國詩歌仿擬的基礎上,拓展了自身的文化格局,建構了詩意盎然的中國化空間。
(二)粘貼性互文
所謂粘貼性互文,指的是通過向前文本提取要素,來重新組合生成的主文本。這種互文方式,意在刻意凸顯前文本的異質性,來與主文本的其他詩行形成斷裂,進而達成對前文本符號意義的凸顯。
20世紀的美國詩人對中國前文本的粘貼,主要采用的為內嵌式形式。所謂內嵌式粘貼,指的是源文本被鑲嵌進主文本,進而成為其構成要素。賴特詩歌《冬末,越過泥潭時想到了古中國的一個地方官》里,開頭“And how can I,born in evil days/And fresh from failure,ask a kindness of Fate?—Written A.D.819”[20]119直接粘貼自韋利所翻譯的白居易《初入峽有感》,原文為:“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這一設置,奠定了全詩的基調與主旨,也表達了詩人希圖與白居易進行跨越時空對話的用意。對話的開始,詩人想象白發蒼蒼的白居易在湍急的長江三峽溯流而上時,應是格外寂寞:“我想起你/惴惴不安地進入長江三峽/纖夫拉著你的船逆流而上/送你去忠州城里”。[21]因為,1960年的詩人,隔著遙遠的時空,正在體認著同樣的寂寞:“又快到春天了/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大石頭/造成了我獨有的沉沉暮色/也有纖繩和激流”。[21]身處“什么也看不見/除了那株可怕的經冬而愈黑的大橡樹”的明尼阿波利斯城,詩人渴望從白居易那里尋求一點慰藉。結尾,詩人悵惘地追問:“你在山那邊找到孤零人的城市了嗎?/還是緊握著那條磨損了的纖繩的一頭一千年都沒有放手?”[21]這一追問,與其說是面向白居易,不如說是面向詩人自身。遙遠的古中國詩人,某種程度上是詩人自身的鏡像。其緊握纖繩一千年不放手的形象是詩人想象視閾中的幻象,同時也是指引詩人擺脫窘困現實的希望。
這種通過粘貼中國古典文本來觀照自身的寫法,在龐德的詩歌中同樣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但比賴特走得更遠的是,龐德直接在詩歌中粘貼漢字。早在費諾羅薩那里,漢字就被稱為“表現大自然的行為和過程的生動的速記圖畫”[22]。作為費諾羅薩美學思想的忠實擁護者與傳承者,龐德更是將漢字象形、會意的重要功能發揚光大。在龐德的理念中,兼具詩意與視覺動感的漢字,本身就是一種意象,“一切思想都經過它而不斷地沖進沖出”[23]。據學者王偉軍統計,整部《詩章》中,中國漢字共計147個。我們以“旦”與“中”為例,來進行說明:
北風與它的麒麟同來
令下士心碎
閃耀的黎明旦在茅屋上
次日
有絞架看護的影子
比薩的云無疑森羅萬象
絢麗和我迄今所見的一樣
(比薩詩章·第七十七章)
旦字,象形兼會意。字從日,從一。一指代(東方)地平線。因此,日與一聯合起來象征日出東方。《漢書·劉向傳》中:“不寐達旦。”這里的旦,便作早晨解。此處,龐德直接將漢字粘貼于詩中,一方面念及英語里的dawn(黎明)跟中文的“旦(dan)”字諧音;一方面是取其象形、會意功能,以圖說“閃耀的黎明在茅屋上”的盛景。其被鑲嵌于詩歌之內,造成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同時表征著詩人對地上樂園的期許。
懶惰熟悉土地和雨露
但讓他們只守三周Chung
我們懷疑中
政府不會信賴這個中
(比薩詩章·第七十六章)
從詞源上來說,中最早見于甲骨文,為象形字。意指中間,引申義為內、里、中心,后又引申為一半、得當、符合等義。在儒家看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這里,龐德取其中庸之義,表征理想社會的倫理秩序。龐德一直認為,中庸是政治家必須具備的品質。同時,他也清醒地意識到,這一理念在美國并不會得到實施。此處,詩人通過刻意凸顯漢字“中”,表明了要想實現繁榮昌盛的太平景象,必須實踐儒家思想的政治態度。
三、相反性想象
相反性想象是這一時期美國詩人想象中國的第三種方式。所謂相反性想象,是指從一個審美對象的相反面去想象另一個審美對象。在薩特那里,相反性想象的動力機制是匱乏:現實越是匱乏,想象活動的創造性反而越容易被激發出來。在20世紀美國詩人建構中國形象的過程中,這種相反性想象隨處可見:和諧的歷史中國構成了混亂的美國現實的反面,而友善的現實中國則構成了奉行霸權主義行徑的美國的反面。
(一)混亂與和諧
在相反性想象中,作為想象客體的現實美國和歷史中國在表象上就具有截然相反的特質:歷史中國是農業社會,遵循的是男耕女織的農業文明模式,整體上呈現出天人和諧的面貌。這種和諧,概括起來有三層意思:其一,人與自然的和諧;其二,人際關系的和諧;其三,國家與民族的和諧。而20世紀的美國是現代化社會,物質文明得到大幅度發展,但同時也充滿混亂。這種混亂既表現為戰爭動亂、也表現為價值觀混亂。身處混亂之中的美國詩人,通過將歷史中的中國與現實中的美國進行比對,建構了天、地、人和諧的古代中國形象,表達了對混亂現實的不滿與批判。
齊格蒙·鮑曼在《對秩序的追求》中將混亂定義為“無秩序的一切”[24]。同時,他清醒地認識到,戰爭——作為一種追求秩序的行動,會產生出新的混亂。在龐德看來,“如果國君體內沒有秩序/他就無法在自己的領地內整頓秩序”。[25]689因此,詩人對戰爭深惡痛絕。《比薩詩章》正是這種對戰爭進行撻伐的詩歌。詩歌寫于二戰末期。當時,詩人正因“叛國罪”被囚于比薩附近的美軍監獄,陪伴著他的,只有隨身攜帶的《大學》和《中庸》。目睹昔日繁榮的現代都市,如今支離破碎、滿目瘡痍,詩人不禁感嘆戰爭所帶來的巨大毀滅,“夢想的巨大悲劇落在農民/彎曲的雙肩”[26]3。反觀歷史中的中國,那里恍若天地初開,“如舜在泰山上/在祖宗的廟堂里/如同自神跡初萌/堯的圣靈,舜的/真誠,禹這位治水者的憐憫”[26]11。此處,歷史中的中國既是一個確切存在的地理空間,同時也是詩人對于美好世界的符號性想象:秩序井然、生機勃勃。這種想象出來的天地越是和諧美好,現實的困窘越是顯得難以忍受。從此種意義上來說,相反性想象指向的與其說是逃遁,不如說是質詢。面對殘破的歐洲,詩人憤怒追問:“《圣經》里講的啥?《圣經》有哪幾本書?說說看,甭想糊弄我。”[26]13然而,詩人清醒地認識到,《圣經》并不能為美國帶來和諧,孔子關于“誠”的教導才是指導美國走向和諧的正確路徑:“獻給國家的禮物莫過于/孔子的悟性”。[26]59此處,詩人提到的“誠”,來自《中庸》里的核心思想:“誠者,天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意為真實無妄是天地法則的運作規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誠”的意義不僅于此,它甚至被當作天地化育過程的原初動力:“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中庸》)也正是在此種意義上,龐德對“誠”這一古老的東方命題推崇備至。在他看來,“誠”不只是個人道德水平的自我完善,更代表著永恒真理。而政客們為了獲得利益,“用屁眼給大眾演講”“為保飯碗而撒謊”[25]61,則是對“誠”的背棄。因此,面對美國當代領導人對中國傳統的蔑視,詩人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慨:“對唐史一無所知的傲慢的野蠻人用不著騙誰。”[26]5美國一向自詡為文明國家,美國白人更是以文明人自居,此處詩人卻斬釘截鐵地將其定義為傲慢的野蠻人,不僅有力地駁斥了殖民思維下的世界文明秩序論,同時也使詩歌內部充滿了巨大張力。
與此同時,20世紀美國的混亂,還表現在由資本主義現代化所帶來的精神的日益萎縮與頹廢。酒精、縱欲、拜金主義是此種混亂的表征。“不計其數的家庭為子女抽煙酗酒和整夜開車兜風引發的爭吵無比頭疼。”[27]82這種混亂不僅“把各種精神焦慮植入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28],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20世紀美國詩人的創作。他們從頹廢、放蕩的現實出發,想象文明、和諧的古代中國,希圖從中找到療愈的良藥,重新恢復現代人類內在精神的和諧。林賽的《中國夜鶯——壁氈上的故事》,正是這種嘗試的體現。眾所周知,20世紀初,美國城市化得到大幅發展。以紐約、舊金山為代表的現代化大都市,更是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詩歌開頭,詩人卻描繪了一幅現代荒原景象:“舊金山沉睡著,好像死去,/死于縱欲、游樂、淫冶、放蕩”。此處,縱欲、淫冶、放蕩的舊金山,與幾年后艾略特在《荒原》中呈現出的荒涼、空虛、毫無生機的倫敦一樣,都表達了現代人精神的混亂、悵惘與荒蕪。只是與艾略特將拯救荒原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不同的是,林賽將眼光投向了歷史中的中國。在詩人看來,與動蕩、縱欲的現代社會相比,古代中國才是夢想中的太平盛世:“我們生活在偉大的時代,孔子后來說那是盛世。”在這種文明滋養下的“張”——一個洗衣工,因此可以在瀕死的舊金山心平氣和地整夜熨燙:“有一個景象使我心滿意足,/我看見綠色的樹,高飛的翅膀,/我從上海帶來的不死鳥在歌唱。”接著,詩人借不死鳥之口贊頌中華文明:“當全世界的人還在茹毛飲血,……當全世界還在用石棍石刀,/我們卻在香料樹下品嘗茶味,……我們抄深奧的書,/把玉雕鏤,/我們在桑樹下織藍色的絲綢……”[29]172可以看出,詩人所謂的盛世,不只在于物質文明的繁盛,更在于精神文明的豐盈與生活狀態的恬淡、自然。而這也正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所在。無論是儒家的“反求諸己,盡心知性”(《孟子·離婁下》),還是道家的“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德經》),都在強調人之形體與精神的合一。因為只有合一,人們才能“從自己的形骸、功名利祿和外在聲名的限制中解脫出來,達到與天地精神獨往來的道德人格的最高境界,以獲得精神上的絕對自由”。[30]從此種意義出發,對于20世紀的美國詩人來說,遙遠的歷史中的中國,代表著人類可以把握的和諧、統一的整體,而牽引著他們對這一空間凝望的動力機制,正是對動蕩、頹廢的混亂現實的重新整合的欲望。
(二)霸權與友善
所謂霸權,意指肆意干涉別國內政,以謀取主宰世界(或地區)事務的權利的主張、政策和行動。縱觀美國20世紀的全球戰略,最顯著的特征便是擴張戰略、霸權意識。作為這一系列霸權行徑的親歷者,20世紀的美國詩人,通過將美國的擴張、掠奪與現實中國的友善進行對比,批判了美國霸權意識的運作機制與內在困局,同時呈現了被官方權力話語所遮蔽的真實中國。
首先需要明晰的是,友善作為一種倫理秩序,主要表現為內在本性善良,對外親和友愛。推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友善指相互尊重、互不侵犯。然而近代以來,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為奪取世界霸權,一再挑戰此種倫理秩序。蘭斯頓·休斯《怒吼吧,中國》,正是反抗此種世界霸權行為的產物。該詩作于1937年,此前四年,詩人曾取道日本到過中國,并與中國的左翼作家們有過正式接觸。在其為期三周的訪問中,中國人民的熱情友善與艱難困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20世紀美國最杰出的黑人詩人之一,詩人不僅為美國黑人發聲,同時也將同情傾注到了黃皮膚的中國人身上。在他看來,飽受美國霸權主義欺凌的中國人民與深受美國種族主義之害的黑人有著共同的命運。在詩的開篇,詩人誠摯地歌頌了中國人民的友善:“打遠古起你從來不/竊取別人的東西。”此處,竊取與占領,都代表著對他人作惡。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友善既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也包括“推己及人”的體諒之心。詩歌雖然寫于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之時,但是詩人的矛頭對準的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利用中國人民的友善,在中國的大地上實施的霸權行徑:“他們乘著炮艦來了,/建立租界/勢力范圍/公共租界/傳教堂/銀行/種族隔離的青年會。/他們用馬六甲藤條打你,/要是你膽敢抬頭——/他們就會砍掉你的腦袋。”面對“再沒地方精繪瓷器,/吟詩作賦/……不再有安定”的現代中國,詩人痛惜不已,并且期待著它能強大起來,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尊嚴:“怒吼吧,中國!是噴火的時候了!/張開你的嘴,東方的老龍,/吞下揚子江里的炮艦,/吞下你天空中的外國飛機,/制造焰火的老技工,吞下子彈——/再朝敵人臉上吐一口自由的唾沫!”[31]47
值得注意的是,霸權行為的實施往往假借正義之名。垮掉派詩人金斯伯格的批判,著重指向的便是此種顛倒黑白的話語建構。具體看來,他對此種話語建構的批判,主要是借助于相反性想象以對比實施霸權主義的美國與友善的現實中的中國來達成的。在《梵高之耳揭秘》中,詩人替中國的抗美援朝辯護。當時,美國政府將朝鮮戰爭宣傳為由蘇聯策劃的一樁企圖聯合全世界所有共產黨人向資本主義國家進攻的陰謀,而中國的抗美援朝則是對美國的一種明白無誤的挑戰。對此,詩人直接將中國指認為“被欺辱的天使”。在他看來,如果美國繼續一意孤行的話,有朝一日,被欺辱的中國天使“必將會把我們從未來的金色之門趕出去”[32]151。在《贊歌》中,詩人抨擊美國政府的冷戰思維,認為他們渲染的中國形象,“并非真實的中國”。在《維基塔中心箴言》中,這一批判更為明顯。該詩寫于越戰時期。當時,美國為了建立起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大肆渲染戰爭的必要性與正義性,并將中國、越南等國家指認為邪惡的威脅。在這一大背景下,詩人直截了當地指出,“所有這一切黑色語言/都是由權力體制寫成”!在鋪天蓋地的戰爭宣傳下,普通民眾根本沒有辦法接觸到事實的真相。因為,“戰爭就是語言/語言已經被濫用/出于廣告和宣傳/使用語言/就像是變幻魔法在這個地球上稱王稱霸爭權”。與精心編造的謊言相對的是古老東方的格言。它充滿智慧,但卻因為“老而無用”,已經早早被政治家們棄置一旁。面對美國領導者企圖以民主的形式掩蓋霸權,詩人毫不留情地將平靜的美國鄉村指認為“這就是向中國發起戰爭的土地”[32]259。可以說,通過不斷插入相反性的話語,詩人強化了真實/話語之間的二元對立。由此,政客們傳達的“真相”被還原為虛構和謊言,中國——這一被指認為邪惡的存在,得以被還原為正義之邦。而中越人民的反抗,也被重新定性為尋求和平。從此種意義上來說,金斯伯格的目的與其說是對美國霸權行徑的揭露,不如說是通過戲謔、對抗的話語來使大眾清醒地了解霸權意識的運作機制,進而完成對所謂官方真實的解構。顯然,后一種具有更為深遠的影響。
四、結 語
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以“歐洲的落后形式”而存在。而在20世紀美國詩人這里,中國形象呈現出一種多樣性、開放性與交互性。中國器物和山水畫是他們想象中國的最初動力。通過再造器物表征與再造視覺空間,他們在想象的層面上“抵達”了中國,打開了一個關于中國藝術與美國詩歌的對話空間。通過與中國古典文本的互文性想象,汲取其中關于政治、人倫、自然經驗的啟示,他們逐步形成了獨特的創作模式與創作理念,并以此為鏡鑒,對置身其中的美國現實進行了反思與批判。而此種以中國古典文學文本為媒介來想象中國的方式,最終也將地理層面的中國升格為了文化層面的中國。同時不能忽視的是,相反性想象的運用,使他們得以更為深刻和復雜地理解中國。通過將和諧的歷史中的中國與混亂的美國現實,友善的現實中的中國與奉行霸權主義行徑的美國進行比對,20世紀的美國詩人跳出了歐洲中心主義視野,呈現了被官方權力話語所遮蔽的真實中國。總的來說,20世紀美國詩人對中國的想象,賦予了20世紀美國詩歌以瑰奇的想象空間,同時也使詩歌內部充滿了巨大張力,這不僅拓展了美國詩歌的文化格局,而且有力地駁斥了殖民思維下的世界文明秩序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