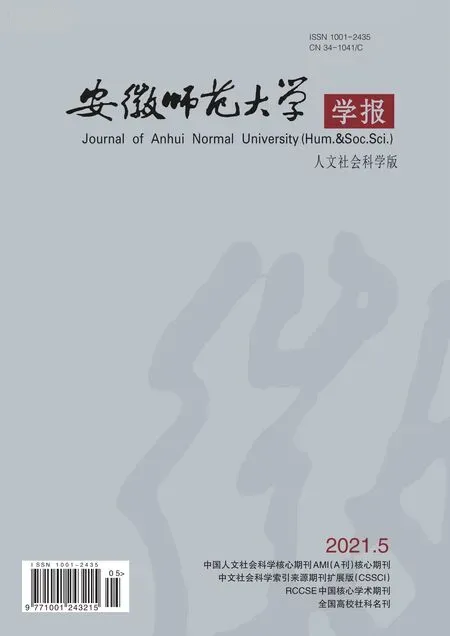明代福建地區的科舉競爭與地域專經*
丁修真
(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安徽蕪湖 241002)
正統元年(1436)春會試,翰林院侍講學士,江西泰和人陳循出任考官,面對紛紛落榜的士子,不由發出“棄璧之嘆”:
有司奏定以四方分為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于百人,南十之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經之多寡,每經七取其一,《書》最多,《詩》次之,《易》《禮》《春秋》又遞次之。左限右隔,是以各方之士同治一經,往往自相戰取先后。雖有該博之學者,不得以此而勝彼,雖無超卓之才者,亦可以此乙而勝甲。定制所在,縱智者亦無如之何,此余所為不能無棄璧之嘆也。[1]143從陳循的言論中,可以看到影響明代科舉取士的兩個重要設計,一是分卷錄取,二是分經錄取。本文討論聚焦于后者。現有研究已證明,明代從鄉試至會試中,士子錄取,按照五經各自比例進行。[2][3]因此“各方之士同治一經”者,需“自相戰,取先后”。治《易》者不會與治《書》者“同場競技”,即使前者學識遠勝于后者,也會因本經名額“定制所在”而落榜,是故,陳循才會有“棄璧之嘆”。這也意味著,在考察明代科舉取士的錄取結果時,除地域因素外,需注意因“同治一經”而引發的競爭關系。
由分經取士所引發的競爭關系及其表現,學界目前的討論尚不多見。事實上,尤其是在鄉試層面,因地方士子面臨的競爭激烈程度要遠高于會試,①據學者研究,明代會試的平均錄取率在8%左右,鄉試則要低至4%左右,而參加鄉試的生員數目更是遠遠大于會試人數。見郭培貴:《明代科舉各級考試的規模及其錄取率》,《史學月刊》2006年第12期。所以在解額與五經錄取比例固定的情況下,考察這樣一種競爭關系如何呈現,又如何演變,無疑會成為深化科舉人才地理認識的一個取徑。
有鑒于上述思考,本文以明代福建地區鄉試錄匯編《閩省賢書》(以下簡稱《閩書》)為依據,②現存《閩省賢書》有三個版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有康熙刻六卷、續一卷(以下簡稱康熙本)和清孔氏岳雪樓六卷的抄本(以下簡稱清抄本),分別藏于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此外尚有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崇禎刻本。三個版本在中式者信息的記載均存在差異,利用時需要注意。本文涉及各類圖表的數據,主要依據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碩士生杜曼秋在整理過程中襄助頗多,特此說明與致謝。在統計明代福建90科鄉試錄取情況的基礎上,以專經為視角,具體分析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數、變化趨勢以及消長關系,進而考察明代福建鄉試中所呈現的競爭關系及其變化過程,以期深化相關問題的討論。③從科舉地理與科舉家族兩個維度來看,涉及福建地區研究的有:劉海峰《論“科舉學”的廣博性——以福建科舉為例》(《東南學術》2001年第2期)概述了福建自唐至清的科舉發展脈絡,并簡要統計分析了各府科舉的發展狀況。多洛肯《明代福建進士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版)作為專門研究福建進士的著作,考察了明代福建進士及其地理分布的情況。季平《明代福建進士的地域分布研究》(《教育與考試》2009年第6期)從府縣兩個側面分析進士分布的不平衡性,同時從縱向的時間上分析了各府在不同年間的中舉名額。戴顯群《明代福建科舉盛況與科名的地理分布特征》(《教育與考試》2013年第5期)在總結分析前人對進士人數的考證和統計的基礎上,探究福建舉人和進士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影響其的主要因素。葉可汗《明代福建進士家族研究》(遼寧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以福建地區的進士家族為研究對象,歸納其地理分布特點及成因并分析進士家族形成的原因及影響。在第二小節中簡要敘述了福建鄉試與舉人地理分布。郭培貴、蔡惠茹《論福建科舉在明代的領先地位及其成因》(《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在概述明代福建科舉出色的表現的基礎上,不僅從經濟發展、官方與民間教育、文化發展、科舉氛圍等方面分析地方科舉發達的原因,并且探討了福建進士家族綿延之長的原因。蔡惠茹《明代福建科舉家族的時間分布及其成因》(《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和《明代福建科舉家族的規模、代數構成及空間分布》(《中國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分別從時間和空間上探究福建科舉家族的分布情況。
一、明代福建鄉試中各府的錄取情況及其變化
本文根據《閩書》收錄的明代福建90科鄉試名錄,對各府的錄取人數進行了初步的統計,同時結合各府人數變化的階段特征,進而分成洪武—永樂、宣德—景泰、天順—嘉靖、隆慶—崇禎四個時期,以便揭示其發展趨勢。④考慮到行文整潔及閱讀方便,本文暫不羅列90科鄉試各府的所有數據,惟在說明具體問題時,列制相關表格;公元紀年只標注代表性年份,余則省略。
表1中的第一階段,明代洪武至永樂年間,是鄉試“不拘額數”的運行時期。福建省在這一階段錄取人數最低值為洪武四年(1371)的18人,最高為永樂十八年(1420)的145人,有記載的舉人數共1 355人。具體至各府,福州府中式536人,接近總錄取人數的之半,可謂一家獨大;建寧府、興化府、泉州府分列二、三、四位,因人數接近,均可歸入第二梯隊;汀州、漳州、延平、邵武四府分列末位,是為第三梯隊。可以注意到,上述排名靠前的地區,除建寧府外,均為福建濱海之地。

表1 明代福建鄉試各府科舉人數排名
第二階段,宣德元年(1426)至景泰四年(1453),為明代鄉試解額制運行初期。福建鄉試額數初定為45名,較此前大幅下降,受此影響,各府錄取人數銳減,排名也隨之變化。福州府仍然以276人傲視其余各府。此前排名第二的建寧府則以44的總人數下滑至第四。興化府、漳州府升至第二與第三。從各科年的錄取情況來看,在解額實施之初,建寧府尚能與興化、漳州等地相抗衡。但在景泰元年、四年間再度不拘額數錄取的情況下,其他各府均實現了人數的大幅增長,惟有建寧府不升反降,造成其總人數上的落后。
第三階段,景泰七年以后,明代鄉試解額基本固定,除萬歷四十三年(1615)至崇禎十五年(1642)人數略有微調外,福建地區的解額人數長期維持在90人左右。這一時期主要的變化趨勢,是此前一家獨大的福州府逐漸失去了領先優勢,興化、泉州、漳州等地輪番實現人數上的反超。這一過程又可分成天順—嘉靖、隆慶—崇禎兩個時期。
天順至嘉靖時期的主要變化,是泉州府逐漸實現對興化府和福州府的超越。從總人數看,這一時期,福州府1 205人仍列第一,興化1 000人緊隨其后。但若觀察具體科年人數(表2),可見二府優勢的逐步喪失。以泉州府崛起為說明,景泰七年至成化十六年(1480)的9科鄉試中,錄取人數尚不及排名第四的漳州府。成化七年一科,泉州只有1人中式,漳州府有6人。成化十三年,泉州府3人錄取,漳州府有14人,且在個別科年甚至要低于第五位的建寧府。然而從成化十九年始,泉州府迅速實現了對漳州府的反超,不過與興化府、福州府的差距仍然較大。

表2 景泰—成化時期福建各府鄉試人數
至嘉靖年間,泉州府在人數上已遙遙領先漳州府,并逐漸完成了對興化、福州府的趕超。從具體科年看,嘉靖四年(1525)泉州府11人中式,至七年、十年兩科鄉試,大幅增長為28、27人,暫時超越興化府。至嘉靖三十七年,泉州府中式33人,接連完成對福州、興化兩地的趕超。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時期,漳州府的人數也在迅速增長。(表3)

表3 嘉靖時期福建各府鄉試人數
從隆慶至崇禎,泉州與漳州已經完全取代了福州、興化二府的領先地位。隆慶四年,泉州府錄取人數高達51人之多(表4),占福建鄉試錄取人數一半之多。甚至在一些科年中,福州與興化二府錄取人數之和不及漳州一府。萬歷十年,福州16人,興化8人,漳州31人。萬歷十九年,漳州府23人,福州府11人,興化府8人。從嘉靖末至隆慶初,十余年之間,福建地區科舉地理格局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此消彼長,興衰倏忽。清人施鴻保認為“明時,興化、泉州科甲最多,鄉試每占通省之半”[4]10b,反映的正是此時期的情況。

表4 隆慶—萬歷時期福建各府鄉試人數
綜合上述變化,可以看到,明代福建地區的鄉試競爭關系,隨著明代解額制度的調整,主要呈現為明初福州府一家獨大,至明代中期福州、興化二府兩強相爭。嘉靖以后,泉州府、漳州府迅速崛起。建寧、汀州等四府除在明初鄉試“不拘額數”階段尚有可觀外,其余時期內基本處于被“壓制”的局面。那么,這樣一種階段性變化,與“士之同治一經”所產生的競爭關系又有怎樣的聯系?
二、明代福建鄉試中各府的專經與競爭關系
根據《閩書》,輔之以及福建地區科舉名錄,本文共統計福建地區73科鄉試中本經可考者6 540人,其中業《詩》者最多,為2 074人,占總人數的32%左右;其次為習《易》者,1 995人,占總人數的30%左右;習《書》經者1 438人,占總人數的22%;習《禮記》者與《春秋》者較少,分別為494與539人,分占總人數的8%。這些數字代表著明代福建省“同治一經”競爭中的勝出者。《詩》《易》《尚書》人數占多,而《春秋》《禮》絕少的習經分布,也為科舉時代之共相,主要原因在于士子考試中的“趨易避難”。[5]
如上文所述,明代福建鄉試的格局變化,主要體現于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四府之間。故下文將以四府的習經人數為對象,考察各府專經的表現及其變化,進而分析因專經而產生的競爭關系。
1.《詩》經與漳州府的崛起
在統計的2 074位習《詩》舉人中,福州府647人,占總數比重31%;興化府541人,比重為26%;漳州府388人,占比19%;泉州府243人,占比12%。福州、興化二府士子在《詩》經的競爭中有明顯優勢。從變化趨勢看,福州、興化府的優勢主體現于嘉靖以前,至嘉靖后期,漳州府和泉州府《詩》經的競爭力有了長足的進步。具體表現為:成化以前,福州府在《詩》經人數上遙遙領先;成化以后,興化府逐漸趕超,形成兩強爭鋒的局面,一直維持至正德十四年(1519)前后。至嘉靖初,泉州府、漳州府的人數開始增加,興化府開始減少,福州府則略有回升,四府在《詩》的競爭中陷入膠著狀態。從萬歷年間開始,漳州府的優勢愈發明顯,福州府則對泉州、興化保持著微弱的領先。(圖1)

圖1 明代福建四府《詩》經中式人數的變化
整個明代,漳州府通過鄉試產生的舉人數在1 000余名,不及福州府半數。《詩》經人數同樣如此。但因在短時期內集中爆發,故在明代后期成功趕超福州府。漳州府下轄的漳浦縣,其在明代共產生舉人180余名,人數在全省排名第12,其中《詩》經舉人138人,排名第五,人數主要集中于嘉靖后期。與此情況相反的福州府長樂縣,《詩》經總人數188名,位列全省第3,在嘉靖以前,均科《詩》經人數在5人左右,嘉靖以后,卻經常出現連科不中的局面。圖2繪制的兩縣《詩》經中式人數的變化,可以視為漳州、福州二府競爭關系下,此消彼長的一個縮影。

圖2 明代福建長樂、漳浦二縣《詩》經中式人數的變化
2.《易》經與泉州府的崛起
在本文統計的1 995位《易》經中式者中,泉州府831人,占比42%;福州府552人,占比28%;漳州府303人,占比15%;建寧府193人,占比10%,興化府占比過小,在此暫不討論。從變化趨勢上看,明初《易》經競爭力最強的是建寧府,但至宣德解額制實施以后,便陷入低谷,此后雖不乏中式者,始終難現此前輝煌。福州府在明代中期保持了較明顯的優勢,能與之角力的是漳州府。弘治年間開始,泉州府的人數優勢開始顯現,與福州、漳州形成競爭之勢。嘉靖十三年至嘉靖三十四年的20年間,是四府競爭最為激烈的時期。泉州、福州兩府反復更換領先地位。漳州府與建寧府則維持著一定的競爭力。嘉靖三十七年以后,泉州府迅速拉大與其他府的差距,逐漸形成一家獨大的局面。(圖3)

圖3 明代福建四府《易》經中式人數的變化
泉州府在明代共產生舉人1 500余名,與福州府有較大差距。其科舉發展趨勢與漳州府相似,均是在明代后半段發力。其下轄的晉江縣,共產生《易》經舉人248人,名列全省第二。福州府《易》經舉人最多為福州府學186人,位于全省第3。晉江的《易》經舉人主要集中于嘉靖以后,福州府學則鼎盛于成、弘之際,盛衰之間,反映出福州、泉州二府科舉實力的交替。(表5)

表5 明代福州府學、晉江縣學《易》經中式人數變化
3.《尚書》與興化府優勢的維持
在1 438位習《書》經舉人中,興化府856人,占60%;泉州府191人,占13%;福州府有115人,漳州府111人,各占8%。在人數上,興化府在福建地區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從圖4來看,明初四府《書》經中式人數差距不大,但自宣德解額制度確立之后,興化府的優勢迅速體現出來。景泰年間的不拘額數,使興化府的中舉人數達到頂峰,其中大部為《尚書》優勝者。直至嘉靖年間,興化的領先地位仍十分明顯。嘉靖末年,泉州府《書》經人數逐步增長,至隆慶四年(1570)一度超越興化。進入萬歷年間,漳州與福州的人數也有明顯增加,興化府雖仍保有領先地位,但優勢已大不如前。(圖4)

圖4 明代福建四府《書》經中式人數的變化
通過對《詩》《書》《易》三經體現的四府關系的分析,可以對明代福建鄉試的變化趨勢做如下的概括。一是在分經取士制度的影響下,福建科舉實力較強的四個府均有較明顯的專經特征。鄉試的競爭,正是圍繞各經固有名額展開的爭奪。二是各個地區的專經特征有較明顯的階段變化。福州府能夠長期保持優勢,取決于其《詩》《易》在不同時期內的領先地位。興化府在明中期始終位居第二,一方面得益于《書》經的巨大優勢,一方面來自于對福州府《詩》經份額的蠶食。隆慶以后,漳州府在《詩》與泉州府在《易》上的突出表現,在《尚書》上與興化府的競爭,使二府迅速成為福建地區的科舉“新貴”。三是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下,沒有一個地區能夠長期保持專經的優勢。明初不拘解額時期,是各府競相發展時期。進入宣德以后,各府處于此消彼長的關系中,有專經優勢的地區往往率先脫穎而出,但優勢難以長期保持。專經地區的轉移意味著原有人才“高地”的衰落,從另一角度看,也未嘗不是對舊有壟斷局面的打破。泉州與漳州在明代后期的崛起,表明地區之間科舉實力差距的逐漸縮小,福建地區的鄉試競爭也呈現更為多元的局面。
三、明代福建地域專經現象的考察
活躍于明成化、弘治年間的吳寬曾道:“士之明于經者或專于一邑,若莆田之《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禮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蘇而已。”[6]卷34,285文中提到的莆田,為興化府下轄縣屬之一。興化府在整個明代科舉地位的不墜,正是來自莆田等縣域專經的強力支持。上文的分析也表明,決定府際競爭關系變化的發起和落腳點,正在于莆田這樣的縣域專經。
那么,影響這些縣域專經興起與衰落的原因又何在呢?不論是此前的福州、興化,抑或是后期的泉州與漳州,均位于福建省的沿海地區。換言之,福建省的科舉發展主要取決于“海運”。對此,不少學者也曾就濱海地區的人文現象進行過考察,認為海路的暢通,海外貿易的興起,是地方科舉與人文的強心劑。[7][8]這樣一種觀點,固然可以視為地方科舉興衰的一般邏輯,但卻難以解釋為何在沿海府際之間存在著的盛衰消長。故在此,本文擬以福州府閩縣地區為對象,通過對該地區《禮》經盛衰的考察,嘗試做出相應的解答。
明代科舉中,《禮記》《春秋》二經應試者少,往往被視為“孤經”。原因之一在于傳注繁復,不利于記誦。①“夫以其繁如此,重之傳注,而訓詁家更欲自傳注推演之,且其得者既無取于相明,而其失者復不足以相正。有識之士乃厭棄焉。”(明)陳鴻恩:《禮記手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唐振吾廣慶堂刻本,第94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頁。據吳宣德統計,在明代64科會試中分經錄取中,習《春秋》和《禮記》者所占比例不及十分之一。[2]又據汪維真的統計,《禮記》在五經中的比例在天順四年(1460)之前在10%到15%之間,隨后降至7%到10%之間,正德六年之后降至7%以下。[9]這一比例,與福建鄉試中的《禮記》錄取情況大致相當。
根據《閩省賢書》記載,福建地區可統計的《禮》經出身的舉人有494名。其中福州府有282人,占總數的57%,下轄的福州府學、閩縣、候官縣包攬全省前三名,分別為88、81、58人;泉州府有108人,占22%,下轄的泉州府學、晉江分列全省第四、五名,分別為40、35人;建寧府25人,漳州府21人,約占4%。由此可見,以福州府附廓閩縣、候官為中心的區域,是明代福建科舉中名副其實的《禮記》人才高地。
南宋時期,閩縣便已有深厚的治《禮》傳統,代表者有三山地區的劉氏三先生。②三先生分別為劉彝、劉康夫、劉藻。劉彝著有《周禮中義》十卷、《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禮記大全》等書。劉康夫“以敦厚風俗,崇獎名教為己任,主鄉校者三十余載,從游千余人”。劉藻著有《禮書》《易解》。(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光祿劉執中先生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75、170、173頁。其中劉藻又與王普、任文薦被朱熹譽為“明《禮》者,此三人是也”[10]卷10,171。至明,以學術合輒科舉者,代表人物如陳湜,為永樂十三年進士,授翰林編修,[11]卷72,1 343著有《儀禮舉要》三卷。[10]卷41,491鄭旭,明太祖選德望十人傅東宮,旭名第二。著有《詩經總旨》《初學提綱》《詠竹稿》等書。[10]卷41,491其孫鄭亮,“家居,學徒造門問業”,開始以《禮》學傳家。[10]卷41,493稍后者有鄧遷,嘉靖七年以《禮記》中舉,著有《禮經講義》等,其子鄧原岳,字汝高,萬歷十三年以《禮記》中經魁,壬辰進士,著有《禮記參衡》。[10]卷41,1 343鄧氏族子鄧庭曾,字道宗,撰有《禮記集解》《禮記訂補》。[12]96明末有鄭羽儀,崇禎癸未科進士,以《禮記》中式,有《戴記新旨》行世。[11]卷61,1167
除上述科舉人物外,閩縣《禮記》的成功,更得自于地方科舉家族的支持。明初閩縣地區共有32個進士家族,占福州府總進士家族的62%[13],其中不少便是以《禮》傳家。其中父子相傳者,林鈍“永樂領鄉薦,會試乙榜……升江西興國教諭,亦多所造就,《禮》經有傳,自鈍始”[10]卷20,507,其子林清源、林泮、林濬淵俱以《禮》登進士第。陳良弼,正統六年福州府學《禮記》舉人,子陳宗超弘治十七年閩縣《禮記》舉人。周熊,成化四年《禮記》中鄉試第四人,乙丑進士;其子周朝佐、周朝俛皆以《禮記》登進士第。張澤,成化十九年以《禮記》中鄉試第五人,聯捷會試[14]卷48,346,其子張孟中亦以《禮記》捷聯登第。周文燫,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舉人,子周仕堦,嘉靖四十三年閩縣禮記舉人。何偉,嘉靖元年禮記舉人,子何鎣,嘉靖十三年禮記舉人。
兄弟中式者,鄧焯,成化元年以《禮記》中式,弟鄧焲,成化十年以《禮記》中鄉試第五人。[14]卷48,335、341陳良弼正統六年鄉試中式,其兄陳拳正統三年中式,弘治十七年良弼子陳宗超以《禮記》中式,正德十一年其孫陳登希以《禮記》中式,聯捷進士。天順三年,李廷韶與弟廷美“以《禮》經同領鄉薦”[15]卷49,346,弟李廷儀則中成化七年鄉試,廷儀子李源,弘治十七年以《禮記》中式。孫承謀,福州府學萬歷十九年《禮記》舉人,子昌裔,萬歷三十一年閩縣禮記舉人,從弟孫昌祖,侯官人,天啟四年《禮記》舉人。
三代以上者,如洪英為永樂十二年《禮記》舉人,弘治年間,孫洪晅以《禮記》中式,“精于《禮》經,門下教授多所造就,能世其家學”[14]卷49,346,暄子世文和世遷皆以《禮記》中第,至嘉靖十三年,尚有洪英曾孫洪世文以《禮記》中舉。鄭鐄,正統六年辛酉《春秋》舉人、子鄭舉,正德八年《禮記》舉人、舉子鄭啟莫,嘉靖十九年《禮記》舉人。[14]卷48,322,361;卷49,376林廷庸,天順三年廣東中式,習經不詳,子文琛,閩縣成化二十二年《禮記》舉人,文琛子志寅,嘉靖二十二年閩縣《禮記》舉人。[14]卷48,332、348;卷49,377也有一些科舉家族,在傳之數代后,改習《禮記》的,如嘉靖三十四年閩縣《禮記》舉人葉于僉,曾祖葉鋌,成化十六年福州府《易》經舉人,祖葉文浩,弘治十四年(1501)閩縣《易》經舉人。[14]卷48,344、356;卷49,376
上述事例中,鄭旭及其家族無疑最具代表性。永樂十二年甲午科,鄭旭長子鄭瑛于應天中式,本經為《易》,子鄭珞、鄭珙,先后應福建鄉試十二年、二十年鄉試,分別以《春秋》《尚書》中式,子鄭瑛,亦以應天中式,治經不詳。鄭珙孫鄭濟,以《易經》中弘治己酉科鄉試。鄭瑛子鄭亮,以《禮記》中宣德元年丙午科鄉試。鄭亮孫鄭伯和以《禮記》中弘治辛酉鄉試,其“未第時以《禮》經授門下,士甚眾”[11]卷49,1 007。鄭漳、鄭澄以《禮記》分別中正德十一年、嘉靖元年鄉試。澄子鄭相以《禮記》中嘉靖十六年鄉試。相子鄭熙在隆慶庚午科鄉試中亦以《禮記》中式。從鄭旭至鄭熙,家族綿延八代,科甲不絕。其發跡于福建鄉試不拘額數時期,鄭旭于五經皆有涉獵,諸子科舉也是各執一經。宣德解額制實行后,區域內的科舉競爭難度陡然上升,鄭亮以《禮》起家,至孫鄭伯和應試時,福建鄉試分經取士人數已基本固定。對于家族應舉策略而言,專習《禮記》顯然能夠增加中舉的幾率,加之其他以《春秋》《尚書》《易》獲得成功的支派科舉之途已斷,鄭氏一族遂由明初的分治五經轉而為專治《禮》經。
除本土科舉家族外,外來學說的輸入對地方科舉成功亦有襄助。鄭瓘,字溫卿,浙江蘭谿人,“成化丁酉鄉薦,授閩縣教諭”[16]卷53,3a,任期考滿回京,登弘治三年庚戌科進士,著有《禮儀纂通》。其友人李承芳曾道:“周禮之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溫卿素有所考,而志欲行之者。”鄭瓘精于《禮》,且勤于誨人,任教閩縣時造就頗多。“溫卿訓閩時,其徒應科目而出者甚眾,且屢典文衡焉。凡士之出其門者,皆著有時名。”[17]卷129,9-10在其任教期間,成化十九年和二十二年福建兩科鄉試的《禮記》中式者,超過半數出自閩縣學。
從發展階段看,閩縣《禮記》的科舉成就,大部分集中于明代中期以前。至嘉靖后,代表性的家族和人物逐漸減少。強盛如鄭旭一族,在隆慶之后也是甲第乏人。從具體人數來看,隆慶以前,閩縣《禮記》共產生了67名舉人,占其明代《禮》經中式總人數2/3以上。可見,隆慶之后,閩縣《禮》經在科場中已不具優勢。
從表6二府《禮記》人數的變化關系可以看到,嘉靖后期,隨著泉州地區科舉整體實力的提升,其《禮記》人數也開始相應增加,并且在萬歷年間,一度壓制了福州地區。閩縣《禮記》在隆慶以后的衰落,與來自泉州地區的挑戰密不可分。以《禮記》人數排名全省第五的泉州府晉江縣為例,該地區的35名《禮記》舉人中,7人是在隆慶以前產生的,而從萬歷元年至萬歷二十二年的8科鄉試中,便產生了14名舉人。萬歷初期,是晉江《禮記》的一個“爆發期”。那么,這樣一種“爆發”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表6 明代福建福州、泉州二府《禮記》人數變化
在有關泉州科舉的記載中,有二人無疑值得注意。一是本地人林嶤,其曾在閩縣從鄧焲講《禮記》,“盡得蘊奧,以授泉士”[10]卷68,669。不過林嶤二子,林性之與林一新,分別在嘉靖元年與嘉靖十六年考中舉人,所業本經仍是泉州所專之《易》[18]卷56,1 464,由此也可見師承自閩縣的泉州《禮》學,競爭力似乎有限。另一人為常熟陸一鳳。一鳳祖陸隆恩、曾祖陸容皆以《詩》經取科第,父朝介為生員,至其改習《禮》經,嘉靖三十一年舉人,八上公車而不中,謁選得授泉州府推官,萬歷二年到任,萬歷七年卒于任上。其孫陸問禮、陸崇禮先后以《禮記》得中。在泉期間,其學深為陳鳴熙、何喬遠等人敬服,刻《三禮奧義》行于泉。[19]卷90,300-301其中,何喬遠與兄喬遷同中萬歷四年鄉舉,陳鳴熙、弟鳴勛、鳴烈先后中萬歷七年、萬歷十三年、二十二年鄉舉,均以《禮》經中式,鳴熙子昆奎又以《禮》記中萬歷三十四年舉人。值得注意的是,何喬遠父何炯,精擅于《易》,“士從游者以數百人”[10]卷41,493,有名者如嘉靖十九年舉人翁尭英、王承箕,嘉靖三十七年舉人沈維龍等,均以《易》經起家[10]卷60,614;卷75,722-724,何氏兄弟放棄家學捷徑,改經取勝,陸一鳳顯然是有提攜之功。[18]卷66,1 725
相較于林嶢對閩縣《禮》學的輸入,陸一鳳的到來與早逝,或可視為泉州《禮記》科舉在萬歷初年短暫爆發的原因。何氏兄弟盡管以《禮》起家,但其后人并未堅持下去。何喬遠子何九云、何喬遷孫何運亮,均以《易》中萬歷四十年、崇禎十五年鄉試。這一變化,意味著泉州士子對于《禮》的選擇,也可能是“迫不得已”的策略。對此,嘉靖三十一年中舉的泉州人李贄深有切體會,其謂:“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禮》經少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竊祿。”①“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禮》經少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竊祿。”[明]李贄:《李溫陵集》卷11《易因小序》,《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44冊,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151頁。李贄的兩次改經,顯示了其在泉州《易》經強手環伺下的變通。由此也可以理解盡管有家學淵源,何氏兄弟仍會選擇改習他經。然而即使這樣,在萬歷四年之前,何喬遷也是“屢蹶棘闈,每放榜,二人輒廢箸”[18]67。而陸一鳳的到來,竟成何氏家族命運轉圜的契機,其所傳入的《三禮奧義》,遂成為地方士子的決科之利,地方科舉的面貌也隨之一變。
四、結 論
福建為明代科舉的領先地區之一,其科舉表現一直受學界所矚目。本文以《閩省賢書》基礎,在統計明代福建90科鄉試錄取情況的基礎上,以專經為視角,進一步梳理了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數,分析其變化趨勢以及競爭關系,得到以下三點認識。
一是明代福建科舉格局的變化,主要呈現為前期福州府的一家獨大,至明中期變為福州、興化兩府爭鋒,萬歷后再變為泉州府、漳州府崛起的變化過程。這表明,地方科舉的優勢并非一成不變,對于明代科舉人才地理研究而言,除把握地方科舉的整體狀況外,還需注意其興衰變遷,方能更準確地定位地方人文的歷史地位。
二是上述科舉優勢地區,均存在明顯的專經特征。福州專《詩》,興化好《尚書》,泉州重《易》。而各個地區人數的消長,又取決于各地專經實力的變化。福州憑借《詩》經稱雄明代前期,但至成化以后,逐漸為興化所趕超。至嘉靖以后,漳州等地的迅速崛起,加速了福州府科舉優勢的喪失。長期位福建科舉第二把交椅的興化府,則因漳州、泉州等在明代后期《尚書》方面的強勢表現而逐漸低落。憑借著隆慶以后《易》經的突出表現,泉州從明初的中游,一躍為福建科舉的“人才高地”。
三是對于地方專經的微觀考察可以發現,閩縣《禮記》的成功在于早期歷史積淀下大量科舉家族的支持。這是地方治經文化對于科舉的直接影響。泉州《禮記》的崛起則表明,要想撼動領先者的地位,轉益多師是一種可行的方法。這既需要數代科舉人士不懈的努力,又需要恰當的“機運”。當本土的科舉文化遭遇外來學說的影響,尤其是在杰出科舉人物的帶動下,有可能實現人才數量上的“彎道超車”。
王汎森在《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一書中提到,在人類歷史天空中,大師們往往是成群地登場,一時間群星璀璨的答案在于物質條件與心理素質的強大支持、“群聚效應”“帶跑者”所發揮的效應,還有同儕之間健康的競爭兼合作關系的激發等,不過其并未將這些觀點做進一步的證釋。[20]252福建地方科舉發展過程中呈現的人才數量階段性與集聚性現象,或許多少能夠對這一問題做出些回應。